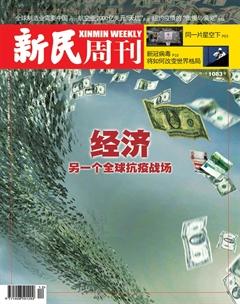不想讓金陵東路停在過去

沈彬
那天看了一篇微信公號的文章,才確定我熟悉的那條金陵東路終于要沒了。
早在1月初,金陵東路的居民們漸次喜氣洋洋搬場,店面如今都貨真價實地關了。
看著南粵風格的騎樓下的店鋪,統一被砌上磚紅大墻,總覺得要寫些什么——
小時候跟阿爸、姆媽“逛上海”——不要笑話我們浦東人,我們到市中心一直叫“去上海的”——幾條路線記得很清楚:南京路就是人多、店多;逛淮海路,就是路長到讓人絕望;金陵路呢?就是沿街騎樓。
記得那時金陵東路有好幾家布店、服裝店,姆媽一路是要逛過去的,我只是覺得無聊,但是金陵東路有騎樓,夏天不必站在毒太陽底下,還是很愜意的一件事。
我的生活和這條160年的老街有了故事,但我不想讓它永遠停留在過去。
對當年坐輪渡才能去浦西的浦東人來說,金陵東路上最“彈眼落睛”的建筑,是緊靠著外灘的金陵中學的大樓,素白高挑的建筑,在外灘清一色的花崗巖的建筑中相當出挑。它高達32層,當年曾是法國領事館所在地。
小時候,上海的高樓并不多見,坐電梯更是難得的享受。坐在浦江的輪渡船上,我就在幻想金陵中學的學生每天上下樓,都坐著電梯呼呼生風的樣子。無論如何,能在外灘后排上學,還是一件很拉風的事吧。
如今看慣陸家嘴高樓的上海人,有著平視全世界所有CBD高樓的器量,這恰恰是上海的變化給上海人帶來這種自信。
一條金陵東路,我小時候最想玩的地方就是那家曹素功墨莊。在騎樓下做出中式的琉璃瓦的翹角屋檐,構成中式山門。當時,我被里面各式各樣的墨錠給迷住了,有八仙過海的,有西湖十景的,有水滸一百單八將的,還有元寶形、屏風樣式,最多的還是“五百斤”、“千秋光”的墨錠。這里頭最貴的要數朱砂墨錠,我總要趴在玻璃櫥窗前數價簽上到底有幾個零。然后,這些一尺高的“龍飛鳳舞”墨錠、1萬元的朱砂,就成了我和小朋友吹牛的資本。
當年,我最想買的是五色的盤龍彩墨條,透著誘人的光彩,但一直沒有舍得買。前幾天,偶爾在淘寶上刷到這款彩墨條,也不過20元錢,還標明是“老庫存”,但顏色終不像當年那樣好看了。這有點像16歲小姑娘的花裙子,等到26歲有錢買了,卻再沒有當年的味道了。
今年年初,有新聞說,上海市南山路弄堂內的中華老字號“曹素功”面臨搬遷,讓人感慨。什么是上海呢?上海就是機會,上海就是變化。曹素功作為徽墨代表,卻在上海發揚光大,走的不是保守路線,相反是用足了上海品牌、上海場景。海上畫派巨擘——任伯年晚年曾在曹素功墨莊久住,他以畫家的體驗,指導工人改變了墨的調色,從此這款徽歙墨就被注入了上海的靈魂。
談老上海的文章,難免有一份淡淡的回不去的憂傷,這是人之常情。但是,懷舊,不是為了回到過去。在這條金陵東路上,還是小男生的我,吃到了人生第一口紫雪糕;在“曹素功”里,買到過第一支狼毫筆;10年前上夜班時,我天天踩著自行車,駛過夜深寂靜的金陵東路,去趕渡江的末班車……
我的生活和這條160年的老街有了故事,但我不想也不能讓它永遠停留在過去。因為我們只是城市的過客,城市的有機體有著它的生命節律。目前已經明確,改造之后金陵東路的騎樓不會拆,風貌會保留,會打造成“海派金陵路,活力新走廊”,那會是另一個城市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