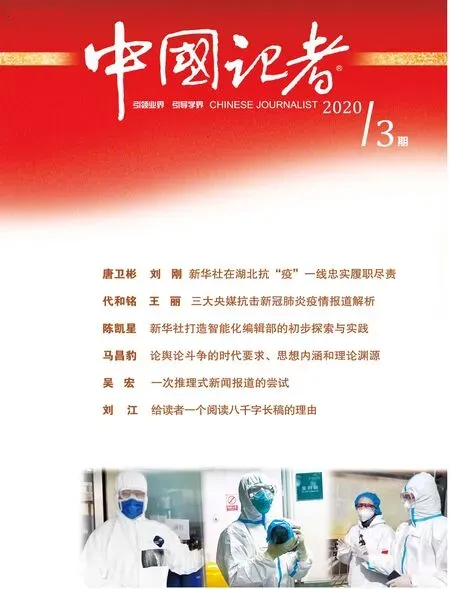走進疫情風暴中心
——疫區一月記
□ 胡浩
大年三十,離漢通道關閉第一天。
當我乘坐著回鄉的高鐵匆匆駛過這個讓人聞之色變的城市,車廂里的乘客無不好奇地向窗外張望:武漢,現在到底什么樣?
沒想到,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將用一個月的親身體驗來書寫。大年初四晚接到通知,匆匆安撫家人后,連夜趕回北京。大年初五,我們一行媒體人,走進疫情風暴的中心——武漢。
一、險
車門即將開啟的那一刻,我把一次性口罩摘下,換上厚厚的P M2.5口罩。說不懼怕,是不可能的。此前,各省報道的案例中,有太多人僅僅是在武漢中轉或短暫停留,就被感染了新冠肺炎。而有同事朋友得知我要去武漢好心勸阻,給我發來各種網上的視頻、文章,更是讓人心慌膽寒。夜幕下,這個空蕩蕩的城市,似乎連空氣中都彌漫著病毒,每次呼吸都是一種冒險。
身邊有媒體小伙伴開玩笑說,要不咱們別下車了。但其實大家都知道,這一刻,已不容退卻。
初到武漢的幾日,面對一道道橫亙于前的難題,人心慌亂、應對忙亂:
——底數不清。傳染病防控,必須找到和控制好傳染源,切斷疫情傳播途徑。當時的武漢,發熱門診人滿為患,網上求助頻頻出現。這座城市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了新冠肺炎?多少人尚未得到收治?沒有確切數據。
——方法不明。面對未知的病毒,怎么防控?如何治療?沒有現成答案。
——物資不足。缺床位、缺醫護、缺設備。當時全國所有的醫用防護服儲備,尚不能滿足武漢市一天的需求,床位的不足更讓不少患者求醫無門。
有大學同學向我求助,一位師弟的父親患新冠肺炎病重,問我是否能幫助聯系解決床位。我相當無奈地告訴她,采訪時親耳聽到省衛健委某領導因其家人患病無法入院,一直在打電話聯系卻也無果。床位的緊張、患者的眾多,由此可見一斑。
慌與亂,總是相伴相生。在紛亂的風暴中心,慌不可避免。
有同樣從北京來武漢支援抗疫的朋友感嘆:“在武漢戴口罩和在北京戴口罩,感覺截然不同。”正如一位武漢作家所寫:這段時間,在外地的朋友,經常發信息說:“我們一樣,也困在家里啊。”可是,我真的想告訴你們:你們的困,和我們的困,不一樣;你們的封,和我們也不一樣。我們每個小區,甚至每個樓棟,都有確診的患者。沒有人知道,下一個是誰。你們困在家里,可以打牌可以輕松地看電視;而我們每個困在家里的武漢人,在不停地擔心和害怕,不停地刷新聞,希望出現一點兒好轉,希望疫情早一點拐頭。
是的,正因為人們因恐慌而不停刷新聞的需求,所以我們來了。
二、戰
疫情來勢洶洶,風暴的中心絕無旁觀者。惟有各盡所能,背水一戰。
一到武漢,我們就投入緊張的采訪報道。白天轉戰采訪,夜間挑燈寫稿,凌晨2點睡,早上8點走,成為生活的常態節奏。
1月30日,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武漢市東湖高新區關東街南湖社區和龍城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江夏經濟開發區廟山鄔樹村;
2月1日,湖北孝感;
2月2日,火神山醫院;
2月4日,武漢市防控指揮部、洪山體育館方艙醫院;
2月8日,雷神山;
2月9日,湖北黃岡;
……
從重癥患者收治的定點醫院,到集中上千名輕癥患者的方艙醫院,從疾控中心實驗室到疑似患者和密切接觸者集中醫學觀察隔離點,有朋友形容說,“別人是往外逃,你們是追著病毒跑”。

▲ 2020 年2 月4 日,醫護人員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確診患者的行李物品送入武漢火神山醫院病房(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肖藝九/攝)
為了能及時獲得最真實的信息和最鮮活的素材,我們盡可能多采、多聽、多記。從中央赴湖北指導組了解中央最新的防疫精神和指示;向醫療專家和一線醫護人員問診湖北疫情防控現狀和相關防控舉措的效果;與社區工作者深談基層疫情防控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前方報道團隊人手緊張,我們在面臨巨大精神壓力的同時也承受著比平時更多的工作量。
由于每天長時間在外戴著口罩很少飲水,再加上睡眠不足。一天早上起來,我的嗓子又紅又腫,扁桃體發炎了。因為擔心因扁桃體發炎引起發燒,陷入被隔離的困境,我顧不得是否藥物濫用,直接雙管齊下,同時服用頭孢和藍芩口服液,將扁桃體炎壓制住。
2月15日,雨雪大風襲來。江城漫天飛雪,寒風往來呼嘯。冒著大雪,我們輾轉到武漢市泰康同濟醫院、武漢市優撫醫院等多地采訪,緊接著又到武漢市防控指揮部參加會議。一路踩著冰雪,我的鞋襪全都濕了,腳凍得生疼。為確保會議室通風,身后的窗戶大開,點點雪花隨風飄落到我的電腦上。
但我心里深知:沒有一個冬天不會過去,沒有一個春天不會到來。溫暖的春天應當就在不遠處。
三、思
我為什么要來武漢?作為一名記者,到疫情風暴中心能發揮什么作用?這是我一直在問自己的問題。
行前曾有朋友勸阻我說,你是一個9歲孩子的媽媽,平時又不跑醫衛口,沒有必須去一線的理由。而且,醫護人員上一線可以救死扶傷,你們記者去了能做什么?多一篇稿子少一篇沒什么影響。當時我的回答是,可能作為一名新聞人,我骨子里還有新聞理想。
能走到風暴中心,探尋事實、傳遞信息、記錄歷史,是新聞工作者的責任,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是一種幸運。
自從上大學成為新聞人,成為戰地記者就一直是我的愿望。2003年非典,我剛剛從學校走到工作崗位,在新華社總編室每天報送各種總結材料和數據。那時的我就特別羨慕一線記者。隨后伊拉克戰爭點燃中東,我參加駐外考試并申請派駐伊拉克,可惜最終只來到了與伊拉克毗鄰的約旦。當下,再次面臨上戰場的選擇,我確實不愿再留遺憾。
我們不是醫生護士,但同樣也能為抗疫而戰。
正如中國記協在慰問信中所說,“及時準確、公開透明報道疫情信息,全面準確解讀有關政策,把黨中央各項決策部署和各地各部門有力措施傳播到千家萬戶”“正確引導輿論,堅決維護社會穩定,傳播科學防控知識,增強群眾防病意識,把共克時艱、戰勝疫情的信心傳遞到億萬人民”,這就是新聞人在疫情防控阻擊戰中能夠發揮的作用。
在武漢,我看到上百名從各地逆行而來的媒體同仁,不問艱險、不計回報,同心而戰。他們用筆、用鏡頭向全國展現疫情風暴中心最真實的情況,凝聚抗疫決心和信心;他們解答疑問、澄清流言,傳播科學正確的防疫知識,有效避免疫情進一步擴大化;他們用一個個細膩感人的故事,傳遞愛與溫暖。
在這次疫情防控阻擊戰中,媒體人還發揮著一項特殊作用:深入武漢三鎮街道、社區、小區進行摸排,隨機調查武漢市未收治隔離的“四類人員”情況,像“探針”一樣深入疫情防控最前線,為中央指導組指導督導湖北省和武漢市疫情防控,了解分類集中收治隔離工作的落實進展,推動解決存在的問題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從每日新增確診病例數千名到幾百名,在萬眾一心的抗疫努力下,風暴已漸趨緩。
三月將近,武漢終將春回大地,櫻花如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