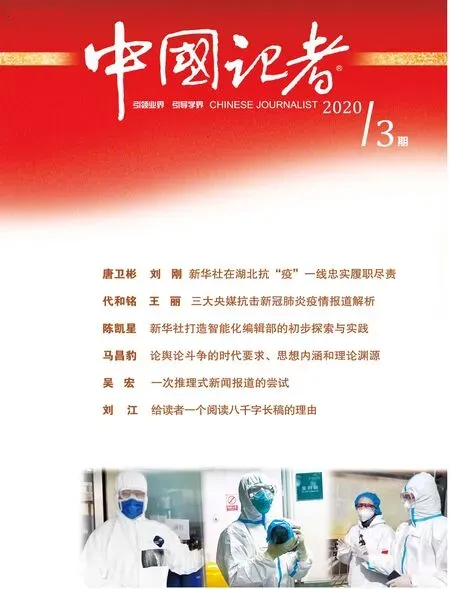用鏡頭記錄不平凡的平凡人
□ 柯皓
做了16年攝影記者,也經歷過很多重大報道的考驗。但新冠肺炎疫情突然來襲時,我的心仍如初入職場般準備不足。從凌晨的機場到重癥病房,從方艙醫院到居民社區,我的足跡遍布武漢三鎮……面對過患者家屬婆娑的淚眼,也見到過ICU里醫生堅毅的眼神。這一個多月里,漸漸地,我的內心從最初的惶恐不安變得慢慢平靜下來、直面一切。我一直堅守一線,以期記錄下暴風眼中的武漢,汲取一股股令人感動的力量。
一、傳播正能量的“漸凍”院長
1月26日,我和同事采訪武漢金銀潭醫院院長張定宇。出發前,同事簡單介紹了張定宇院長的情況。張定宇的愛人因新冠肺炎感染住院隔離,而他卻在這次疫情阻擊戰最先打響的地方、“離炮火最近”的金銀潭醫院,帶領600多名醫護人員,指揮堅守了近30天。我快速梳理信息,籌劃要拍攝的場景。
可是張定宇實在太忙。當日,解放軍陸軍軍醫大學醫療隊成建制接管該院兩個病區,同時,上海醫療隊正式接手該院老病房。張定宇手上兩部手機時刻響個不停。我們等了6個多小時,才有機會和張定宇面對面進行采訪。采訪中,張定宇講訴著一個多月來的緊張工作,突然說道:“我是一名漸凍癥患者。”當時,我心里“咯噔”一下,好像被什么東西卡住了,手中的相機險些滑落。在后面的采訪中,我都低頭不去看他的眼睛,怕他看到我眼中的淚水。當天時間太緊,張定宇忙于處理協調工作,沒有給我拍攝的機會。
多年的采訪經驗告訴我,這是一個傳播正能量的重大典型人物,我的鏡頭不能缺席,必須盡可能多地拍攝畫面和視頻。第二天,我再次來到金銀潭醫院,終于在他回到辦公室的間隙開始了拍攝。為了不影響他工作,我見縫插針,在辦公樓區域拍攝他工作的視頻和圖片。到了晚上,得知他要去病房協調危重病人轉運,我又緊跟其后,拍下他黑夜里一瘸一拐穿梭在醫院的背影、在病房外協調救護車、氧氣瓶的場景。拍攝完成,素材傳回《湖北日報》融媒體中心。經過后方編輯制作,視頻素材被加工成完整的短片。1月29日,《湖北日報》及其全媒體平臺文、圖、視頻同步推送,瞬間刷屏,搶占了各大網站的頭條。我拍攝的張定宇照片也被《人民日報》、新華社、央視等轉發、采用。
二、哭泣的醫生還原最真實的敬業情懷
1月28日,我和同事一早趕到武漢市肺科醫院ICU采訪。ICU病房里都是昏迷的重癥患者,來自國家衛健委專家組的醫生和護士們正在病床旁忙碌,我透過全是霧氣的護目鏡,用相機記錄眼前的一切。拍攝完成回到清潔區時,已臨近中午。同事余瑾毅在走廊的辦公桌旁采訪剛從ICU出來的胡明醫生,我坐在一旁參與采訪。期間,胡明醫生接到了一個電話,還沒說話,他就突然起身走向走廊另一頭,轉身回避我們。出于職業敏感,我多看了幾眼,發現他好像在抽泣。雖然聽不到他在說什么,但我意識到一定有突發情況。我立刻打開相機電源,直接開始錄制4K視頻。1分鐘后,胡明掛了電話,強忍著眼淚,回到辦公桌前。原來是他的好兄弟、東西湖區人民醫院ICU主任感染新冠肺炎,目前病情轉重,正在搶救。胡明紅著眼睛說,這些兄弟們為了搶救病人付出了太多,他們中有很多人自己的親人被感染了在醫院搶救,但還是各自堅守在崗位上。說到這里,他再次哽咽,頓時淚崩。同時,我的眼眶也熱了。整個過程我一直保持相機在錄制狀態。

▲ 2月5日晚,入住武漢國際會展中心“方艙醫院”的患者躺在病床上安靜地看書,一旁經過的護士向他豎起大拇指。當天22時起,位于武漢市江漢區武漢國際會展中心的“方艙醫院”正式啟用。(柯皓/攝)
采訪結束后,我立刻回到馬路邊的車上取電腦,處理拍攝素材。我首先處理的是最后拍攝的“醫生哭泣”的視頻素材,而不是早上在ICU里拍攝的畫面。經過一周的拍攝,隔離病房和ICU里的畫面已不再獨特和稀缺,反而是后來突發的感人瞬間更具傳播價值。我把視頻素材迅速發回報社,同時和后方編輯溝通。很快,湖北日報全媒體在多平臺多渠道對該視頻進行了分發。在抖音平臺上,視頻編輯給這段“哭泣的醫生”短視頻配上了一段文字:“同行倒下了,病人還得繼續救!武漢肺科醫院胡明得知同行好兄弟感染病危,泣不成聲!”不出所料,“哭泣的醫生”成了當日湖北日報新媒體產品中的爆款。這條20秒的短視頻獲得了1.46億次的播放量、877萬點贊和39萬條網友評論。
“哭泣的醫生”之所以能夠打動網友,獲得如此大的點擊量和關注度,我想是因為視頻展現了發生在你我身邊,有血有肉、令人感同身受的敬業情。人們在災難面前都脆弱。胡明代表的醫生們,一直戰斗在救人一線,在疫情籠罩的當下給受眾以剛強硬漢的形象,但在這一刻淚崩,正體現一個有血有肉的男子漢最真實的一面。面對苦難還要堅毅地活下去,還要繼續去面對、去搶救更多的病人。這也是這個非常時期所有醫護人員情懷的一個縮影。
作為一名攝影記者,在進行災難、疫情報道時,應該更多關注苦難中的人性。在后續拍攝中,我不斷提醒自己,注意細節,關注疫情下人們的狀態,記錄下感動自己的每個瞬間。
三、讀書小人物傳遞大信心
2月5日,武漢首個“方艙醫院”開始啟用,轉入病人。我和首批病人一同進入武漢國際會展中心方艙醫院。病人們進來后,護士們忙著幫病人搬行李、找床位、登記病例信息。不時有病人呼叫醫生,現場十分忙亂。
在拍攝時,我偶遇新華社記者熊琦,在這種危險的環境中遇到熟人格外親切。我們互相協助,把在病房里找到的梯子架在走廊上,輪流站上去拍攝全景。就在我尋找取景構圖時,突然發現不遠處有位患者躺在床上看書,與方艙里的忙亂相比,這股安靜的力量深深地打動了我,我迅速把他拍進了畫面。不一會兒,一名護士經過,不禁朝這位讀書的年輕人豎起大拇指,我立刻按下了快門,連拍了一組照片。隨后,我又拍攝了一段視頻和特寫鏡頭。我第一時間給報社發回所有素材,并和視頻編輯溝通。這組圖片和視頻經湖北日報多平臺多渠道分發后傳播效果很好。網友也給這位讀書的年輕人取名“清流哥”,很多網站紛紛轉載。就連年輕人所看《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的作者、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都在推特上轉發了這張照片。
后來,我又在拍攝中遇到了一位“考研哥”。2月14日,武漢體育中心方艙醫院,一位學生模樣的患者坐在角落的桌子旁讀書做筆記。我遠遠地拍攝了一組照片。隨后我上前和他交談,用手機拍攝采訪視頻。原來他是一名大三學生,目前正在備戰考研,目標是武漢大學的新聞傳播專業。這條“考研哥”視頻點贊達到40多萬。
其實在方艙醫院里,有很多這樣的人和故事。靜心讀書的“清流哥”、身體病了仍要繼續學習的“考研哥”,這些疫情下的“小人物”向大家傳遞出的是信心和希望。經過這幾次拍攝,我越來越明確,他們就是我要時刻關注和拍攝的對象。
對于疫情報道,作為一名攝影記者,除了忠實于新聞事實,客觀記錄之外,我們有責任去思考和探索如何積極捕捉疫情下的人性之美,大愛之善。從細節切入去展示大背景,記錄打動自己的每個瞬間,用鏡頭語言鼓舞大家積極勇敢地面對生活。即使形勢嚴峻,生活還要繼續,每個人都鎮定下來,做好自己,就是這個時代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