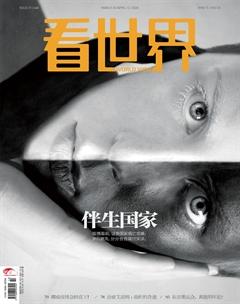如何一眼認出人群中的“日本男性”?
何焰

“常春藤七武士”,坐梯子上的為黑須敏之,中間戴眼鏡者為穗積和夫
一個男人,如果過度打扮,就容易遭受討厭。學生時代穿得最時髦的男生,最容易被家長當作是“流氓”。長大之后越在意外表的男性,越可能被批評說,“沒有男子氣概”。
雖然沒有人會拒絕帥氣和美貌,但是男人,最好不要對時尚表現出強烈興趣。
這是大多數亞洲社會的禁忌。即使在亞洲地區時尚風氣最濃郁的日本,也一度是這樣。
男性時尚
在東京奧運會舉辦的1964年,幾乎每個周末都有一兩千名青年,在東京銀座游逛。他們穿著類似的衣服—三粒扣的西裝外套、緊身的卡其褲,頭發梳成三七分,聚集在一起。
男男女女,嬉戲張望,共同模仿從美國東海岸學生群體中引進的“常春藤時尚”。這是日本街頭時尚的發端,也是日本時尚氣質多樣化的開端。
這群摩登男孩女孩,很快被日本警方逮捕、驅趕。但沒有叛逆,就沒有時尚,警方的治安維護,反而將當時的“常春藤”著裝,送上了神壇。
在之后的東京時尚演義中,每一種新潮流發起人,都是這樣,從邊緣走來,從男裝變革,激烈地開張。
石津謙介是日本“常春藤”時尚的始祖。銀座的兩千名青年,都是因為他介紹的美式時裝,而上街、被捕,引發狂熱,也因為他的一席演講,一周內消散如煙。
當時的VAN的店員,即使兜里一塊日元也沒有,也可以憑借三粒扣西裝、卡其褲和樂福鞋,隨意走進東京任何一家高檔消費場所,不被攔下來。VAN逐漸讓消費者們相信,這種新的美式穿衣風格是出色的,而不是流氓的。

日本歌手、演員木村拓哉
幾乎每一次時尚的興起,都是對前一次的顛覆。
20世紀60年代,日本時尚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新宿的邋遢嬉皮士俘獲了年輕人的心。嬉皮士風格,同樣不是日本的原創風格,而是來自美國西海岸的牛仔靈魂。
一時之間,牛仔褲替代了卡其褲的地位。在那十年日本賣出的牛仔褲,布料拼接起來,可以從地球來回月亮90次。牛仔褲的至尊經典款,Levis501直筒褲也面世了。值得一提的是,這條牛仔褲,不管是原版還是復刻款,都在日后賣出天價。
山崎真行作為叛逆少年,開創了日本的非主流“Yankii”時尚。它以原宿為據點,為20世紀70年代的中學輟學生和少年犯,提供時尚引導。夸張的豹紋、果凍色調的衣裙,把頭發梳得高高豎起,抹上一大罐頭油之后的鴨尾飛機頭,是他們的特征。
對于這一批日本時尚年輕人來說,坐上摩托飛車,挎上收音機,在周末的原宿廣場上起舞,是他們的永恒回憶。而隨后,由他掀起的“古著”狂潮,也“點石成金”般開啟了一輪新的日本時尚。
到了20世紀80年代,川久保玲、山本耀司在巴黎秀場一鳴驚人,隨后人們關注到了三宅一生、高田賢三。這些日本設計師,從國際市場回日本后,成為國內的神級人物,并塑造了一種“巴黎日本風”。
重松理在澀谷開了他的第二家Beams之后,消費者們開始逃離原宿,沖入澀谷。他的店鋪,開啟了一種新的澀谷休閑風格,帶來的“混搭”概念,在20世紀90年代初,統領了日本社會。當時的澀谷男孩女孩們,雖然身上每一件衣服都是美式風格,但整體美感卻已超越了美國。
20世紀90年代,是木村拓哉穿Bape的年代。藤原浩將嘻哈文化帶進日本,而他的徒弟Nigo,“藤原浩第二人”,將這種地下時尚更加推廣,即使是當時最炙手可熱的日本男星,也會連續穿著他們的品牌。當然,在優衣庫、Gap這些店鋪席卷日本之后,如今的Nigo,也是優衣庫的U.T. T恤的設計人。
縱觀日本街頭60年,女裝的流行趨勢和循環速度,始終要比男裝快上許多。但真正展現日本時尚變革的,還是要從男性時尚看起。


夸張的豹紋、果凍色調的衣裙,把頭發梳得高高豎起,抹上一大罐頭油之后的鴨尾飛機頭,是“Yankii”文化的特征
從叛逆里來
日本是制服社會,什么場合穿什么樣的衣服。對日本人來說,一個新的生命歷程,校園新生、職場新人、參加新的運動,往往都是從一套閃閃發光的新制服開始的。
日本的制服是有講究的。在一些特別場合,日本男士必須穿著西裝。會議、婚禮、葬禮場合的西裝,也各自有不同的設計。
有個古老的笑話,中國人去日本購買西裝,穿回國覺得很漂亮自豪,結果鬧了笑話。他不知道那是葬禮專用的。
但講究,并不意味著時尚。在傳統的日本文化中,人們把“著裝得體”編織進社會規范。“只有好好穿制服的孩子,才是好孩子。不好好穿衣服的人,可能是教育出了問題,要么不孝,要么有犯罪的可能。”
這個想法如今聽起來是天方夜譚,但對于90后之前的各代中國人來說,很容易感同身受。乖順的學生,在路上碰到穿喇叭褲的同學,大多會繞開走。穿慣了制服的時代,對時尚的恐懼是共通的。
但是,如果人們到哪里都穿制服,那么這個國家就不可能會有“年輕時尚”。如果人們,尤其是男人們穿上學生服、工作服,那么就從不會為穿著動腦子,而沒有時尚眼光的訓練,就永遠也不可能穿得多漂亮。
日本最早的時尚,是從變形的學生制服里來的。
青少年開始通過打扮自己來尋找自己的時候,第一件事必然是反抗制服。他們換上制服以外的外套,就是把對時代的批評穿在身上。
VAN Jacket把“常春藤”衣服賣給了青少年,這些青少年被警察帶進監獄,VAN也被成年人仇視。但實際上,它模仿的只是美國東海岸的大學生穿著。當VAN變成主流,成為家長會上的得體服裝之后,VAN的時尚勁頭也就過去了。
緊接而來的“脫離甚至遠離制服”,也是意料之中的。嬉皮士風格,“Yankii”不良少年風格,前衛的“巴黎日本風”,Beams的澀谷休閑風格,由藤原浩引入、Nigo發揚的街頭時尚……幾乎每一次時尚的興起,都是對前一次的顛覆。反叛服裝定式,是日本時尚永恒的潮流。
對于日本女性來說,“卡哇伊”是一個絕對高級的形容詞。不同于其他國家形容另一個人“可愛”時,多少帶點意味不明的貶義,日本人的“卡哇伊”,幾乎是一個沒有負面意義的詞匯。但是,日本的女性時尚,也早已脫離了只有“可愛”的階段。
一度,東京街頭多了許多通身黑衣的女孩,她們當時被稱為“烏鴉女”。這些“沒有性別的服裝”開始流行,對傳統的成熟女性形象進行了否定。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日本時尚的興起,可不只有叛逆作為興奮劑。
對叛逆心態的包容,讓日本消費者有機會打破對著裝的偏見,從制服里出逃。但真正對日本時尚業有持續影響的,是日本的時尚刊物、經濟發展、制造業發達和工匠精神。
1956年,日本結束“戰后”狀態,開始經濟快速增長。戰后嬰兒潮一代,富裕階層最先追逐時尚,進而輟學生和不良少年們也不甘人后,在原宿發展出自己的時尚。但歸根結底,不管是富裕階層,還是輟學生、藍領工人甚至不良少年,他們都有足夠的資金為自己購置相應成本的衣著。
這60年里,美國始終是日本時尚界的模仿對象,如今美國早已失落自己的著裝傳統,比如樂福鞋恍然已經變成了人字拖,“休閑”到令人嘆惋。而由于日本人的工匠精神、日本時尚刊物的權威以及日本制造業的不斷精進,21世紀初,日本的美式時尚已經遠遠超過了美國本身。
至于“日本時尚之城”的寶座,60年來,始終在東京的銀座、新宿、原宿和澀谷之間,漂來奪去。好在到最后,誰也沒有統一誰,才保留下來日本這多樣化的時尚繁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