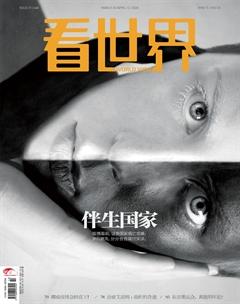冷靜克制的德國,與病毒共存?
章晶

3月22日,德國首都柏林的亞歷山大廣場行人稀少
疫情蔓延至歐洲,局面不容樂觀。截至3月26日,德國新冠肺炎累計確診37323例,死亡206例。
兩個月前,我在擔心國內的親友,現在輪到他們來擔心我了。2月,媽媽因為國內疫情暴發而取消了來德國的行程;現在,我因疫情在歐洲暴發,而暫停了去亞洲的旅居計劃。
“媒體的報道實在太夸大其詞了”
不久前,我們一家三口受邀去先生阿姨家的農場木屋,品嘗蘋果卷配香草醬。當時,新冠肺炎正在德國持續蔓延,但公布的確診病例尚未過千,暫無死亡,歐冠聯賽等大型活動是否該照常進行仍在商榷中。不過,新冠肺炎的新聞已占據各媒體頭條數日,話題正逐漸升溫。超市也刮起了第一輪搶購囤貨風,口罩早已脫銷。
于是,當我們圍坐在木桌邊吃熱乎乎的蘋果卷時,自然少不了對這一熱門話題的討論。阿姨當時對我說:“我想,媒體的報道實在太夸大其詞了。”婆婆的男友,也在一旁點頭贊同。
我不知如何回應。我知道與此同時,很多國人都在批判德國政府與媒體對疫情不夠重視、宣傳力度不夠、無所作為。因此,一些在德華人與留學生甚至想“逃難”包機回國,認為中國更加安全,而大部分德國人卻在這樣的危機面前,顯得異常淡定。
安格拉·默克爾坦言,預計會有60%~70%的在德人群將感染新冠病毒。
近日,德國新冠肺炎確診人數翻倍飆升,歐洲被世衛組織稱為“疫情中心”。不久前德國衛生部長詹斯·斯潘(Jens Spahn)還表示不會關閉國境,現又宣布關閉德國與法國、奧地利、瑞士的邊境。同時,學校、幼兒園停課,各種防疫措施多維度不斷升級中。在這樣的巨變與風暴之間,你永遠無法預料明天會發生什么。我不確定,阿姨如今是否仍然覺得媒體在夸大其詞,在德華人是否開始更冷靜淡定地與疫情相處了。
作為中國人,我比身邊的德國人更早關注疫情的暴發,更多了解疫情所觸發的人間悲劇,深知病毒的隱患與危害。甚至一部分的我,仍處于國內疫情的陰影之下,因此很難像許多德國人那般,理性而樂觀地對待這場正在暴發的疫情。同時,我也沒有許多華人那般的恐慌與憤慨。可能因為我歸園田居,這里人煙稀少,大多數人生活平和富足,即便在疫情的陰影下,也相對較少出現極端行為與物資短缺的現象。
與新冠病毒共存
如果說中國在面對疫情時,采取的是舉國之力抗擊嚴守,那么,德國采取的防疫措施是與新冠病毒共存,降低與拖延疫情對社會和經濟的危害。在這樣的對比之下,德國的做法似乎顯得有些冷漠與不夠徹底,這一點也令很多國人難有共鳴。
德國作為聯邦制共和國,它是通過各個邦政府與民間力量共同運作的。因此,即使衛生部長斯潘早已表示高度重視疫情,他也只能建議、倡導而沒有發號施令的權力。政府部門需要與民眾達成共識,再理性地按照疫情所處階段做出相應的舉措。在民眾與地方尚未意識到疫情的嚴重性時,推行嚴格措施,雷厲風行地大力宣傳,會顯得用力過度甚至超出法律邊界,也易引起恐慌。
經歷了納粹陰影的德國,一直有過度矯正的傾向,在汲取了慘痛教訓之后,他們不想再重蹈覆轍。因此在疫情危機之下,德國政府與大部分民眾也在盡力保持理智與覺知。而大多數德國人近年來沒有經歷過顛覆性的天災人禍,他們往往更注重生活質量與個人理想,內在安全感較為充足,缺乏面對危機的警覺與靈活的應變能力。
雖然德國沒有像英國一樣宣布“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的防疫政策—即讓六成民眾感染,痊愈后普遍獲得群體免疫力—但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也坦言,預計會有60%~70%的在德人群將感染新冠病毒。
柏林Charité醫學院的病毒專家德羅斯滕(Christian Drosten)是明星學者,他在近期播出的播客節目中提道:“我不再認為夏天會讓我們有喘息的機會,這次的疫情會全年持續,高峰在6、7月份。”他也表示,較為年輕的人群在夏日高峰之后,應該會擁有一定程度的免疫力。
雖然歐洲確診病例與死亡人數在不斷上升,但意大利的陽臺音樂會讓我感受到了一種樂觀態度。冷靜克制務實的德國人,又會在疫情的陰影下衍生出什么來?估計可能性最大且呼聲最高的就是疫苗了吧。
關于隔離與死亡
回到阿姨家的餐桌前,我們也因疫情討論到了隔離與死亡。阿姨聽說我們要飛去斯里蘭卡(當時還可以入境),有可能被隔離兩周,覺得這簡直不能太糟了。熱愛戶外活動的婆婆也覺得,我在國內的家人太慘了,過去兩個月都被困于家中。先生說,隔離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死亡。我4歲多的女兒也參與到討論中說,比起死亡,還是被關在屋子里兩周都不能出去玩更糟糕。
就當我們一邊喝著咖啡一邊淡定地聊著隔離與死亡的話題時,與我們一同圍坐在桌邊的,還有先生將近90歲的外婆。獨居于農場的外婆,無疑是對這個話題最沒有參與熱情的,同時也是疫情危機之下最脆弱群體中的一員。我想,如果在國內,不太可能在老人面前如此直白地談論死亡。
回過頭來看,華人在德國疫情暴發初期的焦慮可以理解,而德國民眾的后知后覺與政府相對溫和的策略,其實也是合情合理的。當我們了解到國情、體制與階段的差異之后,才能更具同理心并理性深入地看待疫情之下不同國家的應對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