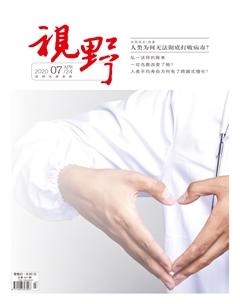瘟疫并不是歷史的配角
趙靈犀

一直以來人們認為瘟疫是歷史的配角,其實瘟疫一直是歷史的主角,大瘟疫的每一次到訪都深刻地改變歷史進程。自從人類開始群居以后,瘟疫就一直在如影隨形地跟隨著我們。由此產生的信仰、巫術,更是長時間影響人們的精神世界。
瘟疫為何如此可怕?在于強大的傳染性、變異性,病毒的變化速度驚人,而人類進化出抗體的速度相對緩慢,瘟疫爆發,大規模的族群死亡,對于任何人都將帶來強大的沖擊和震撼。
這種刺激,是任何人為的戰爭、酷刑、懲罰都無法比擬的。
病菌阻礙南北融合
古代中國人為何不愛去南方?因為瘟疫,古人稱呼為瘴氣。中華文明發源于黃河流域,著名的黃帝炎帝大戰都是在今天的山西和華北地區開展,這里氣候干燥,四季分明,不利于病毒的快速繁殖,是那個時代最為合適的生活區域。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曾經提到“江南卑濕,丈夫早夭”,也就是江南氣候潮濕,人不能長壽。從史料上看,被派往南方的官員往往任期很短,而且死亡率高得出奇。
造成人員大量死亡的顯然不是潮濕的氣候,而是居住在潮濕環境中的病菌。在黃河流域,天氣幫了人類大忙,寒冷的冬天殺死了大量病菌,而在溫暖的江南,病菌可以一年四季肆意繁殖,長年累月,這里就充斥著大量北方人從未經受過的疫病,比如登革熱、瘧疾等等,它們就在這里等候北方移民自投羅網。
所以自古被發配到南方都被認為是有去無回的,極有可能病死他鄉,因為北方人沒有適應當地的各類病菌,而當地人已經很好地適應了。
三國曹操赤壁大敗很大的因素就是北方士兵到了長江流域,大量染病,瘟疫流行,造成大量非戰斗減員。這次打敗而回幸存的士兵也因此有了抗體,所以經過幾十年的適應,當再次伐吳時,瘟疫不再發揮作用,晉軍得以順利進軍。
北宋時62歲的蘇軾被一葉孤舟送到了徼邊荒涼之地海南島儋州。據說在宋朝,放逐海南是僅比滿門抄斬罪輕一等的處罰,目的就是要讓當地的瘴氣將其置于死地,還不會背上殺才士的罵名。
戰勝病菌才能統一中國
由于病菌的阻隔,南北融合的過程一直很緩慢,唐代以前南北文化、語言、經濟差異顯著,如果就這樣發展下去,很有可能會形成兩個各自進化的中國。
隨著永嘉之亂,大量人口被迫開始南遷。但是直到唐代,也就是8世紀左右,長江流域及以南地區的人口密度都不高,到了400年后的南宋,成千上萬的農民才遍及華中和華南地區。
可以想象,移民的過程是緩慢且痛苦的,人們要面對從未經受過的疾病,然后在漫長的調適期里和它們逐漸適應、共存。所幸,中國人完成了這個艱難的融合。
瘟疫塑造了我們的精神世界
過去幾千年里,人們雖然無法用科學解釋瘟疫,但對瘟疫的觀察,卻讓我們總結出一套遠離瘟疫的方法,以儀式的方式流傳下來。比如,有的宗教禁食豬肉。要知道,過去的養殖條件可不像今天,豬的飲食相當龐雜,包括腐爛的動物尸體、糞便,還有各種不干凈的東西。假如豬肉沒有徹底煮熟,人一旦吃進去,就很容易感染寄生蟲。所以,在麥克尼爾看來,古代禁食豬肉的宗教習俗,本質是建立在對疾病的恐懼之上,它可以減少病從口入的幾率。除此之外,另一個宗教儀式——沐浴,則能夠避免因皮膚接觸導致的感染。伊斯蘭教和印度教中都有沐浴儀式。
但諷刺的是,年深日久,這些儀式最初的功能在傳播中逐漸被人們淡忘,再后來,儀式被徹底神圣化,反而成了疾病傳播的途徑。比如,為了慶祝宗教節日,成千上萬的朝圣者聚集在一起集體沐浴,這就為疾病尋找新的宿主提供了絕佳的機會。你看,疾病對文化的塑造,催生了一套頗為實用的制度習俗,這些習俗以文化的方式留存下來,但有的習俗在傳承和演繹中,卻又漸漸背離了初衷,甚至發揮了反作用。
另外兩大宗教,佛教和基督教,在宗教文化上也或多或少受到了疾病的影響。佛教源自印度,與寒冷地區相比,傳染病在印度的發病率顯然更高;基督教形成于耶路撒冷等城市,人口密度比較高,傳染病的發病率也肯定高于人口稀疏的地區,所以從一開始,兩種宗教都把突如其來的疾病看作理所當然。他們都勸導人們說,死亡是對痛苦的超脫,是進入極樂世界或者天堂的必經之路,在那里,生前受到的所有不公和痛苦都將得到補償。
在公元251年的羅馬大瘟疫中,一位基督教主教曾經寫過這么一段話,大概意思是:瘟疫對異教徒來說是災難,但對上帝的仆人來說則是一場拯救。那些死去的人中,正義者被召喚去開始新生,非正義者則被召去受刑,所以,這場瘟疫凸顯了正義,測試了人類的靈魂,它爆發得正是時候,而且很有必要。這套解釋對正遭受瘟疫的人來說,是一種無與倫比的安撫。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因為疫病,基督教和佛教才建立了一套適用于痛苦、疾病和亂世的思想和情感體系,收獲了大量的追隨者。
除了對宗教的影響,瘟疫對文化的塑造也深入日常生活。在大部分農業社會,早婚和多生孩子都是一種美德,也是天賜福澤的標志。當然,繁衍后代是生物的本能,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過去醫療條件落后,嬰兒的死亡率很高,生育盡可能多的后代,也可以抵御疾病帶來的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