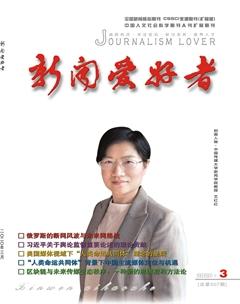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回顧與展望
艾紅紅 韓文婷
【摘要】我國新聞學博士招生自1984年啟動至今,無論是在招生中引進和試行“申請—考核”制,還是在培養過程中強調學科前沿知識及增加過程性考核環節,都是為提高培養質量而做的有益嘗試。在此基礎上,提高招考機制的科學性與公平性,側重對研究能力與創新思維的考察,彌補培養過程中“學”與“術”的偏差,細化不同研究方向博士生的考評規則,以及嚴把學位論文選題關與質量關,平衡好過程性考核與最終考核之間的關系等,將是下一步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改革的重點。
【關鍵詞】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歷史;反思
我國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起步于1984年,至今已有36年的歷史。其改革與發展的路徑既與其他學科/專業博士生教育進程大致契合,又呈現出本學科獨有的特征,在招生、培養、過程性考核及學位授予等環節積累了很多有益經驗,也存在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
1983年5月25日至6月1日,第一次全國新聞教育工作座談會由中宣部和教育部在北京聯合召開。會后下發的《關于加強新聞教育工作的意見》指出,新聞教育所培養的人才無論數量和質量都不能適應新聞事業發展的需要,“必須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有一個較快、較大的發展”,要求改革招生與分配制度,增設新專業點,改變專業單一化狀況。[1]此后新聞學博士生教育被提上了日程。1984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獲得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權,并于當年開始招收新聞學博士生。隨著1988年首批新聞學博士生圓滿畢業,中國開始有了自己培養的最高級別的新聞學專才。但直到1996年,全國仍只有人大和復旦兩個新聞學博士授權點。
拐點出現在1997年。這年6月,教育部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決定將新聞學由二級學科升為一級學科,定名為“新聞傳播學”。次年修訂并公布的博士生學位授予點專業目錄顯示,“新聞傳播學”列于文學門類之下,下設新聞學、傳播學兩個二級學科。2000年,國務院學位辦批準有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點的高校可自主設立若干二級學科專業點。此后,新聞傳播學博士招生數量與規模水漲船高,博士生的專業和方向設置也日趨靈活多樣,出現了傳媒經濟學、跨文化傳播學、廣播電視與數字媒體等新的專業方向。到2019年底,全國新聞傳播學一級學科博士點已增至26個。[2]
在招生專業及博士點不斷擴張的同時,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招考也從最初的統一考試變為統一招考、碩博連讀、推薦免試、單獨選拔優秀人才及少數民族高層次骨干人才計劃等多種渠道和方式,重在考察考生的個人品行、創新精神、創新能力、科研潛質和綜合素質。其中,“申請—審核”制與“申請—考核”制就是為優化招考制度而進行的有益嘗試,目的是增加過程性考察環節,下放給學院和導師更多自主權,從中篩選出真正適于科研的優秀人才。目前,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華中科技大學、武漢大學等高校新聞傳播學專業博士生招生均實行了上述制度。
從博士生入學后的培養環節看,培養目標與培養體系尤其是課程體系基本是與時俱進的。新聞傳播學研究方法、新媒體研究、媒介與社會、數據挖掘與可視化傳播、視聽語言研究、文化與傳播研究、受眾分析、媒介前沿、國際傳播等以前沒有的課程陸續被納入博士生培養方案,體現了學科增長點在跨學科與高層次之間的有機嫁接。為鼓勵博士生們廣泛閱讀與精深研究,近年來,一些高校新聞傳播院系還通過“學術午餐會”和讀書會等多種方式,積極為博士生搭建課外學術交流平臺。
培育適應融合媒體時代的高端國際傳播人才,是近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培養的另一重要趨勢。近年來,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等新聞傳播院系都為博士生設置了新聞傳播學雙語課程,注重與國外高校和專家團隊交流,加強國際合作,著力培養熟練掌握外語、擁有國際傳播能力的優秀人才,取得了很大成就。部分高校還要求博士生除完成國內課業外,需在國外對應的高校、科研院所訪學半年到一年,并完成相應的課程,為此甚至不惜推遲三年畢業計劃。而國家留學基金委近年推行的公派研究生計劃也鼓勵和資助聯合培養博士生出國從事6—24個月的訪學,更是助推了這一國際化進程。
在上述課程體系與培養方案中,除了不斷改革和新增的內容,一些傳統的基礎性課程卻自始至終貫穿了幾十年的博士生教育體系。如作為通選課程的外國語和作為專業通選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課、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課等。尤其是近幾年,無論媒體變革如何劇烈,無論對適應媒介需求的復合型人才如何界定,都始終強調博士生在學期間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也就是說,重視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是當代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基本特色,也是這一學科博士生教育的底色。
二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啟動之初,王中、甘惜分等早期的博士生導師既熟稔新聞業的基本流程,又注重博士生的基礎理論培養。但隨著部分從學校到學校的新聞學博士畢業后陸續成為導師,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學”與“術”分離現象日益加劇。這本無可厚非,也符合學術發展的規律,說明新聞學、傳播學在中國經過多年發展,其理論基礎與學術含量已有了很大提升。問題在于,新聞學專業尤其是新聞實務方向的博士生是面向媒體一線,如果導師的實踐與理論視野不能與之匹配,培養質量恐難以保證。尤其是在媒介融合的熱潮和新媒體的沖擊下,新聞傳播業需要實踐經驗與理論水平雙高的專業人才,需要具備綜合、交叉學科背景的優秀學子充實媒體研究部門。而這極有可能也是部分來自高校、脫離媒體實踐的純科研型博導自身所缺失的。研究表明,美國排名第一的西北大學Medill新聞學院幾乎所有教師都有媒體從業經驗,其中一半人的媒體從業時間達20年以上,85%左右的教師獲得過各級各類的新聞獎項。美國其他新聞院校的師資中,業界人士占2/3左右,與1/3的“學院派”教師有機組合在一起,確實能使新聞傳播理論教學真正與傳播實際相結合。[3]意識到這一缺失后,近幾年一些高校新聞院系開始聘請業界的資深媒體人兼任博士生導師,以彌補“學”與“術”失衡的狀態。但實際執行的效果卻不盡如人意。一是業界導師大多擔任本單位較高領導職務,本職工作繁忙,無法像高校教師那樣全職指導學生,很多具體事務只能委托校內教師代勞,無法實現學與術的互補;二是在教育部日益緊縮的招生名額分配機制下,聘任校外導師勢必與本校教師利益沖突,如果校外導師無法到崗履職,又會引發批評,故而這一嘗試目前尚處在謹慎探索、小步前行中。
站在博士生的角度看,還應是“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培養環節效果如何,固然需要招生培養單位、導師與學生通力合作,其實更需要學生順利通過各項課程考核,同時對學術公關課題孜孜以求,尋找解決和創新之道。
與其他專業一樣,新聞傳播學博士生在學期間,除各門課程必須及格外,學術論文與學位論文情況也是考核其學業水平的重要指標。早期的新聞學博士生培養并沒有在學期間發表論文的硬性規定,學生們擁有較大自由,可集中精力專攻學位論文。但近年來隨著教育部和各高校對博士生管理的精細化,很多高校強制要求博士生在學期間必須發表一定數量、一定規格的論文,并將其與畢業要求掛鉤。在這一硬性規定下,各專業期刊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論文發表數量激增。博士生們還頻繁出入各類學術會議,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推了各地的學術會議熱潮。不可否認,很多優秀的學術論文出自在校博士生之手,制度刺激的正面效應顯著。然而也應看到,將在學期間發表的論文數量、刊物等級與學生畢業條件掛鉤,勢必出現為完成指標而不顧質量的短期行為,承擔學術泡沫及低水平重復等不良后果。一些博士生為追求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傾向于尋找易于操作的選題;那些需要長時間花大力氣去開掘的有價值選題,則在上述論文需求指揮棒下受到冷遇。另一個不良后果是,以前博士生在學期間發表的論文多與學位論文相關,或是其學位論文的階段性成果。但在當前的查重機制下,引用自己公開發表的論文也有被判定為“抄襲”的風險。為避免出現查重數值高的問題,博士生們不敢將自己的學位論文相關內容作為中期成果,只能改做其他議題。這分散了在學期間的研究重點不說,也意味著學位論文研究與打磨時間的縮短。事實上,這一現象并非新聞傳播學專業所獨有,但如何改變唯課業成績和學術論文是瞻的評價體系,設立相對多元的評價標準,恐怕是下一步改革的重點之一。
作為博士生所受學術訓練的最終答卷,幾十年來,新聞(傳播)學博士生學位論文從學術角度對新聞傳播的理論、歷史與實踐的不同方面進行了深度開掘,可說是管窺新聞傳播學學科發展水平的一個重要指標。通過對比分析1988年至今的博士論文標題可以發現,首先,近幾年來,出現頻次最多的詞已由30年前的“新聞”變為“傳播”。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傳播學作為后起之秀,已經從最初本著改造傳統新聞學的目的對傳播學理論和學術規范的橫向移植,到目前已成了新聞傳播學領域的“主題詞”與“關鍵詞”;而傳播力構建作為提高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正受到來自最高領導層的重視,也必然會在新聞傳播學博士生論文中有所投射。其次,論文標題中的另一高頻詞匯是“中國”,說明近年新聞傳播學博士論文依舊緊盯國內問題,重視建設中國自己的新聞傳播學。這也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事業不斷取得“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體現。最后,近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學位論文的主題更加多元,其中僅與新媒體元素相結合的就占據了半壁江山。這種對“新媒體”“互聯網”“網絡”的聚焦與追逐,顯然是新聞傳播學博士生學位論文與時俱進,關注媒介發展現狀及趨勢的結果。總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作為新聞傳播業的頂尖人才培養體系,從博士學位論文標題詞頻呈現出的扎根本土和追逐前沿特征,說明本學科的培養目標與結果、社會需求與教育反饋之間的良好互動。
然而僅從論文的標題還難以判斷博士生論文的水平與質量,測度其創新性與適用性。一個公認的比較突出的問題是,部分從事應用研究的學位論文如傳媒/傳播“戰略”“策略”“對策”“建構”等課題,很多都出自沒有傳媒實戰經驗的年輕博士生之手。一些成果在實踐層面的零轉化和難落實,至少說明了這類“應用型”研究在可行性環節的把關上存在缺失。
三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健康發展,既需要制度設計上的不斷完善,更需要與時俱進、勇于改革的責任擔當。博士生教育的重要目標是研究能力與創新思維,但目前的招考制度卻未能體現這一要求,也與英美國家的招考制度形成較大反差。
筆者認為,在招生自主權已部分下放的當下,除保留碩博連讀、專項計劃等招生方式外,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招生可進一步提高“申請—審核”制及“申請—考核”制的份額,把對學生能力的考察前置,給學院和導師更大的自主權。在現有的26所新聞傳播學一級學科博士點高校中,以“申請—考核”制作為唯一招考方式的一級學科點目前已有幾家,如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清華大學等。有的學校在初審材料后的考核環節還加入了筆試內容。中國傳媒大學、北京大學、暨南大學等十幾所高校則對部分考生采取“申請—考核”制方式。另有7所高校(科研院所)尚未開展“申請—考核”制試點。實行“申請—考核”制的優勢在于,專家組事先審核學生的報考材料,可對其學業水平、外語能力和學科專業背景等有更多的了解,在此基礎上重點考察學生的科研能力與報考專業的匹配度,并根據復試成績決定錄取資格。為避免導師在篩選過程中的偏差或舞弊行為,可采取導師組匿名打分等雙盲方式,盡量保證審核層面的公平與公正。如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的做法是按申請專業分別進行初審。“初審小組對申請人的學術背景、專業基礎、研究計劃、綜合素質等進行全面考察,每位專家獨立評分。”再根據申請者的初審成績排序,“每個專業按不高于普通招考博士生招生計劃3倍的人數擬定復試人員名單,經學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領導小組審議后再將初審結果通知到申請者”[4]。華中科技大學則是學院成立研究生招生工作領導小組,對整個復試和錄取工作進行統一領導,成立招生工作監察小組,監督檢查學院的招生錄取工作。[5]對考生而言,如果想在“申請—考核”制環節不被淘汰,就需在碩士階段或實際工作中擘畫未來研究方向,并在這一過程中不斷調整思路,積累相關科研成果和經驗,形成前后相繼、已取得的學術成果或工作經驗支持后續博士生階段研究的路徑,而不是像現在很多考生那樣,先期全力投入復習應試,進入復試階段才匆忙準備入學后的科研設想。
招考機制的調整,還需培養環節的密切配合。加大招生階段的考核力度,是為了讓真正優秀的人才進入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隊列。學生入學后,還需通過相應的過程性評估,進一步完善培養過程中的動態考評機制。目前所有單位的博士研究生培養實行的都是導師負責制,采取導師負責與集體培養相結合的辦法,或為每個博士生量體裁衣,成立論文指導小組。隨著互聯網新媒體的發展及媒介融合的加深,跨學科、跨專業的博士生新增專業(方向)還會不斷涌現,需要在不同專業、高校甚至媒體之間進一步打破區隔,選擇部分專業設立“融學科”培養模式[6],如設置新聞與計算機、政法、外語等學院間的交流活動,對學科交叉范圍建立融合式的合作發展平臺,并為博士生們跨專業和跨學校選課提供條件。而在最后的學位論文環節,目前幾所高校新聞院系推行的博士學位論文預答辯制度,實際是為博士生的學位論文設置了一道質量關,可在所有高校新聞傳播院系推廣。
由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是高端新聞傳播學理論與實踐人才,雖說其整體偏向本來就是“紙上談兵”,但也不應忘記回饋新聞業的滋養,尤其是偏應用型的學術研究成果,需對生機盎然的新聞傳媒業產生引領與示范作用。基于當下基礎研究型與專業指導型博士的培養和考評區別不大的問題,可以考慮進一步細化規則,或參照歐美國家的做法,區分本學科中哪些博士專業培養的是實操性人才,哪些專業培養的是基礎研究工作者。對從事基礎性研究的博士生,不應單純以發表的論文數量與刊物層級作為考評標準,尤其不應將這類指標量化甚至做出硬性規定,而是應著重加強其基礎理論與科研能力的培養,關注其研究成果的質量而不是數量。對于偏重新聞傳播實務的專業和方向,例如媒體實踐、媒體調查、大數據相關專業方向博士生,學界對“雙師型”師資建設的熱議由來已久,應著力搭建業界和學界共享共建的平臺,大力引進一線的高級記者、資深編輯進入博士生導師隊列,通過學、研、產三者的結合,給博士生以充足的實戰機會,同時開啟博士生導師團隊作業模式,師生共同在相關領域集中開展研究,攻克前沿議題,讓這類科研成果擔當業界的“參謀”與“指導”,同時接受來自業界的反饋與修正。對這類從事應用型/實踐類研究的新聞學博士,宜將其在學期間的實踐情況和科研成果的轉化情況納入考評體系,而不應僅僅看其在哪些刊物上發表了學術論文。也只有實現“術”與“學”的雙劍合璧,打通學界與新聞業界的現有壁壘,才是高層次新聞傳播實戰人才應對全媒體挑戰的必經之路。
參考文獻:
[1]關于加強新聞教育工作的意見(一九八三年八月)[M]//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中國新聞年鑒.北京:中國新聞出版社,1984:59-62.
[2]中國地質大學(武漢)藝術與傳媒學院.構建新時代中國新聞傳播學[N].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02-21(002).
[3]劉海貴,張帆.美日新聞教育及變革對中國的啟示[J].新聞愛好者,2013(3):72-74.
[4]復旦大學研究生招生官網[EB/OL].http://www.gsao.fudan.edu.cn/6f/90/c15014a159632/page.htm.
[5]華中科技大學研究生招生官網[EB/OL].http://gszs.hust.edu.cn/
info/1094/2649.htm.
[6]連晤琪.大數據背景下傳媒人才培養路徑探析[J].新聞愛好者,2018(7):72.
(艾紅紅為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韓文婷為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生)
編校:董方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