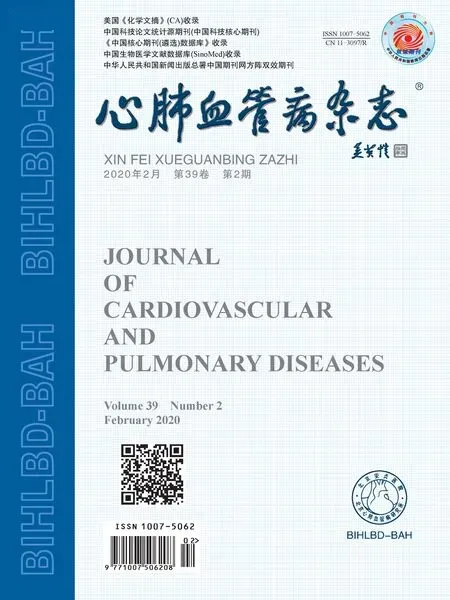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期間心血管疾病管理與診治策略
李 斌 劉愛軍 楊 明 范祥明 蘇俊武
1.新型冠狀病毒(nCoV-2019)流行病學
2019年12月初,1例患者在武漢市被診斷患有罕見肺炎[1]。接著從患者的支氣管肺泡灌洗液中采集樣本,基因組測序分析發現潛在病因是一種新型冠狀病毒,稱之為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nCoV-2019)[2]。WHO將該疾病正式命名為2019冠狀病毒病(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nCoV-2019是新型的人畜共患病冠狀病毒,屬于β屬的冠狀病毒。基因組測序發現蝙蝠冠狀病毒中有一個短的RdRp區域,稱為蝙蝠冠狀病毒RaTG13,而nCoV-2019在整個基因組中與RaTG13非常相似,整體基因組序列一致性為96.2%[2]。另外對比與SARS-CoV僅有79.5%的序列相似,與MERS病毒的同源性達到約50%,分析表明COVID-19與人類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SARS)和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相關的β冠狀病毒截然不同,而且2019-nCoV受體結合蛋白刺突(S)基因與其他CoVs高度不同,因此推測nCoV-2019來源于蝙蝠[4-5]。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六版)》[3]明確了其流行病學特點: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者是主要傳染源,無癥狀的感染者也可能成為傳染源;目前主要的傳播途徑除了呼吸道飛沫和密切接觸傳播外,最新新增一條即在相封閉的環境中長時間暴露于高濃度氣溶膠情況下存在經氣溶膠傳播的可能,糞-口傳播和母嬰傳播有待進一步證實;人群普通易感。根據臨床癥狀將患者分為輕型、普通型、重型和危重型。
早期的病例以中老年為主[4],后期亦發現兒童甚至嬰幼兒感染的病例。目前流行病學調查認為nCoV-2019潛伏期為1~14 d,多為3~7 d。對最早期感染的425例患者進行流行病學研究發現平均潛伏期為5.2 d(95%CI: 4.1~7.0),分布的第95個百分位數為12.5 d,根據此研究提出可以為暴露者提供14天的醫學觀察期或隔離[5]。
患者的典型臨床癥狀是發燒,干咳,乏力為主[4],少數可出現鼻塞、流涕、咽痛、肌痛和腹瀉等癥狀。患者常出現淋巴細胞減少,凝血酶原時間延長、乳酸脫氫酶升高等實驗室檢查改變。鼻咽拭子、痰和下呼吸道分泌物、血液、糞便等標本中檢測出新型冠狀病毒核酸即可明確診斷。感染患者常出現典型的胸部影像學改變:多發小斑片影或雙肺多發磨玻璃影,嚴重者出現肺實變[6]。重癥患者可在發病一周后出現呼吸困難和/或低氧血癥,嚴重者快速進展為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膿毒癥休克、難以糾正的代謝性酸中毒和出凝血功能障礙及多器官功能衰竭等。
2.nCoV-2019與ACE2
血管緊張素轉化酶II(ACE2)被稱為SARS-CoV14的細胞受體。為了確定nCoV-2019是否還使用ACE2作為受體進入細胞,Zhou等[2]使用了表達或不表達ACE2蛋白的人類,馬蹄蝠,貓,豬和小鼠的HeLa細胞進行了病毒感染性研究,結果顯示nCoV-2019能夠進入使除小鼠外的所有表達ACE2的細胞,而不含ACE2的細胞則不法進入,表明ACE2很可能是nCoV-2019進入細胞的受體,另外還對其他的冠狀病毒受體進行研究未見陽性結果。Xu等[7]也通過對新型冠狀病毒刺突蛋白進行建模來驗證nCoV-2019的受體,發現ACE2可能時該病毒的受體。已證實ACE2在人體的72個組織中均有表達,在肺組織中ACE2主要在I型(AT1)和II型(AT2)肺泡上皮細胞內有表達。Zhao等[8]對8例肺移植供體肺組織中的43 134個細胞分析發現,ACE2在所有肺細胞的中表達比例只有0.64%,大部分表達ACE2的細胞是AT2細胞(平均83%),其他還有AT1細胞,氣道上皮細胞,成纖維細胞,內皮細胞和巨噬細胞。與無表達ACE2的AT2相比,表達ACE2的AT2細胞內檢測到病毒復制相關基因的表達量明顯增加。雄性供體中表達ACE2的細胞比例明顯高于雌性(1.66%vs. 0.41%),ACE2的分布情況雄性也較雌性廣,這或許能解釋為什么大多數確診的nCoV-2019感染患者均為男性。還有一個有趣的結果就是亞洲捐獻者比白人和非裔美國人捐獻者具有更高的ACE2表達細胞比例(2.50%vs. 0.47%), 這也可能能解釋nCoV-2019和SARS-Cov爆發和擴散主要集中在亞洲地區的現象。
研究發現,ACE2對肺損傷具有保護作用,肺損傷時ACE2表達下調,肺部出現明顯的病理改變,炎癥指標表達明顯增加,而給小鼠注射ACE2后,肺功能和肺部病理損傷情況得到明顯改善,并伴有炎癥的減輕,細胞層面也得到同樣的結果。冠狀病毒(SARS)感染后,可通過其刺突蛋白(S蛋白)與ACE2受體結合進入細胞,然后下調ACE2,這被認為是引起肺損傷得始因[9]。對于ACE2基因敲除小鼠,出現了嚴重的ARDS/急性肺損傷的表現:血管通透性增加、肺水腫加重、中性粒細胞積聚、肺功能進行性惡化。
但是新冠肺炎與SARS不同,SARS起病急,肺部反應快且嚴重,而新冠肺炎初期往往癥狀較輕,后期出現肺部情況的快速惡化。研究發現因出現呼吸困難需要進入ICU治療的患者,相比與非ICU治療的患者ICU患者的血漿IL2,IL7,IL10,GSCF,IP10,MCP1,MIP1A和TNFα更高[4]。結合近期關于nCoV-2019感染者樣本的研究,推測新冠肺炎的發病機制可能是nCoV-2019通過ACE2受體感染后導致的一系列炎癥瀑布反應進一步加重了肺部的損傷。但具體的機制則需要進一步詳細的研究證實。
3.新冠肺炎疫情與心血管疾病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應急響應機制流行病學組對截至到2月11日中國內地所有COVID-19共計72 314例:確診44 672例(61.8%),疑似16 186例(22.4%),臨床診斷10 567例(14.6%),呼吸道標本病原學檢測陽性但無癥狀感染者889例(1.2%)病例數據進行流行病學描述和分析。在確診的病例中,大多數年齡在30~79歲間(86.6%),51.4%為男性,湖北省占74.7%,80.9%屬于輕/中癥,共1 023例死亡,粗病死率為2.3%,80歲以上年齡組死亡率最高為14.8%,男性死亡率為2.8%,女性為1.7%,未報告合并癥患者的死亡率為0.9%,有合并癥患者的病死率明顯升高,心血管疾病患者為10.5%,糖尿病為7.3%,慢性呼吸道疾病為6.3%,高血壓病6%,癌癥5.6%。其中1 716例醫務人員感染,死亡5例,粗死亡率為0.3%[10]。在上述數據死亡率占比中合并心血管疾病和高血壓既往史的患者占16.5%,因心血管疾病往往合并心血管急重癥患者(如:急性冠狀動脈綜合征,急性主動脈夾層動脈瘤,肺栓塞等),在治療時有黃金窗口期,但是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確診往往需要較長時間,因此對于合并心血管疾病患者在診療過程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應該如何決策,即在第一時間救治患者的情況保證診療過程和醫務人員的安全。
現綜合國內外發表文獻、已成文的國內專家共識和專家建議整理了心血管相關疾病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管理和診治策略的相關內容:
4.合并高血壓的管理和診治策略
ACE2的另一個主要功能就是在調節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RAS)中起負調節功能,其機制是ACE2將血管緊張素II(AngII)降解為血管緊張素1-7,從而抵消腎素引起的升壓作用。因此對于nCoV-2019感染患者合并高血壓時,治療變得棘手。世界高血壓聯盟前主席、中國高血壓聯盟終身名譽主席、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劉力生教授聯合國內外專家針對新冠肺炎合并高血壓的患者提出了治療上的建議:①輕型普通新冠肺炎合并高血壓患者,考慮停用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制劑(ACEI)、血管緊張素II受體拮抗劑(ARB)和利尿劑,改用鈣拮抗劑(CCB);②重癥新冠肺炎合并高血壓患者,應立即停用ACEI、ARB和利尿劑,改用直接腎素抑制劑阿利吉倫(aliskiren)和/或CCB;③危重型新冠肺炎患者合并呼吸窘迫或神經血管性水腫時,建議一線醫生選擇合適病例使用緩激肽(bradykinin,BK2)受體阻滯劑lcatibant;④直接腎素抑制劑阿利吉倫,服藥劑量與用法:150~300 mg,口服,每日一次;⑤已發生低血壓的新冠肺炎高血壓患者應停用降血壓藥物;⑥非新冠肺炎的其他高血壓患者應加強家庭自我血壓監測,按醫囑在醫生指導下繼續服藥,不要隨意改變原有治療方案或停用降壓藥物(圖1)。

圖1 劉力生教授等專家關于新冠肺炎患者的血壓管理建議(圖片來源于網絡)
而近期在《中華高血壓雜志》在線發表的題為“合并新型冠狀病毒性肺炎的高血壓患者能否使用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制劑/血管緊張素受體拮抗劑?”的文章[11],8位國內專家表達了不同的觀點。他們認為目前尚不清楚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后ACE2下調對高血壓患者在易感性、臨床表現和預后方面影響的差異。使用或未使用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RAS)抑制劑在感染風險、臨床分型和死亡率方面是否有差異?使用RAS抑制劑增加ACE2水平是保護作用更大還是損害作用更大?ACEI或ARB對ACE/ACE2平衡的影響有多大?他們認為這些問題還需要更多的基礎和臨床研究證實。對于在是否停用RAS抑制劑臨床和基礎研究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如果驟然停藥或換藥,可能增加其他風險,他們認為維持血壓的長期平穩控制是最重要的。并且還需要進一步比較用或不用此類藥物,以及停藥與未停藥患者新冠肺炎患病風險、重癥比率、急性呼吸窘迫、重癥心肌炎的發病情況等。而關于ACEI和ARB 能有效降壓和保護心血管系統的證據很充分。因此他們推薦: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高血壓患者仍應按現有指南接受規范化治療,包括繼續服用ACEI和ARB。合并新冠肺炎的高血壓患者應根據臨床分型、個體化的制定治療策略,對于輕型和普通型患者如果一直在服用ACEI或ARB,可以繼續使用,而重型和危重型患者應根據生命體征、血液動力學、靶器官損害等情況決定治療方案的選擇。從未使用過ACEI的新診斷新冠肺炎的高血壓患者,可避免使用ACEI,以免干擾對呼吸道癥狀的判斷。
5.合并急性冠狀動脈綜合征的管理和診治策略
急性冠狀動脈綜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是引起胸痛的常見原因之一,包括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STEMI)、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non S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NSTEMI)和不穩定性心絞痛(unstable angina,UA)。急性心肌梗死因發病急、致死性高、最佳救治窗口期短,因此治療需要爭分奪秒。但新冠病毒感染,因存在較長的潛伏期,送檢標本檢測確診所需等待時間長,可能導致患者錯過最佳治療時機。因此對于這部分患者的治療是心血管醫生遇到的難題。
這部分患者在治療時需要遵循以下五個原則。①就近原則:鼓勵急性心肌梗塞患者就近就診、原地治療,盡量減少患者轉運和人員流動。②安全防護原則:原則上伴有發熱等其他呼吸道癥狀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在發熱門診首診,若為疑似2019-nCoV感染病例則收入醫院隔離病房,待排除2019-nCoV感染后,方可轉入心臟監護病房。③溶栓優先原則:對于疑似或確診為2019-nCoV感染的患者,若合并STEMI,原則上應就地收入隔離病房,無溶栓禁忌證者優先選擇溶栓治療。有溶栓禁忌證的高危患者,評估感控風險后可在符合感控要求的指定隔離導管室進行介入治療,術后轉入隔離病房。導管室人員實行三級防護。④定點轉運原則:對于病原學檢測陽性的2019-nCoV感染患者,合 并急性心肌梗死,若心血管病情尚穩定,而以呼吸道癥狀為主的高危患者,原則上應轉運至當地衛健委指定的 定點醫院進行治療。⑤遠程會診原則:鼓勵各省、市、地區大型綜合性醫院心內科或心血管專科醫院啟動遠程會診、指導下級醫院或傳染病院等專科醫院的急性心肌梗死救治[12]。
胸痛中心總部于2020年2月10日共同發布了《新冠肺炎流行期間胸痛中心常態化運行專家共識》[12],共識中針對確診或疑似新冠肺炎患者合并STEMI和NSTEMI救治流程以及疑似新冠肺炎患者ACS患者需要急診PCI的流程做出了明確的說明。
(1)新冠肺炎患者合并STEMI救治流程 完全排除新冠肺炎的STEMI患者。可以按照胸痛中心的常規流程進行救治;但如首診醫院無法進行不具備PCI治療能力,應首選靜脈溶栓治療(盡量選用第三代溶栓藥物),盡可能減少轉運;
疑似/確診的新冠肺炎的STEMI患者。若發病在12 h之內,在首診醫院進行溶栓治療是首選。溶栓場所可在急診科或者發熱門診,并做好傳染病防護的二級最好三級防護下進行溶栓治療。溶栓治療成功的STEMI患者應繼續在隔離病房觀察。后續根據新冠肺炎診斷情況安排下一步治療方案,如排除新冠肺炎,則可轉入心血管內科擇期冠狀動脈造影;如確診為新冠肺炎,則轉診至定點醫院隔離病房安排后續治療。
針對溶栓失敗或者具有溶栓禁忌證的患者,須評估行急診PCI的獲益與醫患雙方所承擔的風險(醫護人員感染風險+患者的手術風險)比。如果風險大于獲益,或雖然PCI獲益較大但患者本人或家屬不同意手術,或者發病超過12 h且血流動力學穩定的患者則轉入隔離病房保守治療,進一步排查肺炎。如果獲益顯著大于風險且患者與家屬均同意手術,則進行急診PCI(圖2)。對于發病時間超過12 h但仍有胸痛癥狀或者血流動力學不穩定的患者,在平衡獲益-風險后亦可考慮急診PCI治療。

圖2 確診/疑似新冠肺炎合并STEMI時的再灌注治療策略(圖片來自《新冠肺炎流行期間胸痛中心常態化運行專家共識》)
(2)確診/疑似新冠肺炎合并非ST段抬高急性冠狀動脈綜合征(NSTE-ACS)的處理流程 在疫情期間,NSTE-ACS患者原則上在首診醫院以藥物治療為主,同時進行新冠肺炎的排查工作。若藥物治療難以穩定的患者建議轉診至本地既有冠心病介入條件又是新冠肺炎定點醫院進行診治。在評估NSTE-ACS患者時,需要根據診治指南進行缺血及出血危險分層,如果不是缺血極高危,或者即使是缺血極高危但同時合并出血高危因素,則建議在隔離病房進行保守治療;如果是缺血極高危且不具備出血高危風險,預期患者接受急診PCI治療的獲益顯著大于醫患雙方的總體風險,則建議在具備隔離條件且符合感控要求的導管室進行緊急PCI治療。術后如果確診為新冠肺炎,則在新冠肺炎定點醫院隔離病房進行后續治療,排除新冠肺炎者轉入CCU進行后續治療(圖3)。

圖3 確診/疑似新冠肺炎合并NSTE-ACS患者的診療流程圖(圖片來自《新冠肺炎流行期間胸痛中心常態化運行專家共識》)
(3)疑似新冠肺炎合并ACS患者進行急診PCI治療時必須權衡患者獲益與醫患風險慎重做出的決策 因新冠肺炎傳染性強,對防控要求高。一旦做出需要進行急診PCI的決策,除了遵循急診PCI的常規流程外,關鍵是做好感染控制工作,所有醫務人員應在傳染病防護的三級防護標準下進行操作(圖4)。醫護人員在圍術期有暴露風險者,應按照防疫規范實行隔離,一旦術后患者確診為新冠肺炎,建議該團隊醫務人員進行“醫學觀察”二周,觀察期間出現異常,及時上報并治療。建議具備急診PCI能力的新冠肺炎定點單位,在有條件的情況下,開辟專用導管室,統一管理,專門防護。
6.合并急性主動脈夾層的管理和診治策略
《新冠肺炎流行期間胸痛中心常態化運行專家共識》[13]中指出主動脈夾層的基本處理流程同上述ACS。因患者需要進行增強CTA檢查以確診和評估患者病情,因此對于疑似或者確診的新冠肺炎合并主動脈夾層患者,CTA檢查環節及運送環節均應在二級以上防護條件下進行。明確診斷為主動脈夾層后,根據主動脈夾層類型、生命體征及臨床表現是否穩定、所在醫院是否有具備外科/介入治療條件、是否為新冠肺炎定點醫院、是否有隔離手術室等綜合考慮后決定。詳細工作流程見圖5。若基層醫院在CT及CTA閱片時遇到困難,可通過胸痛中心區域協同救治體系建立的網絡遠程會診獲得幫助。
7.合并肺栓塞的管理和診治策略
《新冠肺炎流行期間胸痛中心常態化運行專家共識》[13]中指出對于急性肺動脈栓塞的救治,基本原則是盡可能依托具有CTA檢查條件的首診醫院完成全部診療過程,即使是高危的肺動脈栓塞,亦可在上級醫院的指導下進行溶栓治療。因此,原則上不應轉診。有溶栓禁忌證的高危肺栓塞患者,可以考慮參照ACS的急診PCI流程在嚴密防護下實施介入治療。
8.危重癥新冠肺炎患者體外生命支持-體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
隨著新冠肺炎患者的逐漸增多,重癥病例數量呈上升趨勢,死亡病例亦逐漸增多,主要原因為新冠肺炎重癥病例出現嚴重呼吸窘迫綜合征,甚至呼吸衰竭。根據國家衛健委制定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6版)[3]建議對于常規治療無效的危重型患者可采用ECMO作為挽救性治療。為了降低危重型肺炎患者的死亡率,指導ECMO在2019-nCoV引起的重癥呼吸衰竭中的應用,中國醫師協會體外生命支持專委會組織專家進行商議和統一標準,并發布《危重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體外生命支持應用時機及模式選擇的專家建議》[14]。內容涉及在新冠肺炎患者中使用ECMO的適應癥和禁忌證、使用ECMO治療的時機、ECMO模式的選擇。
新冠肺炎患者ECMO使用適應癥:危重癥型患者,即在發病一周左右出現呼吸困難和(或)低氧血癥,嚴重者快速進展為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并引起多器官功能衰竭。新冠肺炎患者ECMO使用(相對)禁忌證:合并無法恢復的疾病,如嚴重的中樞神經系統并發癥,惡性腫瘤晚期等;存在抗凝禁忌證,如新冠肺炎患者引起肝功能衰竭合并嚴重凝血功能障礙,大出血;在較高機械通氣設置條件下(FiO2>0.9,P-plat>30 cmH2O,1 cmH2O=0.098 kPa),機械通氣7天或更長時間;年齡:無特定年齡禁忌證,但考慮隨年齡增長死亡風險增加;伴有嚴重多器官功能衰竭;如果需要循環輔助行VA ECMO支持,主動脈瓣中-重度關閉不全,急性主動脈夾層也為禁忌證;藥物免疫抑制(中性粒細胞絕對計數<400/mm3);存在周圍大血管解剖畸形或者病變,無法建立ECMO血管通路。

圖4 疑似新冠肺炎急診PCI工作流程圖(圖片來自《新冠肺炎流行期間胸痛中心常態化運行專家共識》)
危重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有時病程進展較快,如果患者經過規范的ARDS標準治療仍然難以改善低氧狀態,在缺氧造成多器官損傷或呼吸機設置過高之前及時啟動ECMO。結合之前相關臨床研究及國際體外生命支持組織推薦建議,參考任何原因引起的低氧性呼吸衰竭(原發性或繼發性)ECMO時機,當患者死亡風險達到或者超過50%時,應考慮使用ECMO。當患者死亡風險達到或者超過80%時,啟動ECMO治療。在最優的通氣條件下(FiO2≥0.8,潮氣量為6 mL/kg,PEEP≥10 cmH2O),如果無禁忌證,且滿足以下條件之一即可啟動ECMO。 ECMO治療時機:PaO2/FiO2<50 mmHg(1 mmHg=0.133 kPa)超過3 h;PaO2/FiO2< 80 mmHg 超過6 h;FiO2=1.0,PaO2/FiO2<100 mmHg;動脈pH值<7.25 且PaCO2>60 mmHg 超過6 h,且呼吸頻率>35次/分;呼吸頻率>35次/分時,pH值<7.2且平臺壓>30 cmH2O;嚴重漏氣綜合征;合并心源性休克或者心臟驟停。
ECMO模式的選擇:根據輔助目的的不同,即病變器官的不同,ECMO主要有VV(靜脈-靜脈)和VA(靜脈-動脈)兩種模式。在新冠肺炎患者中,主要以呼吸功能障礙即呼吸衰竭為主,因此VV ECMO應作為首選模式,可采用股靜脈作為引流通路,頸靜脈作為灌注通路建立ECMO循環,右側股靜脈和右側頸內靜脈因走行相對較直作為首選。插管尖端應分別放在上、下腔靜脈與右心房交接的位置,避免再循環,降低ECMO的氧合效率。胸部X片或者經胸超聲可用于判斷插管位置。而當新冠肺炎患者在呼吸衰竭基礎上同時合并存在心源性休克或者出現心臟驟停時,可選用VA ECMO模式。一般選擇股靜脈和股動脈作為血管通路。經股動脈插管的缺點在于容易導致上半身缺氧,靜脈插管選擇頸內靜脈或股靜脈,將插管尖端置于右房中部可部分緩解上半身缺氧。如仍不能緩解,可以進行VAV ECMO輔助。VAV ECMO模式即在VA模式的基礎上,在右頸內靜脈再置入一根插管與ECMO動脈環路相連接,這種模式中動脈血液被分成兩部分,分別回輸到右心房和主動脈系統,相當于聯合了VA ECMO和VV ECMO在同一個環路中,同時提供心肺支持。
總之,對于疫情的防控,需要遵守“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科學指導、及時救治”的原則,盡量做到“早發現、早報告、早診斷、早隔離、早治療”,從而控制疫情傳播。國家發布的各防控方案和診療方案、不斷更新的疫情相關流行病學特點、專家們提供的心血管疾病相關的共識和建議等,為我們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能夠安全、有效的完成醫療救治工作,提高新冠肺炎患者救治率、降低病死率提供了很好的理論依據。另外希望醫務工作人員做好防護工作,保證安全,早日戰勝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