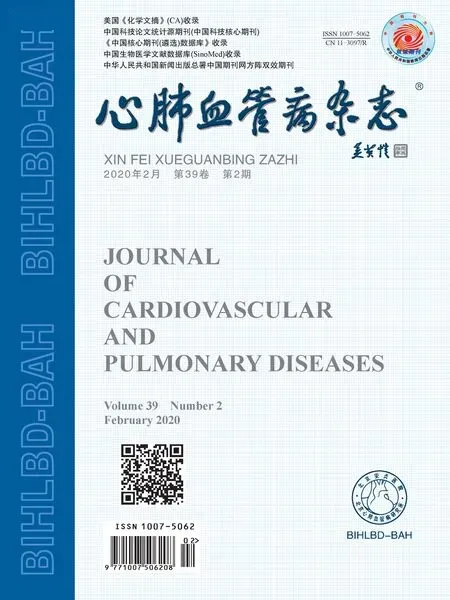胸部CT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診斷及治療中的應用
張 楠 徐勛華 李 宇 劉家祎 徐 磊
2019年12月初,中國湖北省武漢市發現了首例原因不明的肺炎病例[1],并迅速在中國及世界多個國家和地區傳播、爆發。中國的公共衛生、臨床和科學界迅速做出反應,通過高通量測序發現了一種新型β屬冠狀病毒,命名為2019新型冠狀病毒(2019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2-3]。2020年2月12日,世衛組織正式將由2019-nCoV引起的疾病命名為2019冠狀病毒疾病(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隨后1周內中國病理學專家通過手術和尸檢標本,闡釋了COVID-19肺炎患者肺部病理學表現[4-5]。
2019-nCoV是具有包膜的RNA冠狀病毒(肉瘤病毒亞屬,正冠狀病毒亞科)的第七個成員[3]。其基因特征與SARSr-CoV和MERSr-CoV有明顯區別。主要的傳播途徑是經呼吸道飛沫和密切接觸傳播。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長時間暴露于高濃度氣溶膠情況下存在經氣溶膠傳播的可能。體外分離培養時,2019-nCoV 96個小時左右即可在人呼吸道上皮細胞內發現[6]。
目前2019-nCoV感染患者的主要確診方式是通過收集鼻咽拭子、痰、和其他下呼吸道分泌物,通過實時熒光RT-PCR檢測2019-nCoV核酸陽性,或通過高通量病毒基因測序發現高度同源性。但是RT-PCR檢測的假陰性率較高,限制了感染患者的及時確診[7-8]。而COVID-19肺炎患者具有一定特征性的胸部CT影像學表現,可以發現RT-PCR檢測陰性,但肺部出現早期炎癥的患者[8-9]。研究表明,通過CT發現COVID-19肺炎患者的敏感性明顯高于首次RT-PCR檢測[7]。因此在一定時期內,胸部薄層CT 掃描圖像在湖北地區作為臨床診斷的主要證據[10]。僅2月13日一天,武漢通過胸部CT掃描增加了13 332例臨床診斷病例,為公共衛生監測和反應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近日發布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六版)》[6]取消了通過胸部CT做出臨床診斷的相關內容。但是CT結果仍然是對于COVID-19肺炎患者病程評價和治療效果評價的重要臨床依據,在COVID-19的疾病管理中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影像科和臨床醫生,需要正確認識COVID-19肺炎胸部CT,尤其是薄層CT的特征性影像學征象,及其與病理、臨床病程的關系,從而為COVID-19患者的篩查和治療提供準確的臨床影像信息。
1.輕型及普通型COVID-19肺炎患者CT影像學表現
COVID-19肺炎的CT表現與其他病毒性肺炎相比,缺乏特異性。由于患者年齡、機體自身免疫能力、基礎疾病的差異、以及發病時間的差別,CT影像表現具有一定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表現為不同患者間CT表現的差別,以及同一患者不同病灶間具有一定的差異。
目前已有多組病例研究,對COVID-19肺炎患者肺部CT影像特征做出了詳細的描述[11-15](表1)。常見的影像學表現包括:
(1)分布特點:多發病灶,常累及雙肺多個肺葉,胸膜下及肺外周帶分布更常見,下葉及背側受累居多(圖1)。
(2) 病灶密度特點:多數病灶表現為純磨玻璃密度影(GGO)及混合磨玻璃密度影。而單純實變病灶相對較少(圖2)。

圖2 患者52歲,男性,COVID-19患者胸部CT圖像 患者畏寒發熱一周,最高體溫達39 ℃。胸部CT軸位圖像顯示雙肺內多發彌漫性分布病灶,同時累及多個肺葉,及肺野的內中外帶。兩肺內病灶表現略有差異。右肺病灶內局部合并肺實變(細箭頭),病變邊緣模糊。病灶內部可見多發支氣管氣相,支氣管壁未見明顯增厚(箭頭)。GGO內可見多發細密網狀及小葉內間隔增厚表現(局部放大像),形似“鋪路石”樣改變
(3)“鋪路石”改變:指GGO病變內網狀影及小葉內間隔增厚表現,根據所處病程不同,這一征象出現的比例變化較大(圖2)。需要注意的是,此處“鋪路石”改變,并不等同于傳統意義上的“鋪路石征”。“鋪路石征”是指肺泡內異常物質沉積,合并小葉內間隔和小葉間隔增厚,常呈地圖樣分布,此時一個肺小葉為一塊“鋪路石”。此處的“鋪路石”改變通常僅存在小葉內間隔增厚,形成以小葉內間隔劃分的密集、微小的“鋪路石”。
(4)支氣管氣相:約80%患者病灶內可見支氣管氣相[13](圖2)。

圖4 男性,COVID-19肺炎患者胸部CT圖像 A:時胸部CT圖像顯示左肺下葉后基底段混合磨玻璃密度病變,密度呈現外高內低的反暈征,病變邊界清楚;B:抗病毒及對癥治療4日后復查病變范圍較前增大,病變密度增高,以肺實變表現為主;C:繼續治療3日后復查,病變密度明顯減低、吸收
(5)病灶邊緣:純磨玻璃密度影及混合磨玻璃密度影可表現為病灶邊緣模糊(圖2)。
(6)少數患者可伴有少量胸腔積液、心包積液(圖3)。

圖3 79歲,男性,COVID-19肺炎患者胸部CT圖像患者 咳嗽納差4 d,發熱1 d。入院時白細胞計數12.07×109/L,淋巴細胞計數0.68×109/L。A:入院時CT圖像表現為雙肺內多發磨玻璃密度影,累及多個肺葉,以雙肺中外帶分布為主,右肺病變累及內帶,部分病灶內有典型的“鋪路石”改變。B:治療10 d后復查,部分病灶吸收好轉(細箭頭),同時有新發病灶及少量肺實變出現(粗箭頭)。雙側胸腔內出現少量胸腔積液(星號)
(7)部分病灶可表現為反暈征(圖4)。
(8)肺空洞、淋巴結腫大和鈣化少見。
(9)病變進展:表現為新發病灶;或原有病灶范圍增加、相互融合、密度增高及實變范圍增大(圖3)。
(10)病變吸收:病灶密度減低,范圍縮小。最終可顯示為機化性肺炎的表現或條索影(圖3~4)。
2.COVID-19肺炎患者病理改變及CT典型影像學征象分析
2月16日首先公布了兩例合并肺腺癌的COVID-19患者的肺部病理改變,這兩例患者均接受肺葉切除術[5]。2月18日王福生院士團隊發布了首例COVID-19伴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RDS)患者的尸檢結果[4]。病理結果均顯示明顯的肺泡損傷,肺泡腔內伴有細胞纖維粘液樣或蛋白質樣滲出物,及炎性細胞、多核細胞。患者均有肺泡壁增厚,肺上皮細胞增生、部分脫落,間質內伴有炎性細胞浸潤,ARDS患者伴有肺透明膜形成。部分患者有局灶性機化和間質成纖維細胞增生。
(1)純磨玻璃密度影:2019-nCoV主要通過與ACE2受體結合實現細胞的入侵。ACE2受體在肺內的表達主要集中在II型肺泡上皮細胞上。早期出現肺泡壁及間質增厚、以及少量肺泡腔內滲出時,由于肺泡腔內仍有大量氣體充填,因此可表現為純GGO病變(圖5)。病灶吸收期,由于大量肺泡內滲出及間質內炎細胞的吸收,可再次表現為純GGO病變。

圖6 肺部病理圖片[4-5] A: 肺泡腔內大量滲出物充填; B:繼發ARDS,病理顯示為肺水腫合并透明膜形成時;C:肺泡腔內含氣量進一步減少,造成肺內病灶密度增高,表現為肺實變

圖5 肺部病理圖片[4] A:尸檢病理結果[4]顯示,COVID-19肺炎患者肺泡壁間質增厚,并炎癥細胞浸潤(箭頭),同時肺泡腔內可以有大量氣體。B: 胸部CT圖像(不同患者)GGO病變的產生是由于肺泡壁增厚,導致肺泡腔內含氣量相對減少,造成密度增高表現。同時,由于肺泡壁屬于小葉內間質成分,因此同時在薄層圖像上可清晰顯示為小葉內間隔增厚,呈網狀,形似“鋪路石”樣改變
(2)實變:GGO部分實變及完全實變表現,代表肺泡內大量細胞纖維粘液樣或蛋白質樣滲出物充填,合并部分肺泡塌陷。
(3)“鋪路石”改變:GGO病變內網狀影及小葉內間隔增厚,與肺泡壁及間質增厚的病理改變密切相關(圖5)。但當肺泡腔內滲出物持續增加、纖維化增加及肺泡塌陷時,“鋪路石”改變將不明顯。隨著病程的進展,肺泡腔內滲出物逐漸吸收時,“鋪路石”改變將再次出現。
(4)支氣管氣相:由于2019-nCoV主要入侵II型肺泡上皮細胞,支氣管上皮可有壞死脫落,但是管壁增厚并不明顯,管腔通暢,病理結果中炎性滲出物多集中于肺泡腔內,因此病變中可出現支氣管氣相。如果病灶內出現牽拉性支氣管擴張,提示病變機化、間質成纖維細胞增生、纖維化出現。
3.輕型及普通型COVID-19肺炎患者不同階段CT影像學表現
患者CT表現與病程密切相關,發現癥狀后5 d以上的患者,肺部CT圖像中可觀察到更多的實變病灶(431/712vs. 129/612,P<0.001)[13]。通過對21例輕型及普通型COVID-19肺炎患者多次肺部CT掃描(≥3次),動態觀察胸部CT表現后發現,從初診到痊愈期間,隨著病程的進展,胸部CT表現有明顯的變化,早期表現為胸膜下、單側或雙側肺下葉的GGO病變,逐漸發展為“鋪路石”改變及肺實變。大約在第10 d達到峰值,超過2周后,病灶逐漸吸收,殘留GGO和胸膜下條索,主要表現為四個階段[12](圖7),以66歲,女性患者,畏寒、發熱、咳嗽一周為例。
(1)早期(首發癥狀起病后0~4 d):在此階段,GGO是主要的影像學表現,分布在單側或雙側胸膜下。
(2)進展期(首發癥狀起病后5~8 d):在此階段,病變迅速加重并擴展至雙側多葉分布,此時多表現為特征性的彌漫性GGO、伴“鋪路石”樣改變,并開始出現實變的影像學表現。
(3)高峰期(首發癥狀起病后9~13 d):此期肺部受累面積緩慢增大至受累高峰。影像學以實變病灶為主。同時依然可以觀察到部分GGO病變、“鋪路石”樣改變、和吸收殘留的條索影。
(4)吸收期(≥起病14 d 后):炎癥控制,實變逐漸吸收,“鋪路石”樣改變消失。在這個過程中,仍然可以觀察到彌漫的GGO病變,是實變吸收的結果。吸收階段可以延長到超過26 d。

圖7 輕型及普通型COVID-19肺炎患者不同階段CT影像 A:第7天,雙肺下葉多發GGO病變,位于雙肺野外周帶及胸膜下區域,病灶內見“鋪路石”改變,對應早期向進展期過渡;B:第10天,雙肺病變密度增高,合并肺實變形成,部分磨玻璃密度仍可見“鋪路石”改變;C:第17天,雙肺病變出現多元化改變,部分區域病灶吸收,部分區域病灶密度繼續增高,并且出現纖維條索影,提示病變在進展過程中也在部分吸收;D:第21天,雙肺病灶逐漸范圍縮小,并演變為雙側胸膜下條狀影及索條影,提示整體進入吸收期
4.COVID-19肺炎重型及危重型患者CT影像學表現
截止成稿時(2020年2月28日),我國現存COVID-19確診病例40 000余例,其中重癥患者7 900余例,約占現存確診病例數的19.8%。據調查,我國住院患者重癥發生率為15.7%~31.7%[1, 16-18],全國整體重癥患者死亡率約為38.5%~49.0%[17, 19-20]。因此重型及危重型患者的治療是提高治愈率、降低全國總體死亡率的重要環節。CT在重型及危重型患者臨床治療評價方面能夠提供有效的信息。但目前尚無此類患者的CT影像總結。
本文初步總結10例2020年1月19日至2月8日,湖北武漢華潤武鋼總醫院收治的重型及危重型患者[6]的影像資料,所有患者均有最終治療結果。7例患者好轉出院,3例患者最終死亡。所有患者CT掃描均采用SOMATOM Definition AS+(Siemens, Healthineers, Erlangen, Germany)完成,獲得層厚及層間距8 mm的軸位圖像。
記錄病灶分布特點,包括單側或雙側發病、累及肺葉數量。將肺野均分為外、中、內帶,并記錄病變累及內中外帶的情況。記錄病變類型,包括純GGO病灶、GGO合并實變病灶、純實變病灶、“鋪路石”改變、條索影。評價病灶占肺葉體積百分比,及實變病灶占所有病灶體積百分比情況。記錄病灶內特征,包括支氣管氣相、小葉間隔增厚。記錄胸腔積液、心包積液、增大淋巴結(淋巴結短徑≥1 cm)及肺內基礎病變情況。由于樣本數量較小,數值變量結果不符合正態分布,因此數值變量通過中位數(四分位數范圍,IQR)表示。分類變量通過例數(占總數百分比)表示。
所有患者大部分為男性(7/10),中位年齡為74.5歲(51.3,77.5)。發現癥狀至入院中位時間為7.0 d(5.0,10.0)。9例(90%)患者有發熱癥狀,入院前最高體溫中位數為38.8 ℃(38.0,-39.2),其次最常見的癥狀為咳嗽、咳痰及乏力。5例患者既往存在高血壓、冠心病病史。實驗室檢查所有患者均表現為CRP增高,中位值:84.5 mg/L(46.2, 95.2)mg/L、淋巴細胞消耗,中位值:0.48×109/L,(0.39,0.94),見表2。
本組患者均為雙側多發病灶,所有患者5個肺葉均有受累。與輕型及普通型COVID-19肺炎患者不同,6例患者肺野內帶有病灶受累。4例患者病變占肺葉體積達51%~75%。所有患者均有典型的GGO病灶,并明顯的“鋪路石”改變及支氣管氣相,3例患者合并小葉間隔增厚。同時7例患者合并實變,實變占病灶體積從1%~75%不等,2例患者實變占所有病灶體積50%以上。4例患者出現胸腔積液,2例患者肺內有肺氣腫的基礎疾病表現。本組患者無心包積液及增大淋巴結表現(表3)。

表2 10例重型及危重型COVID-19肺炎患者一般資料[n(%), M(QR)]

圖8 胸部CT圖像 A~D:胸部CT顯示雙肺彌漫性磨玻璃密度病變,累及五個肺葉,病灶范圍占肺野90%以上。內中外帶及肺門旁均可見病灶累及。雙肺下葉背側胸膜下可見合并肺實變影(粗箭頭),占所有病灶范圍25%以下,病灶內見支氣管氣相。雙肺支氣管壁無明顯增厚。雙肺上葉見多發局限性肺氣腫(細箭頭)
以57歲男性COVID-19肺炎患者為例,患者咳嗽、咳痰伴發熱1周,入院體溫38.7 ℃,呼吸20次/min,SPO278%,氧分壓43 mmHg,氧合指數130 mmHg,符合重型患者標準。WBC計數2.83×109/L,淋巴細胞計數0.41×109/L(圖8)。

表3 10例重型及危重型COVID-19患者胸部CT影像表現[n(%)]
5.討論
自2019年12月初以來,短短不到3月的時間,COVID-19疫情在全國呈現蔓延、爆發趨勢,全國34個省市和地區均出現確診病例[19]。隨著全國各界的共同努力,病毒檢測方法的完善和豐富,目前疑似病例存量獲得了大量的釋放,新增確診病例數已經出現明顯放緩,但大量重癥患者仍然居高不下,每日新增死亡病例數依然較高。在繼續維持和加強疫情傳播控制及篩查工作的同時,重癥患者的有效治療逐漸成為臨床抗擊疫情工作的重要內容。
胸部CT在本次疫情抗擊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由于疫情初期缺乏準確的病毒檢測手段,通過傳統的口咽拭子采集樣本進行RT-PCR檢測假陰性率較高[7-9]。而胸部CT能夠早期發現COVID-19肺炎患者典型的病毒性肺炎的肺內征象,被臨床上廣泛用于疑似患者的篩查和檢出。并在一定時期內,作為臨床診斷標準,在湖北省的病例確診工作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0]。但是和其他病毒導致的肺炎相比,COVID-19肺炎肺內征象缺乏特異性,同時與心衰及肺內其他間質性病變表現具有一定重疊,因此僅通過CT進行確診,會產生一定的假陽性結果,因此在湖北省以外的省市和地區并不作為臨床診斷標準。研究表明,COVID-19肺炎患者肺內CT影像征象對于評價患者治療效果,能夠提供客觀的臨床信息[12]。因此,現階段胸部CT除了繼續發揮篩查和檢出疑似患者的作用,在疾病及患者治療管理方面也起著重要的臨床作用。
雖然由于個體差異和病程的原因,不同COVID-19肺炎患者間、同一患者不同部位之間CT影像均可以呈現出不同的影像表現。但仍然具有一定的規律和共性,包括病灶的分布、密度特點、典型的“鋪路石”改變等。目前輕癥COVID-19肺炎患者的影像學表現已經得到了詳細的描述,但重癥患者肺部影像學特征尚不明確。我們的經驗顯示,重癥患者相對于輕癥患者,病變累及范圍相對更廣,累及肺野中帶和內帶的比例相對更高,甚至累及肺門區域。同時初診時,肺實變的發生率更高。總結及觀察重癥患者胸部CT影像特征,對于臨床早期病情預警及監測、治療效果評價將會產生重要臨床價值。
目前已經發布了少量COVID-19肺炎患者肺部病理結果。隨著進一步病理研究的開展,臨床對于肺部病理表現的進一步認識,胸部CT征象的解讀將會更加準確、清晰。胸部CT在接下來的疫情抗擊過程中必將發揮更加重要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