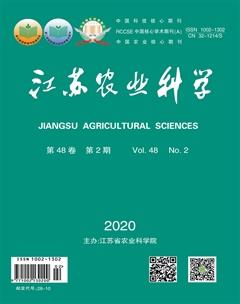內蒙古城市化-社會經濟-生態環境時空耦合關系
趙永峰 鄭慧



摘要:以內蒙古全區及9個主要城市為研究對象,構建城市化-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的評價指標體系,運用層次分析法、耦合協調度模型,定量測算了2003—2016年內蒙古的綜合發展值、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并對測算結果進行了量化對比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從時序的動態演變上看,2003—2010年,內蒙古城市化-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系統的耦合協調發展狀態經歷了較長時期的勉強協調過程,2012年開始實現中度協調。從空間分布上來看,鄂爾多斯、烏蘭察布于2003年最早實現中度協調狀態,其他城市則在2009年后先后逐步達到中度協調,2016年研究樣本城市全部實現中度協調。雖然2003—2016年這14年來內蒙古城市化-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符合系統的耦合協調發展水平不斷提高,但距離良好協調狀態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生態環境子系統和社會經濟子系統對城市化產生的制約作用影響顯著。
關鍵詞:內蒙古;城市化經濟生態;耦合協調;時空耦合關系
中圖分類號: F299.27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002-1302(2020)02-0287-07
收稿日期:2019-10-16
作者簡介:趙永峰(1980—),男,內蒙古包頭人,碩士,副教授,從事區域環境評價與管理方向的研究。E-mail:467980853@qq.com。
隨著近年來內蒙古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城市化的快速增長,資源利用規模持續擴大,工業污染和生活污染等也在迅速加劇,給生態環境帶來了巨大壓力,生態環境惡化和自然資源的減少,將會削弱地區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支撐能力,抑制城市化發展。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也提出了要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社會經濟建設的重要方向,把生態文明理念融入到城市化全過程,協同有序處理好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處理好現階段快速城市化進程與生態環境建設與保護的關系,已經成為內蒙古自治區走生態可持續發展社會主義道路,實現新型城鎮化建設目標的必然趨勢和現實選擇。在這樣的背景下,以內蒙古9個主要城市作為研究對象,構建了復合系統協調發展評價模型,依據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模型,以時空尺度定量分析和識別其協調發展的現狀及演化趨勢,剖析內蒙古城市化、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發展機制,探討和豐富城市化、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3個系統的交互耦合理論和耦合協調演變規律,持續推進健康有序的新型城鎮化進程,對于有效提升內蒙古城市化、社會經濟、生態環境質量與效率,貫徹并推動落實內蒙古自治區社會經濟發展思路,指導和實現生態環境優先發展的新型城鎮化建設有著重要意義。
綜合現有研究成果分析,大部分研究側重于從城市化與經濟發展[1-2]、城市化與生態環境[3-6]、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7-8]等2個系統之間的耦合協調狀況分析,而將城市化、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等3個系統納入同一研究范疇所進行的耦合協調關系實證研究較為鮮見。從現有評價模型構建情況分析,多數研究缺乏對于系統運作機制以及系統要素的充分挖掘,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和具體指標的選取不夠全面。從時空尺度上對于研究區域內耦合協調演化歷程及區域內空間對比分析的研究則更為少見。從具體案例的實踐應用層面來看,以內蒙古作為研究對象所進行的城市化、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3個子系統耦合協調定量分析屬于首次嘗試與探索。綜上所述,本項研究以內蒙古自治區作為研究區域,科學構建復合系統耦合協調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依據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模型,定量測算了2003—2016年14年間內蒙古的綜合發展值、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并對其主要9個城市的耦合協調發展演化過程進行動態時空對比與分析,以利于全面掌握內蒙古復合系統的耦合協調發展現狀與趨勢,以期為內蒙古自治區實現經濟持續穩定增長與生態環境健康有序協調的新型城鎮化建設提供理論支撐與科學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內蒙古自治區位于中國北部邊疆,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土地總面積118.3萬km2,2017年末常住人口為2 528.6萬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62.0%,全區地區生產總值為16 103.2億元,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為14 404.6億元,全年完成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為1 703.4億元,3次產業比例為 10.2 ∶39.8 ∶50.0,人均生產總值達到63 684元,城鎮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 670元,農村牧區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 584元。
1.2 數據來源
本研究以內蒙古自治區9個市(呼和浩特市、包頭市、烏海市、赤峰市、通遼市、鄂爾多斯市、呼倫貝爾市、巴彥淖爾市、烏蘭察布市)為研究單元,以2003—2016年間城市化、社會經濟、生態環境數據為研究對象,分析了2003年以來內蒙自治區9個城市的城市化、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交互脅迫關系和耦合協調變化特征。本研究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充分保證數據的權威性、真實性和可靠性。
1.3 評價體系構建
1.3.1 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城市化、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系統是一個由眾多要素所組成的層次結構復雜的巨系統,3個子系統的協調發展程度是由3個子系統之間復雜相互作用的綜合結果。建立科學完善的評價指標體系實現3個子系統耦合協調發展評價的基礎,依據PSR(壓力、狀態、響應)理論,遵循評價指標選取的有效性、科學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則,通過頻度統計和專家咨詢法對所建評價指標體系進行了嚴苛的篩選,同時充分結合內蒙古自治區的城市區位發展特點,分別構建了城市化、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系統評價指標體系(表1)。
1.3.2 數據標準化處理 本研究采用離差標準化數據處理方法對城市化、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使標準化處理后數據值均介于 0~1之間,以便于不同單位或量級的指標能夠進行比較和加權,
1.3.3 評價指標權重的確定 本研究采用主觀賦權評價法中的層次分析法進行指標權重測算。層次分析法是將系統研究對象分解為若干個目標或準則,然后分解為多指標的若干次級系統層次,通過定性指標模糊量化方法進而定量計算出層次單排序(權重)和總排序,達到多目標、多方案優化決策的系統方法。
1.3.4 綜合指數計算方法 經標準化處理后的數據及指標權重,按照線性加權模型Bi=∑mi=1wixi來計算綜合發展指數。式中:Bi為綜合發展指數,代表各個子系統的綜合評價得分;wi為指標權重;xi為標準化處理的值;m代表指標項數。
1.4 耦合協調發展度評價模型
物理學中關于“耦合”概念的解釋是指2個或2個以上系統或運動形式,通過構成系統元素之間各種相互作用而彼此影響的現象[9]。為了深入剖析城市化、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3個系統之間的耦合關系,參考廖重斌等提出的耦合模型[10],將耦合概念拓展為通過系統內部要素間產生相互影響及作用的現象,耦合協調具體計算公式定義為
1.5 耦合度與耦合協調度判別標準
本研究參考國內相關耦合度的判別標準,綜合耦合協調度的計算結果,將系統耦合度、耦合協調度設定為如表2、表3所示的等級劃分類別。
2 結果與分析
2.1 評價結果
首先根據耦合評價模型中的具體方法與步驟,分別計算得到2003—2016年內蒙古城市化-社會經濟-生態環境復合系統中的城市化綜合發展指數、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指數與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指數(表4)。然后在此基礎上根據耦合協調發展模型分別測算出2003—2016年內蒙古城市化-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符合系統的耦合協調發展狀況,結果見表5。根據協調發展水平度量標準,對內蒙古城市化-社會經濟-生態環境復合系統2003—2016年的協調發展的演化過程及主要城市的耦合協調發展水平進行了協調發展類別的劃分與判定。
2.2 內蒙城市化-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系統耦合協調發展時間變化分析
為了更直觀地對內蒙古城市化-社會經濟-生態環境復合系統的協調發展狀況進行綜合評價分析,將內蒙古自治區2003—2016年的耦合協調度測算結果繪制成折線圖(圖1),對內蒙古城市化-社會經濟-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演化趨勢進行綜合研判與分析。
內蒙古自治區全區整體耦合度、耦合協調度、城市化與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綜合評價指數等指標均呈現為整體波動上升趨勢,其中城市化綜合發展指數增長波動幅度最大,由0.145增長到 0.867,增長0.722,表現為內蒙古自治區全區整體城市化水平實現了穩步持續快速發展階段特征,體現為城市化發展優先于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快速城市化發展進程,這與內蒙古自治區全區近些年來的城市經濟快速發展實際情況相吻合。全區的地區生產總值由2003年的2.196×103億元增長到2016年的1.939×104億元,實現的地區生產總值7.83倍的快速增長,2016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達到2003年的12倍,2016年的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達到1.905×108萬元,相比2003年實現了14倍的增長速度,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城市化水平不斷提升,人民生活質量不斷提高,人均地區生產總值2016年達到9.20萬元,城市各項基礎設施建設、城市綠化覆蓋率等得到極大的改善。
內蒙古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卻未能實現與生態環境建設的協同發展,研究期內全區整體生態環境質量水平大致表現為“V”形曲線波動變化特征趨勢,全面反映出內蒙古自治區全區在社會經濟快速增長的巨大推動作用下,生態環境對其社會經濟的快速城市化發展產生了一定的響應,2003年全區生態環境質量最優,為全區社會經濟的快速城市化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態環境基礎,2003—2005年社會經濟整體發展水平不高,增長幅度相對較小,城市化發展進程滯后于經濟發展,自2005年以后,社會經濟波動運行發展,城市各項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投入也在逐年持續增加,帶動整體城市化綜合發展水平增長幅度加快。伴隨著快速的社會經濟發展進程,生態環境壓力持續增大,自然生態環境對于經濟發展產生了較強的負響應,表現出了顯著持續下降趨勢,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指數波動較大,其中2011年達到生態環境質量最低值,生態環境對于城市化表現出較為深刻的負向響應階段特征。與此同時,生態環境對于城市化也產生了消極的制約作用機制,上述研究結果充分說明復合系統子系統之間存在著極其復雜的交互作用。
內蒙古自治區全區綜合評價指數表現為波動增長變化趨勢,在研究期內增長幅度只有0.32,較為平穩。耦合度、耦合協調度水平時序變化特征表現為隨時間變化小幅波動上升趨勢,系統耦合過程隨年際變化逐步由拮抗階段(2003—2005年)、磨合階段(2006—2015年),向高水平耦合階段(2016年)演化,耦合度水平處在0.455~0.810之間,耦合度增長幅度不大,但耦合度得分隨年際波動變化而向更高水平耦合演化趨勢良好,內蒙古城市化-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系統將進入更高水平耦合發展階段。內蒙古自治區全區協調發展經歷了2003—2011年較長時期的勉強協調之后,于2012年開始轉變為中度協調階段,耦合協調發展度得分由 0.410 增長到0.773,得分增長0.363,增長速度及幅度較小,但耦合協調發展度得分隨年際波動變化趨勢良好,增長趨勢與耦合度年際變化趨勢較為一致,若內蒙古自治區社會經濟發展形勢能夠繼續穩定發展,并始終保持持續高增長態勢,充分注重全區城市化與生態環境的協同可持續發展,近年內全區耦合度、耦合協調度必然會向更高級階段的高水平耦合與良好協調階段發展。
2.4 內蒙古城市化-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系統綜合發展水平時空格局演變分析為了更清晰認識內蒙城市城市化-社會經 濟- 生態環境系統綜合發展水平時空格局演變特征,將內蒙古自治區2003—2016年耦合協調度測算結果繪制成折線圖(圖2至圖4),本研究選取2003年、2010年和2016年3個自然年份9個地級市的城市化-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系統做空間格局的演變過程分析。
從城市化-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綜合評價值的時序變化來看,內蒙古9個主要地級城市綜合評價指數、耦合度、耦合協調度等呈現波動上升態勢。2003年9個城市中有8個城市(除呼倫貝爾市)表現為生態環境優先發展、城市化滯后發展類型,各地級市社會經濟整體發展水平不高,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不足,城市各項基礎設施建設滯后,整體城市化水平不高,綜合評價值得分為介于 0.380~0.466的較低分值。隨著近年來各地級城市社會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地區城市生產總值穩步提升,大量的城市建設資金逐年投入到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與城市發展中,表現為快速城市化發展階段。從耦合協調類型的演化過程分析可知,2009年9個地級城市同時發展成為城市社會經濟超前發展型耦合系統,各城市經濟發展規模與效益逐年增強,逐步形成了基礎設施建設與生態環境治理的經濟
反哺良性循環,實現了城市化、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協同發展階段。2016年呼和浩特市、赤峰市、通遼市、鄂爾多斯市、呼倫貝爾市、巴彥淖爾市、烏蘭察布市等7個城市,發展為城市化發展超前型耦合系統,包頭市、烏海市發展為生態環境超前型耦合系統。
綜合對比9個地級城市城市化-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系統耦合度、耦合協調度的判斷標準,發現各城市之間存在較大差異,其中呼和浩特、烏海、赤峰、鄂爾多斯、烏蘭察布等5市耦合度過程只經歷了拮抗-磨合階段,且磨合過程長期持續;包頭市耦合度過程經歷了磨合-拮抗-磨合-高水平耦 合- 磨合-高水平耦合的復雜耦合度過程;通遼市耦合度過程表現為拮抗-磨合-拮抗-磨合;呼倫貝爾市耦合度過程表現為磨合-拮抗-磨合;巴彥淖爾市耦合度過程表現為拮抗-磨合-高水平耦合。2003年各地級市耦合度較低,包頭、呼倫貝爾屬磨合耦合階段,呼和浩特、烏海、赤峰、通遼、鄂爾多斯、巴彥淖爾、烏蘭察布等7市屬拮抗耦合階段。2010年內蒙古9個地市均表現為磨合耦合發展階段,這與9個城市的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緊密相關,經濟的快速發展促進了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城市生態環境建設資金投入逐年增加,表現為城市化-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系統較低水平的協同發展階段特征。2016年包頭市、巴彥淖爾市表現為高水平耦合,耦合度分別達到0.801、0.807,但仍處于高水平耦合階段的發展初期,而其余7個城市表現為磨合耦合度特征。
耦合協調發展情況涉及勉強協調和中度協調發展2種類型,9個地級城市的耦合協調發展水平呈現為緩慢波動上升趨勢,但城市之間存在較大差異,其中通遼市耦合協調度演化過程波動變化最大。2003年鄂爾多斯與烏蘭察布2市耦合協調度為中度失調,其余7市處于勉強協調階段。2010年中度協調城市增加為4個,分別為烏海、赤峰、鄂爾多斯、巴彥淖爾,其余5個城市處于勉強協調階段。2016年9個地級城市全部處于中度協調階段,耦合協調度得分排序依次為赤峰、巴彥淖爾、包頭、通遼、呼和浩特、烏蘭察布、鄂爾多斯、呼倫貝爾、烏海。其中赤峰、包頭、巴彥淖爾3個市的耦合度、耦合協調度均排名前3位,反映出這3個市在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進程中,不但充分注重城市基礎設施的城市建設活動,而且對于城市生態環境的改善也進行了全面提升,城市化-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系統始終處于協同發展過程中,表現為較高水平的耦合協調發展態勢。
3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以內蒙古全區及9個主要城市為研究對象,構建城市化-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的評價指標體系,運用層次分析法、耦合協調度模型,定量測算了2003—2016年內蒙古的綜合發展值、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并對測算結果進行了量化時空對比分析。結果表明,內蒙城市化-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系統協調發展水平呈不斷提高的趨勢,經歷較長時間尺度(2003—2011年)的勉強協調,2012年由量變轉化為質變提高到中度協調狀態。雖然全區整體協調發展水平持續提升,但距離達到和實現良好協調狀態仍然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間。綜合分析復合系統中各子系統的發展特征可知,內蒙古自治區得天獨厚的優良自然生態環境條件,為全區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提供了良好的資源環境基礎,但是,持續增長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對于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日益嚴重,生態環境對于城市化與經濟發展也產生了較強的負向響應,協調發展類型由過去的生態環境優先發展型逐漸演化發展為生態環境滯后型,生態環境的治理、建設與保護將會在較長時間尺度內成為制約復合系統協調發展的關鍵所在。
從空間分布上來看,內蒙古中部地區鄂爾多斯、包頭、呼和浩特3個市經濟發展狀況良好,呈現出強勁的增長態勢,長期領先全區經濟,這與呼包鄂經濟圈的區域協同發展密切相關,包頭市在2016年已發展成為生態優先發展類型,耦合度達到高水平耦合狀態,而呼和浩特與鄂爾多斯城市生態環境建設相對滯后,生態環境現已成為制約其經濟增長和城市化進程的較大阻力,耦合度長期維持在磨合狀態,今后的快速城市化過程中需要更加注重生態環境質量和效率的提升。內蒙古東部地區通遼、赤峰、呼倫貝爾3個市處于全區經濟發展第2集團,城市化進程發展較快,生態環境受經濟發展的影響波動,隨著城市化快速發展,生態環境壓力迅速增大,呈現為逐步下降趨勢,生態環境建設長期滯后于城市化進程,其中赤峰市城市化指數得分最高,但這一優勢并沒有提升復合系統的耦合協調發展狀態,脆弱的自然生態環境是制約赤峰市整體協調發展現狀的主要原因。內蒙古西部地區巴彥淖爾、烏海及位于中部的烏蘭察布3個市處于全區經濟發展最后集團,社會經濟整體發展水平不高,工業經濟發展不足,城市化進程長期發展滯后,生態環境建設與保護資金投入不足,導致系統整體協調發展狀況不高。
綜上所述,城市化、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之間存在著密切的相互驅動響應關系,其中社會經濟對城市化產生的驅動影響較大,生態環境是制約系統耦合過程向更高級階段演化的重要限制性因素。為實現內蒙古城市化-社會經濟-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全區各城市必須充分抓住國家西部大開發和“一帶一路”建設的良好契機,充分發揮各市的優勢資源,全面合理布局產業結構,推動產業轉型和技術升級,逐步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積極推進全區的生態文明建設,構建生態環境協同治理聯盟,加強城市及區域間的合作與共享,協同進行環境治理與生態修復,共建文明和諧生態大環境,持續推進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穩步提升城市化效率與質量,盡快實現城市化、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復合系統的優質高度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1]陳明星,陸大道,劉 慧. 中國城市化與經濟發展水平關系的省際格局[J]. 地理學報,2010,65(12):1443-1453.
[2]黃木易,程志光. 區域城市化與社會經濟耦合發展度的時空特征分析——以安徽省為例[J]. 經濟地理,2012,32(2):77-81.
[3]劉耀彬,李仁東,宋學鋒. 中國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度分析[J]. 自然資源學報,2005,20(1):105-112.
[4]黃金川,方創琳. 城市化與生態環境交互耦合機制與規律性分析[J]. 地理研究,2003,22(2):211-220.
[5]喬 標,方創琳. 城市化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動態耦合模型及其在干旱區的應用[J]. 生態學報,2005,25(11):3003-3009.
[6]方創琳,楊玉梅. 城市化與生態環境交互耦合系統的基本定律[J]. 干旱區地理,2006,29(1):1-8.
[7]王 靜,韓增林,彭 飛. 北方農牧交錯帶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分析[J]. 資源開發與市場,2014,30(4):430-433.
[8]丁金梅,文 琦. 陜北農牧交錯區生態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評價[J]. 干旱區地理,2010,33(1):136-143.
[9]馬 麗,金鳳君,劉 毅. 中國經濟與環境污染耦合度格局及工業結構解析[J]. 地理學報,2012,67(10):1299-1307.
[10]廖重斌. 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定量評判及其分類體系——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為例[J]. 熱帶地理,1999,19(2):171-177. 馬希龍,張小虎. 中國省域間糧食安全空間格局演化分析[J]. 江蘇農業科學,2020,48(2):294-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