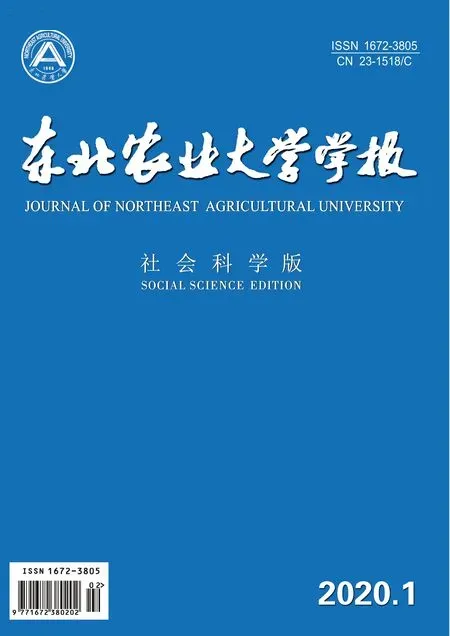飲食書寫與文化對話:高第丕夫人與《造洋飯書》的成書問題
[文]余文章(Yue Isaac)[譯]魏琛琳 趙力瑤 袁楚林
西安交通大學,陜西西安 710049
引言
在歷史上,中國人對西方烹飪的興趣可以追溯到清代初年(1644—1911),康熙皇帝(1661—1722)為滿足其對西方文化和風俗的好奇心,要求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利類思(Lodovico Buglio,1606—1682)和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āes,1609—1677)編撰《西方要紀》。在書中,他們用一整章展現西方各種飲食習俗與傳統。一個多世紀后,隨著中西文化對話不斷發展,對西方飲食習俗感興趣的國人不僅從宮廷王室擴展到文人群體,且將對西方飲食習俗的興趣從思想、理念付諸實踐體驗。從袁枚(1716—1797)的《隨園食單》和李化楠(1713—1769)的《醒園錄》即可看到此轉變。《隨園食單》詳述“楊中丞西洋餅”做法,《醒園錄》里出現“蒸西洋糕法”。這些作品不僅證實國人對西方美味佳肴充滿興趣,且表現出西方風味在一定程度上成功進入中國家庭、與中國本土飲食方式融合,并為諸如袁枚、李化楠等文人接受。
盡管中國人對西方食物興趣與日俱增,但第一部用中文撰寫的西方烹飪食譜直到1866年才出現,即《造洋飯書》(Foreign Cookery),由高第丕夫人(Martha Crawford,浸信會傳教士高第丕的妻子,1821—1902)編寫,此為西方人向中國讀者展示籌備正宗“洋飯”的最早嘗試之一。《造洋飯書》寫于高第丕夫婦作為美南浸信會成員第一次到訪中國至少十年之后,令人訝異的是它不僅在漢語世界并未得到太多學者關注,在西方學界也鮮為人知。在漢語世界,除了鄒振環、邱龐同和熊月之在討論中西文化交流時粗略提及此書(邱龐同在研究中國飲食時提及此書),其他值得一提的文獻還有夏曉虹2008年發表的、在晚清美食烹飪語境下探討《造洋飯書》的文章,以及于照州近來分析高第丕夫人筆下美食術語的文章。西方學界研究狀況更令人困惑:《造洋飯書》在相關研究中一直被忽略,即使小海亞特(Irwin T.Hyatt Jr.)、維恩·佛拉恩特(Wayne Flynt)和杰拉德·伯克利(Gerald W.Berkley)對19世紀阿拉巴馬在華傳教士展開兩種最具影響力的討論中,也完全未關注到高第丕夫人《造洋飯書》寫作①這兩種討論被廣泛認為是充分了解高第丕夫婦傳教生涯的文本,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篇文章均未提到《造洋飯書》,也未將其列入高第丕夫人的出版作品。。
鑒于高第丕夫人編寫的食譜篇幅較短,且尚無恰當英文譯本,因此其冷門和不為人知可謂不足為奇,但其重要性不容忽視。該書除對飲食和文化研究意義重大之外,還包含了高第丕夫人個人的觀點,為研究者探索食物和身份、文化政治之間的相互關系打開一扇窗口。為強調《造洋飯書》的文化重要性,本研究從三部分展開:第一部分對高第丕夫人成長經歷、當時美國南部飲食習慣,尤其全面考查其成長的阿拉巴馬州,以證明包括阿拉巴馬州在內海灣各州的烹飪傳統,不受美國其他地區影響,自成一格,并以此為理由,對《造洋飯書》中重要烹飪傳統的缺失提出疑問;第二部分探究19世紀初席卷歐洲的烹飪革命,以及此發展勢態對食譜撰寫和出版的影響;最后一部分將飲食理念作為階層和文化意識形態的載體,進一步闡明高第丕夫人編撰《造洋飯書》的動機。
一、高第丕夫婦
高第丕夫人于1830年出生于佐治亞州賈斯柏郡一個富裕的種植園主家庭,三歲時全家搬遷到阿拉巴馬州的塔斯卡盧薩,父親在那成為一位有名望的美國南部浸信會執事。她在提格(E.B.Teague,1820—1902)開辦的鄉村學校里接受早期教育,隨后就讀于阿拉巴馬州東部拉斐特市一所女子寄宿學院,兩所學校均以嚴格的宗教課程聞名。盡管宗教信仰一直是高第丕夫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但她并不向往成為一名傳教士。事實上,據其1846到1851年間的日記可見,盡管1845年9月在拉斐特浸信會教堂接受洗禮,但當時高第丕夫人對異性和浪漫愛情的興趣似乎遠超過宗教。盡管經歷幾次錯信和不忠實追求者造成的心碎,高第丕夫人也未立即將注意力轉向基督教。相反,在經歷了至少5次失敗的戀愛后,19世紀40年代末期回到拉斐特市的高第丕夫人,在日記中記錄下“對知識的強烈渴求”和“至少成為一個還算輕松的作家”[1]的決心——表明文學是她情緒低落時職業前景的第一選擇。但情況在1849年發生變化,當時高第丕夫人從前的老師提格正在克林頓工作,為她提供了一個主日學校里任教機會,此間她感到宗教的強烈召喚,還產生一種難以言喻的沖動去探索中國這個神秘的東方古國。
當高第丕夫人最終決定去中國時,恰逢《南京條約》剛剛簽定,為外國傳教士打開進入中國的大門。1850年,她正式向美國南部浸信會海外宣道委員會提出申請。盡管當時該組織僅成立五年,但在將傳教士派往中國方面已具備豐富經驗。但因高第丕夫人當時的未婚身份,委員會對未滿20歲的她遠赴中國的申請持保留意見。因此,有人提議她與恰巧在同一時間申請去中國傳教的肯塔基州的高第丕(Tarleton Perry Crawford)結婚,盡管她感到不太理想,但為了實現愿望還是答應下來。她與高第丕于1851年結婚,不到一年,他們就登上前往中國的海船。高第丕夫婦婚后生活很不順利,他們缺乏了解,高第丕性格刻板教條且易怒,很難相處。小海亞特評價高第丕“易與他人起紛爭、他毫無吸引力的社會哲學觀以及他拒絕對華人基督徒進行合理的領導力訓練”[2],闡明高第丕夫人在中國傳教中遇到的極大阻礙。實際上,在1870年,高第丕夫人一度發現情況十分令人絕望,便獨自踏上返回美國的航程,并考慮離開丈夫。但此后余生她一直支持丈夫的事業,有時甚至不顧自身興趣和傳教理念。如1883年她同意丈夫的請求,關閉了山東登州一所她辦學非常成功的中國兒童學校——這曾被她比作“斷臂之痛”[1]。盡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高第丕的對抗性人格,導致二人在中國傳教過程中過著相當孤立的生活,與一般僑民群體交流也十分有限。
當高第丕夫婦經過一段早已為當時航海者習以為常的漫長而艱苦的航程,于1852年首次抵達上海時,他們受到美國南部浸信會來華傳教士叔未士(Rev.J.L.Shuck,1812—1863)的接待,叔未士不僅在安頓高第丕夫婦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還幫助他們學習漢語。1863年,他們決定遷居山東登州(他們在那里完成全部職業生涯),一度依賴南浸信會來華傳教士海雅西(Jesse Boardman Hartwell,1835—1912)的盛情款待。當時來華傳教士家庭彼此之間往往關系密切,甚至發展為小團體,但沒過多久叔未士和海雅西就對高第丕夫婦喪失好感,海雅西甚至痛斥高第丕是“一個非基督教教徒和沒有紳士風度的人”[2]。實際上,高第丕和他的傳教士同事關系已惡化到一定地步,以至于在他職業生涯末期南部浸信會外國宣道委員會只能別無選擇地斷絕一切和他的聯系。在一系列事件中,高第丕夫人仍舊支持丈夫。
二、中國和阿拉巴馬烹飪
作為一名出色的語言學家,高第丕夫人中文水平(包括口語和書面語)遠超過她的丈夫。這讓高第丕心懷嫉妒并使她生活更加艱難。根據佛拉恩特和伯克利所言,高第丕夫人非常喜愛中國事物,在她旅居中國的48年中,從服裝到住宿,自始至終盡可能采用當地習俗,但卻固執地拒絕品嘗中國菜。據說是因一些“年長的傳教士告誡她中國菜不大有利于健康”[1]。高第丕夫人在1893年6月22日發表于《阿拉巴馬浸信會》(Alabama Baptist)的一篇文章中,講述其讓仆人準備飯菜時遇到的麻煩:
廚師是一個沒有經驗的、品性很好的年輕鄉下人,他從叔未士先生的仆人那里學到了一些東西,但他學得很慢,我經常發現自己陷入最令人困惑的兩難境地。有時當我們點了一樣東西,而來到桌前看到為我們準備的是另一樣東西,滑稽的錯誤會讓我們捧腹大笑[3]。
這些狀況無疑對她決定編輯并公開出版《造洋飯書》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文本內容和實質又是什么?揭示了中西語境中與高第丕夫人和食物書寫話語哪些內容?
人們普遍認為,高第丕夫婦在中國居住期間堅持拒絕中式飲食,僅吃習慣吃的食物。仔細閱讀《造洋飯書》,很容易發現事實并非完全如此。佛拉恩特和伯克利在關于高第丕夫人和美國在華南方傳教士的權威著作中引用了前文提及的1893年發表于《阿拉巴馬浸禮會》上的文章,宣稱“她試圖傳達美國南部烹飪口味的做法引發了一些滑稽的錯誤,當他們來到餐桌前發現等待他們的東西時,這些錯誤有時會讓他們捧腹大笑”[1]。事實上此文并未提到她當時嘗試的烹飪風格(美國南部或其他地方),證明這種推定實為過度解讀②佛拉恩特和伯克利在他們的著作中未提及《造洋飯書》,因而不確定他們是否注意到了這本書的存在。。
很容易發現誤解源自哪里。在十九世紀,阿拉巴馬州因其獨特烹飪風格而聞名,這種風格在傳統上更接近法裔美國人/法裔混血而非英國人。有關于此的證據可在諸如《海灣城市烹飪書》(Gulf City Cook Book,1878年)一類的當代出版物中找到,在這些出版物中,人們可以發現諸如海鮮濃湯、什燴飯、鴿子、香飯和南方炒飯等熟悉的食譜——源于法裔美國人/法裔混血的食物,至今仍被認為是阿拉巴馬烹飪菜品的代表。
通過《海灣城市烹飪書》可發現高第丕夫人的飲食背景,原因有三。一是地理相對性:《海灣城市烹飪書》1878年在阿拉巴馬州的莫比爾市寫作并出版,莫比爾位于塔斯卡盧薩以南大約280公里處。由于莫比爾是阿拉巴馬州唯一的咸水港,塔斯卡盧薩商人常去那里購買食物和其他日用品。地理優勢使莫比爾成為整個南部地區的文化中心,包括塔斯卡盧薩在內的周邊城市均把關注投向莫比爾,以尋求社會和美食方面影響。二是時間上接近。《海灣城市烹飪書》出版于1878年,約比《造洋飯書》晚10年,距高第丕夫婦啟航前往中國不足30年,在相對較短的時間段里,阿拉巴馬人烹飪習慣不可能有太大改變。換言之,可以肯定的是,在高第丕夫人去中國之前,即便她不喜歡《海灣城市烹飪書》中提到的食物,也一定知道其存在。第三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是這兩本烹飪書作者的宗教背景。盡管《海灣城市烹飪書》作者不詳,但作者宗教信仰卻清楚表明其身份為阿拉巴馬州莫比爾市的“南部圣弗朗西斯街衛理公會女教友”。據佛拉恩特所言,“因為大多數浸信會教會一個月才聚會一次,所以教徒們經常在自己的教堂不開會的時候去衛理公會或長老會教堂。”[4]一個教派成員愿意參加另一教派的儀式,證明阿拉巴馬浸信會教徒和衛理公會派教徒之間存在緊密聯系,可得出結論:兩個群體經歷和價值觀較為相似。因此,即使考慮宗教對烹飪習慣的影響,也沒有理由排除《海灣城市烹飪書》是高第丕夫人對自身飲食偏好的適當反映。
鑒于高第丕夫人在飲食方面的成長背景,《造洋飯書》中沒出現阿拉巴馬州的招牌菜相當令人驚訝。然而,本土菜的缺席并非《造洋飯書》的唯一特點;高第丕夫人似乎有意選擇了英國中產階級美食話語作為原型,這在其食譜的整體布局中顯而易見。
三、《俄式上菜法》(Service à la Russe)與維多利亞美食革命
在工業革命時期,一場規模較小的革命同時發生在英國餐桌上——日益繁榮的中產階級在選擇晚餐服務時以俄式上菜法取代法式上菜法。采用法式上菜法的宴會中,所有菜品均是一次性端上桌,甜點和開胃菜出現時間并無差別。法式上菜法在維多利亞時代到來之前是一種流行選擇。這種上菜法鼓勵客人自己動手,他們通常站立選擇喜歡的食物。相較而言,采用俄式上菜法時,每位客人根據特定位置就座,由仆人一道接一道端來。座位安排和上菜順序均被周到考慮。這種做法起源于俄羅斯,很快傳播到倫敦和歐洲其他地方,并成為一種禮節,它關注細節,從每次服務時間到特定刀叉的擺放等。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到后來延伸到食譜編寫的思維方式。
《比頓夫人的家政管理手冊》(Mrs.Beeton’s Book of Household Management,1861)即是恰如其分的例子——此書是維多利亞時代烹飪書的黃金標準,至今仍被認為是“家政圣經”[5]——其展示的第一個食譜是湯,然后是各種肉類、蔬菜和糕點,最后是蛋糕和飲料,此呈現順序并非偶然。現代讀者可能會發現這種行文布局十分熟悉,二十世紀的烹飪書大多遵循此鋪排,這一特殊排列次序源于俄式上菜法的服務順序,其在《比頓夫人》等文本中出現,顯然是出版商利用頗受中產階級歡迎的俄式上菜法盈利的一種嘗試,因此類文本主要消費者便是中產階級。
為了深入說明俄式上菜法的興起和維多利亞時代烹飪書慣例化之間關系,可以對比研究維多利亞時代之前的烹飪書。蘇珊娜·卡特(Susannah Carter)的《節儉的家庭主婦或女廚師》(The Frugal Housewife,or,Complete Woman Cook,1765)即典型例子。《節儉的家庭主婦或女廚師》早在俄式上菜法傳入的大約十年前出版,與《比頓夫人》相反的是,其專門迎合工人階級女性口味,提倡節儉而非奢侈的飲食方式。盡管像《比頓夫人》一樣,《節儉的家庭主婦或女廚師》將其食譜分為“湯”“派”和“蛋糕”等類別,并據此類別設置章節標題,但內容呈現順序似乎較為隨機,沒有特定原則,如圖1所示。

圖1 《節儉的家庭主婦或女廚師》食譜
此外,正如某些章節標題所示,此書分類方法似乎未遵循任何特定模式。一些章節根據烹調方法分類,如“烘烤”“煮”和“煎”,另一些根據食物類型編寫,如“排”“糕餅”和“樸定”。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式用餐禮儀中,菜單有特定的排序方法,先湯后肉,最后才是甜點,《比頓夫人》的排序方法與這套禮儀幾乎完全吻合。相比之下,《節儉的家庭主婦或女廚師》編寫方式就顯得隨機一些。透過兩本食譜編撰風格和外在呈現方面的差異,可以看出俄式上菜法對維多利亞時代食譜印刷文化的廣泛影響,這種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
相比之下,十九世紀中葉的美國食譜類作品并未采用此種編撰樣式,說明俄式上菜法在美國大眾中并無如在歐洲般的歡迎和反響。事實上,這一觀點可在1869年《上流社會的習慣:先生和女士們的指南手冊》(The Habits of Good Society:A Handbook for Ladies and Gentlemen)文本中得到進一步證實。在標題為“晚餐、用餐者和晚餐聚會”的章節中,建議讀者按照以下順序上菜:
1.湯
2.魚
3.餡餅(牡蠣餡、龍蝦餡、蝦肉餡或小牛肉末餡)
4.包括家禽在內的前菜
5.烤肉或主菜
6.蔬菜
7.野味
8.糕點,布丁和煎蛋卷
9.冰凍甜食
10.甜點[6]
盡管此書未專門提及“俄式上菜法”一詞,但上述就餐順序與俄式上菜法順序驚人相似,表明這種上菜方法已在歐洲普及。事實上,作者進一步指出此方法“不論在英國還是法國均未得到嚴格地遵守”[6]的觀點可能只是一種錯誤判斷(《比頓夫人》相當清晰地證明了它在西歐的流行),或僅嘗試用較隨意的語氣強調對此方法的推介。無論何種方式,此章節在1869年發表證實俄式上菜法在北美地區仍是非常新奇的理念,就飲食習慣而言,歐洲用餐者要超前于美國。
以上如此詳細羅列俄式上菜法在歐洲和北美接受時呈現的差異,原因在于《造洋飯書》章節布局與《比頓夫人的家政管理手冊》異常相似,以至細節方面兩個文本均以討論管理廚房的基本原則為開頭。表1是對《造洋飯書》和《比頓夫人》在章節鋪排方面的比較③為清楚起見,表格中省略了《比頓夫人》中沒有食譜的一些章節,只涉及特定類型食物的歷史,如第七章“魚類的自然歷史”,它出現在第八章有關魚的食譜之前。除了有關廚房和仆人管理的章節(也被省略了),《比頓夫人》中幾乎所有章節均遵循此種模式。:
除了“醬料”“各式腌菜”和“油酥點心與布丁”部分,還可在《造洋飯書》和《比頓夫人》章節設置之間找到明顯相似之處。鑒于美國,尤其是阿拉巴馬州,并不流行俄式上菜法,這就引出一個有趣的問題:前者(或另一個類似文本)是否被后者用作原型加以參考?

表1 《造洋飯書》和《比頓夫人》章節鋪排比較
四、作為譯本的《造洋飯書》
可以更加詳細地思考這種可能性。高第丕夫人旅居中國多年,她驚人地從始至終保持寫日記的習慣。奇怪的是《造洋飯書》只在日記中出現一次,似乎是其事后回想。唯一一次出現在1865年,當時高第丕夫人提到她為出版商準備了文本。她承認:“我從三本英文書中挑選我最愛的食譜,幾乎囊括了烹飪的所有門類。”[7]可見,與其說《造洋飯書》是一部原創作品,不如將其視為三本不同原著的合譯。盡管高第丕夫人從中選取菜譜的“三本英文書”從未被確定,但考慮到《比頓夫人》的強大影響力,很可能是高第丕夫人引用的三本書籍之一,另一本可能是索耶(Alexis Soyer)的《當代家庭主婦或管家》(The Modern Housewife:Or,Ménagère)。索耶是倫敦改革俱樂部(the Reform Club)主廚,他炫耀賣弄的個性使一些人認為其為世界第一名廚。兩本書在當時非常暢銷,最有可能在地球另一端被發現、最有可能成為高第丕夫人的引用對象。然而,事實真相卻是高第丕夫人幾乎不可能參考這兩本書。在三個文本中各自對牛肉排(維多利亞時代食譜中的主食之一)的說明中即可看出。
《當代家庭主婦或管家》
挑選兩磅的牛臀扒,切成厚度為半英寸的薄片,用胡椒粉和鹽腌制,之后每片均勻裹上面粉,頂部拱成圓頂狀裝在小餡餅盤里,加入一酒杯的水,接下來準備一磅半發的面團,切下一小塊卷成環狀放在盤子邊緣,先用蘸水的面粉刷將其沾濕,然后將面團另一塊卷成盤子大小,將它放在打濕的面團上面,再用刀在其頂部挖洞,用拇指均勻壓邊后將多余部分切下,使這塊派成為一個圓形,并用面粉刷輕蘸雞蛋液均勻涂抹其表面,可根據喜好用面團的切邊裝飾它,最后再調至中火在烤箱中最好烤一小時以上,取出后不論是立即食用還是冷食均風味奇佳[8]。
《比頓夫人》
挑選一塊從風干過的牛臀肉切下的牛排,經過排酸,牛肉口感變得愈發柔軟且有回甘。將其切為長約3英寸、寬約2英寸牛排塊,每塊瘦肉上放一小塊肥肉,然后將肉分層放入餡餅盤中,在每層之間撒鹽和胡椒,如果喜歡的話,還可撒幾粒紅辣椒。在盤中放入足夠多的肉來填充面包的外皮,這樣就能在烘烤時形成漂亮的拱形品相,而不會看起來像癟了的氣球一樣。倒入足夠的水沒過盤子中間后,用面團將周圍糊住(見糕點);刷一點水后蓋上蓋子,用拇指輕輕壓邊,根據盤子形狀將露在外面部分剪去。根據喜好用葉子或任意形狀的面團裝點餡餅,接下來刷上蛋黃液;在面包皮頂部鑿一個洞,最后在烤箱中烤大約1至1.5小時[9]。
《造洋飯書》
牛肉排,照煎樣片、打,熏十分鐘之后取出,切成小長塊,用鹽豬肉三四塊,熏一熏。先用三分厚面餅鋪在深盆內,后拿牛肉豬肉放在盆內,加奶油、鹽、胡椒或酒,或番柿醬,燒熱水,略比肉淺一點,撒些干面在內,用一片面餅蓋之,上開一口,烘。羊肉排,亦照此做法[7]。
可見,《造洋飯書》中菜譜與《比頓夫人》和《當代家庭主婦和管家》中菜譜存在很大區別。在高第丕夫人食譜中,需更多食材(培根、番茄醬和黃油)——從“烤兔肉”到“蘋果餡餅”,《造洋飯書》中大多食譜均需較多食材。這一點值得注意,由于當時中國普遍缺乏西方食品配料。1905年到1936年在山東工作的一名路易斯維爾(美國肯塔基州城市)浸信會傳教士護士(在高第丕夫人去世后接替其工作)米勒(Cynthia Miller,1868—1939)在1919年記述:她為了獲得新鮮牛奶不得不到附近一個飼養了少量奶牛的德國人社區購買[10]。
這說明什么呢?首先,這有效排除了高第丕夫人查閱暢銷書籍的可能性,更不用說翻譯了。加上諸如源文本的可查閱性和當地食材的可獲得性等因素,表明便利性在其選擇食譜時已非首要考量要素,她選擇食譜更多基于自己飲食偏好。其次,《造洋飯書》中缺乏阿拉巴馬州食譜,但此情況顯然與中國缺乏阿拉巴馬烹飪食材關系不大;相反,俄式上菜法明顯影響《造洋飯書》章節布局,再次表明高第丕夫人故意從自己本土烹飪傳統轉向英國中產階級食譜研究,創作出《造洋飯書》。
五、咖喱和英國帝國主義
《造洋飯書》最具獨特性的地方之一即內容包含一篇咖喱食譜(高第丕夫人將其翻為噶唎),這與英國中產階級話語相悖。
任何一種肉類均可用來制作噶唎,但最常用的還是雞肉。將雞肉切成塊并徹底煮熟。隨后將雞塊放入烹飪鍋中,加入高湯和黃油煮沸。混合以下成分:一個中湯匙噶唎粉、半茶匙米飯,一大勺面粉和一大勺黃油,一茶匙湯料以及小半勺鹽。將它們倒在雞肉上,再次燉煮至沸騰,搭配米飯一起食用[7]。
如《造洋飯書》中其他食譜一樣,高第丕夫人關于制作咖喱的說明并未試圖適應所在地原材料短缺的情況。黃油由牛奶制成,且需定期深加工。采購牛奶尚存問題,即能想象獲得黃油有多困難。但在《造洋飯書》中,一半以上食譜(總共271種)需用到黃油,高第丕夫人并未妥協于當時中國原材料不足的問題,而是繼續使用黃油煎肉(相較而言,在中國被廣泛使用、與黃油具有同樣功能的食用油卻未被提及)。這再次說明《造洋飯書》本質是翻譯文本,不能用于說明目標文化的本土環境。
但除了食譜中列出的配料外,高第丕夫人將咖喱食譜也加入書中,表明她傾向采用英國美食。作為一道以辣醬為基礎、起源于印度次大陸的菜肴,咖喱在維多利亞時代的烹飪話語中可能被視為某種悖論。一方面,與傳統牛排餡餅和烤羊肉不同,咖喱起源于亞洲,其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廚房里絕對是一道外國菜;另一方面,正如蘇珊·茲洛特尼克(Susan Zlotnick)所言,十九世紀初,當東印度公司的英國官員休假期間一個接一個回國時,他們對咖喱產生極其大熱情,“到本世紀中葉,咖喱已成為都市資產階級家庭烹飪的主要內容。”[11]咖喱的“英國化”程度不僅體現在咖喱食譜出現在諸如伊麗莎·阿克頓(Eliza Acton)的《現代私廚烹飪》(Modern Cookery for Private Families,1845)、查爾斯·埃爾姆·弗朗卡特利(Charles Elmé Francatelli)的《當代廚師》(The Modern Cook,1845)等暢銷書籍中,連1851年出版的當代英國烹飪書《比頓夫人》甚至提及咖喱“已經完全異化了,如果餐桌上沒有咖喱,人們就會覺得這頓飯不完整。”[12]更重要的是,這種發展和變化并不局限于家庭,《名利場》(Vanity Fair,1848)作者威廉·梅克比斯·薩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甚至在《笨拙周報》(Punch)中專門為歡迎這道菜作了一首詩[13]。早在1809年,東印度公司一位退休孟加拉軍官凱撒·迪安·穆罕默迪(Sake Dean Mahomet,1759—1851)在倫敦波特曼廣場創立印度斯坦餐廳(Hindoostanee Coffee House),此為印度之外開設的第一家印度菜餐廳④雖然印度斯坦餐廳被公認為是第一個在印度之外提供咖喱的餐廳,但根據NupurChaudhuri說法,咖喱的歷史可追溯到1733年倫敦的餐廳,諾里斯街頭咖啡館據稱在干草市場開始為顧客提供咖喱。有關信息請參見NupurChaudhuri《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披肩、珠寶、咖喱和大米》(“Shawls,Jewelry,Curry,and Rice in Victorian Britain”)。。盡管未能成功,默罕默迪在1812年不得不宣布破產,但咖喱卻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成為寶貴遺產,且以一間又一間供應咖喱的餐廳出現,印度廚師和仆人的人手從不短缺⑤1887年,AbulKarim成為第一個在白金漢宮直接為維多利亞女王工作的印度人。他被認為是將咖喱引入皇家菜譜的功臣。,以及咖喱粉逐漸商業化[14]等方式得到保護。
相比之下,盡管一些十九世紀美國食譜如瑪麗·蘭道夫(Mary Randolph)的《維吉尼亞家庭主婦》(The Virginia Housewife,1824)和艾比·費舍爾(Abby Fisher)的《費舍爾夫人的古老南方烹飪手冊》(What Mrs.Fisher Knows about Old Southern Cooking,1881)等均包含咖喱食譜,但大多數書中卻未出現咖喱的蹤影(包括暢銷書籍《節儉的家庭主婦》和《偉大的西方烹飪書》(The Great Western Cook Book,1851),美國不象英國那樣曾經統治過印度這一咖喱的發源地。如1847年查爾斯·霍夫納格(CharlesHuffnagle)曾在加爾各答擔任美國領事,他回到賓夕法尼亞州新希望市斯普林代爾后,把自己的家變成一個私人博物館,婆羅門牛、狩獵戰利品、書籍和家喻戶曉的圣像均成為其藏品。不管游客何時來參觀,霍夫納格均提供或出售加爾各答的結晶糖、摩卡咖啡和稀有的阿薩姆茶,但從未提到咖喱[15]。再次說明,與英國相比,在十九世紀的美國咖喱并不流行。
六、結語
從篇章布局到對咖喱食譜編錄,貫穿《造洋飯書》的英國中產階級話語明顯。需提出的問題是,為什么高第丕夫人決定放棄談論自己家鄉美食,而去編撰一本表面上迎合他人飲食傳統的食譜?盡管高第丕夫人在1846年至1881年間創作了七卷日記,但可惜的是,眾所周知她日記中幾乎只字不提個人生活。日記內容主要集中在傳教上,很少透露她的個人觀點。因此,除非有新證據被發現,否則僅有可供參考的少量文獻,難以真正了解其編纂《造洋飯書》動機。
然而,問題可能有個簡單答案,即高第丕夫婦經濟狀況。事實上,在十九世紀到中國的所有傳教士中,高第丕夫婦的情況較為獨特,他們從未正式成為某個宗教協會的一部分,他們與南部浸信會外國傳教委員會關系持續惡化,最終在1892年被開除。他們與包括叔未士和海雅西在內的其他美國浸信會傳教士關系最初友好,但很快冷淡,因此只能憑借自己支撐在中國的活動。令人驚訝的是,高第丕夫婦很擅長在傳教工作之外賺錢。如在十九世紀60年代初,上海被太平天國軍隊圍攻長達10年。在搬到登州之前,高第丕夫婦一反常規,決定斥巨資購買當時沒人想要的、飽受戰火侵蝕的房產,這在當時是令人不可思議的舉動。如小海亞特所言:
在18個月里(1862—1863年),他賺了6 600美元,[高第丕]將這些錢再次用于投資當地土地。然后把這些土地出租,租金加上他和妻子作為傳教士的工資,總共能給他們帶來每年3 000美元的收入。即使不是發大財,但這也一定是一筆意外之財了;這是高第丕夫婦僅做傳教士的收入的三倍,這筆錢使他們能夠過上美好體面的生活,并擁有了不同尋常的獨立性[16]。
高第丕夫人在1864年一篇日記中對事業的成功表達了明顯的喜悅之情,稱他們現在能夠享受“沒有教會的支持也可以過得很舒服的生活”[17]。因《造洋飯書》寫于同一時期,可想而知高第丕夫人將此書創作視為另一個盈利機會。而十九世紀在中國的英國中產階級人數眾多,很容易做出把受眾定位為英國中產階級的決定。
不論《造洋飯書》出于何種創作動機,其影響不可低估。在1866年至1909年間,上海美華書局至少將其再版三次。盡管確切印刷數量不得而知,但四版發行即使對當代商業出版社而言也是相當可觀的數量。表明該書銷售量遠超高第丕夫人預期受眾(中國僑民群體)的增長速度。換言之,令人驚嘆的銷售數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國讀者的巨大興趣支撐,也是中西交流史上一個重要事件。奇怪的是,盡管此書享有盛譽,但在美食學和文化研究語境中,仍未得到足夠重視。
本文嘗試解決上述問題。通過文本細讀,將它置于英國、美國和阿拉巴馬州不同的烹飪習慣中,可以得出《造洋飯書》遵循嚴格英國中產階級話語,明顯與高第丕夫人的美國南部成長軌跡背道而馳。盡管因缺乏足夠一手證據,只能做出一個有根據的猜測以解釋高第丕夫人緣何會在《造洋飯書》中放棄自身烹飪傳統,轉向英國資產階級烹飪偏好。即便如此,《造洋飯書》仍具研究意義,它使人們了解到整個十九世紀歐洲與美國食物的話語和演變,及其對食譜制作產生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