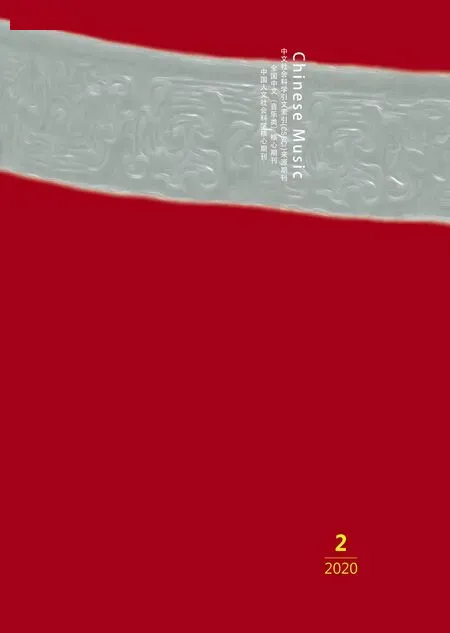音樂創(chuàng)造力:概念與誤識
創(chuàng)造是人類文明的基石,創(chuàng)造力是人類能力和智慧的最高表現(xiàn),是人類進步的源泉。音樂創(chuàng)造力(musical creativity)是一般創(chuàng)造力在音樂領域中的具體表現(xiàn),也是人類音樂文化得以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原始動力。國外有關音樂創(chuàng)造現(xiàn)象的探究早在古希臘時期就已經(jīng)開始,但由于長期受到神秘主義觀念的影響,導致其研究進展十分緩慢。自1950年吉爾福特(Guilford)開啟一般創(chuàng)造力的心理學研究熱潮以來,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科學化”研究才逐步展開。截至目前,有關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研究在哲學、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人類學和認知神經(jīng)科學等眾多領域中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尤其是近年來成為國外音樂教育領域學術研究的熱點。①葉黃晨:《英國音樂教育學科領域近十年研究狀況述評—基于3本SSCI、A&HCI期刊的知識圖譜分析》,《中國音樂》,2019年,第2期,第169-178頁。然而,人們對“音樂創(chuàng)造力”這個概念依然心存疑惑且存在諸多“誤識”。這些“誤識”潛移默化地深入到人們的音樂意識之中,導致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理論研究與教育實踐進展緩慢。近年來,隨著心理學、認知神經(jīng)科學和文化人類學等領域對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關注,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研究取得了積極的進展。在此背景下,汲取不同領域的研究成果,明晰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概念,進而澄清一些誤識,對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學術研究和教育實踐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
一、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概念界定
音樂創(chuàng)造力是一種領域創(chuàng)造力,是一般創(chuàng)造力在音樂領域中的具體表現(xiàn)。理解一般創(chuàng)造力的概念,有助于明晰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概念。
(一)創(chuàng)造力的概念
創(chuàng)造力(creativity)是一個極富爭議的概念,在不同的領域和不同的視角下有不同的界定。在心理學領域,國外最有影響的界定是美國心理學家斯滕博格(Robert J.Sternberg)在其《創(chuàng)造力手冊》中的定義:創(chuàng)造力是一種提出或產(chǎn)出具有新穎性(即獨創(chuàng)性和新異性等)和適切性(即有用的、適合特定需要的)的工作成果的能力。②〔美〕羅伯特·斯滕博格:《創(chuàng)造力手冊》,施建農等譯,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頁。國內最有影響的界定是林崇德等的定義:創(chuàng)造力是指根據(jù)一定的目的和任務,運用一切已知信息,開展能動的思維活動,產(chǎn)生某種新穎、獨特、有社會價值產(chǎn)品的智力品質。③林崇德等:《創(chuàng)新人才與教育創(chuàng)新研究》,北京:經(jīng)濟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25頁。歷史上有關創(chuàng)造力的定義多達數(shù)百種,至今也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界定,每一種創(chuàng)造力的理論都有一個自己特別的定義。④Sternberg,Robert J.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New York: Academic Press,2013.雖然界定不同,但對創(chuàng)造力至少包括四種主要成分則具有廣泛共識,即創(chuàng)造力是由創(chuàng)造的人、創(chuàng)造的過程、創(chuàng)造的產(chǎn)品和創(chuàng)造性的環(huán)境四個方面構成。總體而言,創(chuàng)造力是人腦對客觀世界特定反映的一種心理品質,是人在一定的社會環(huán)境中從事創(chuàng)造性活動并獲得創(chuàng)造性產(chǎn)品的能力,創(chuàng)造性的產(chǎn)品應當包括新穎性與適當性兩大核心特征。⑤貢喆、劉昌、沈汪兵:《有關創(chuàng)造力測量的一些思考》,《心理科學進展》,2016年,第1期,第31-45頁。
(二)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概念
就像創(chuàng)造力的概念五花八門一樣,“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概念也是眾說紛紜。角度不同,人們對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理解不同,因而對其概念的界定也不一致。由于創(chuàng)造力是深藏于主體內部的一種心理品質,而創(chuàng)造性產(chǎn)品則以創(chuàng)造的結果來顯現(xiàn),因此,許多學者都從“產(chǎn)品”的角度來界定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概念。戴維·埃利奧特(David Elliot)將音樂創(chuàng)造力界定為:在一定的音樂語境中產(chǎn)生原創(chuàng)且有價值的音樂產(chǎn)品的能力。⑥Elliott,David James.Music matters: A new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447.馬佐拉(Guerino Mazzola)則界定為:在音樂領域中要有能力創(chuàng)作作品,且這個作品必須是有新意的或具有獨創(chuàng)性的(new/original),以及恰當?shù)幕蛴袃r值的(suitable/useful)。⑦Mazzola,Guerino et al.Musical Creativity: Strategies and tools in composition and improvisation.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2011,p.145.究其本質,這兩種定義都將創(chuàng)造力的兩個核心特征—新穎性與適當性作為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基本要素。然而,由于音樂是一種時間藝術,所有音樂行為都潛在地具有創(chuàng)造性,因此音樂創(chuàng)造力是一種“過程性”行為,而這一過程的核心是思維,因而,另外一些學者則從思維的角度界定音樂創(chuàng)造力。韋伯斯特(Peter Webster)的界定最為典型,他認為:音樂創(chuàng)造力是包括聲音的創(chuàng)造性思維,它是在聚合思維和發(fā)散思維共同作用下產(chǎn)生新的音樂產(chǎn)品。⑧Webster,Peter R.Creativity as creative thinking.Music Educators Journal,1990,76(9),pp.22-28.而另一位學者斯科特·沃森(Scott Watson)也認為,音樂創(chuàng)造力是在音樂藝術作品的創(chuàng)作中運用想象力和原創(chuàng)思維的能力。⑨Watson,Scott.Using technology to unlock musical creativit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20-21.然而,根據(jù)希斯贊特米哈伊(Csikszentmihalyi)提出的“創(chuàng)造力系統(tǒng)觀”(A System Perspective),創(chuàng)造力的產(chǎn)生并不僅僅是一個心智歷程,還是一個文化和社會事件。⑩Csikszentmihalyi,Mihaly.Society,culture,and person: A systems view of creativity.The systems model of creativity.Springer,2014,pp.47-61.因此,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英國學者帕梅拉·伯納德(Pamela Burnard)基于“實踐場域”的觀念提出了“多樣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概念,認為不同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產(chǎn)生不同的音樂創(chuàng)造力。?Burnard,Pamela.Musical creativities in practic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因此,她將音樂創(chuàng)造力界定為:(1)既包括概念的關系結構及將他們與經(jīng)驗世界聯(lián)系在一起的方法,又包括擁有某種社會歷史背景的各種角色;(2)體現(xiàn)著作者身份和調和形式的多樣性;(3)超越了不同風格的限制,代表著音樂產(chǎn)生和消費的多種社會結構。這三層概念把音樂創(chuàng)作力“是什么”和“怎么樣”這些問題從主流意識和對天才論的錯誤認識中區(qū)分出來。?帕梅拉·伯納德:《實踐中的音樂創(chuàng)造》,喻意譯,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5年,第14、12頁。
由此可見,不同的角度關注的重點不同,其概念的界定也不相同。雖然其概念的界定不同,但作為一般創(chuàng)造力在音樂領域中的具體表現(xiàn),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所指”是相對一致的。在本質上,音樂創(chuàng)造力是人腦對客觀世界特定反映的一種心理品質,這種心理品質表現(xiàn)為人成功地完成音樂創(chuàng)造性活動所必須具備的能力。這種能力是人在一定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中,通過創(chuàng)造性思維與音樂性思維的共同作用而產(chǎn)生新穎且適當?shù)囊魳樊a(chǎn)品。不同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和音樂實踐語境會產(chǎn)生不同的音樂創(chuàng)造力,因而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表現(xiàn)具有多樣性。綜合不同視角的觀點,基于音樂藝術的領域獨特性,可將音樂創(chuàng)造力界定為:人在一定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中建構新穎而適當?shù)囊魳穼嵺`的心理品質。
二、關于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誤識
由于創(chuàng)造力本身晦澀難懂,加之音樂藝術的抽象性,使得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概念很難理解。尤其是長期受到“神秘論”的影響,人們在理解音樂創(chuàng)造力時存在一些誤識。這些誤識的產(chǎn)生與發(fā)展深深地根植于人類的各種音樂行為之中,并導致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研究進展較為緩慢。澄清這些誤識,對于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科學認知、深入研究和教育實踐等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
(一)音樂創(chuàng)造力來源的神秘論
有關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探究,長期受到“神秘論”的影響。最早有關創(chuàng)造力的論述就是以神的干預為基礎的,認為有創(chuàng)造力的人是一個空的容器,有待神去用靈感把它填滿,這樣的個體再把有靈感的想法傾倒而出,形成超凡脫俗的作品。?同注②。柏拉圖(Plato)就是依此觀念認為,詩人的創(chuàng)造源于繆斯女神(the Muse)的口授,繆斯女神就是靈感的源泉,一個人可能有創(chuàng)造合唱曲的靈感,而另一個人則具有創(chuàng)造英雄史詩的靈感。?同注②。這是古代人們對創(chuàng)造力的認識,然而,這一認識卻根深蒂固地流傳到了現(xiàn)代,即使在當下,很多人依然認為創(chuàng)造力是神秘的。尤其是在音樂領域,很多人通常將音樂創(chuàng)作的過程認為是一種下意識的行為,充滿神秘色彩,晦澀難懂。比如,莫扎特被認為是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天才,把他的創(chuàng)作描述得“非常神奇”,而這樣的描述很容易讓人們對音樂的創(chuàng)造產(chǎn)生神秘的誤解。這也導致一些權威的詞典和一些理論家給人們灌輸了錯誤的概念,比如經(jīng)常認為音樂的創(chuàng)作完全依賴于“想象”,將藝術家視為天才。?帕梅拉·伯納德:《實踐中的音樂創(chuàng)造》,喻意譯,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5年,第14、12頁。這種對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片面認識潛移默化地深入到人們的音樂意識之中,加深了人們對音樂創(chuàng)造力神秘論的印象。就像神秘主義者認為的,創(chuàng)造力本身根本不能進行科學研究一樣,?同注②。音樂創(chuàng)造力也是神秘而無法進行研究的。這一根深蒂固的誤識,不僅使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研究進展緩慢,更使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教育實踐長期被冷落。
事實上,在文藝復興時期關于創(chuàng)造力的觀念中,已經(jīng)能夠將神靈的啟示和人類的創(chuàng)造加以區(qū)別。?Sawyer,R Keith等:《創(chuàng)造性:人類創(chuàng)新的科學》,師保國等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5頁。創(chuàng)造力的“神秘論”自高爾頓(Galton)1869年出版《遺傳與天才》(Hereditary Genius)一書開始,就結束了這種錯誤,他也開啟了創(chuàng)造力的現(xiàn)代研究。?同注②。尤其是1950年,吉爾福特開啟創(chuàng)造力的“科學化”研究熱潮以來,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心理學研究才逐步展開,這為破解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神秘論”提供了“武器”。事實上,音樂創(chuàng)造本身的確復雜而深奧,其研究也十分困難,但音樂創(chuàng)造力也絕不是神秘而不可知的。比如,音樂創(chuàng)造的過程的確離不開“音樂想象”,但音樂想象也要按照音樂藝術的審美規(guī)律來創(chuàng)造音樂,而審美的規(guī)律是可以被認知的。?張前:《音樂欣賞、表演與創(chuàng)作心理分析》,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06年,第140頁。同時,音樂創(chuàng)造中并不是完全依賴于“想象”,還需要掌握熟練的音樂表達規(guī)律、創(chuàng)造的技巧和豐富的情感表達方式等手段,這些都是可以被人們認知和研究的。近年來,隨著認知神經(jīng)科學的快速發(fā)展,研究者通過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事件相關電位(ERP)等手段,對音樂創(chuàng)造力進行了許多腦科學研究。這些研究不斷發(fā)現(xiàn)了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腦機制,揭示了音樂創(chuàng)造對腦功能網(wǎng)絡的可塑性,證實了音樂創(chuàng)造的過程包含了情感、工作記憶與運動功能的調用與整合等。?盧競:《音樂創(chuàng)作的腦機制研究》,電子科技大學2016年博士論文。同時也發(fā)現(xiàn)了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相關腦區(qū),如前額葉皮層、感覺運動皮層和枕葉皮層等區(qū)域在音樂創(chuàng)造力活動中有所激活等。?Dietrich,A and R Kanso.A review of EEG,ERP,and neuroimaging studies of creativity and insight.Psychological Bulletin,2010,(5),pp.822-848.雖然從音樂美學的角度而言,這些研究成果對于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研究還有一定的“機械性”,但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音樂創(chuàng)造力并非是神秘的和不可知的,而是可以在多個層面進行認知和研究的文化心理現(xiàn)象。創(chuàng)造力專家斯滕博格曾說:“在信仰科學的心理學家看來,創(chuàng)造力研究的神秘主義方法是不能接受的,科學的研究方法之所以不能撼動一些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觀念,只是因為這些科學的心理學家闖入了他們不該涉足的領域。”?同注②,第5、3頁。我國音樂教育家廖家驊20世紀80年代在《談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開發(fā)》一文中就曾指出,培養(yǎng)中小學生的音樂創(chuàng)造力中至關重要的是我們要破除“作曲神秘”的精神枷鎖。?廖家驊:《談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開發(fā)》,《人民音樂》,1988年,第6期,第32-33頁。然而,時至今日,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神秘論”依然籠罩在我們心頭,使得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科學研究與教育實踐進展緩慢。因此,排除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神秘論誤識,堅持“科學”的音樂創(chuàng)造力觀念是當下音樂創(chuàng)造力亟待改變的現(xiàn)狀。
(二)音樂創(chuàng)造力產(chǎn)生的天才論
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天才論”和“神秘論”一脈相承,且較為盛行,認為它是一種超乎常人的特殊表現(xiàn),是少數(shù)天才具有的獨特能力。天才(genius)一詞在18世紀首次被用來形容創(chuàng)造性個體(Becker,2001;Tonelli,1973),后來是指那些具有杰出的智慧和才能、擁有卓越的創(chuàng)造力和想象力的人。在音樂領域,那些載入史冊的著名作曲家,比如巴赫、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等等,他們因杰出的音樂創(chuàng)造力而在一定程度上“佐證”了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天才論,莫扎特幾乎成為天才的代名詞。而創(chuàng)造力的“人格特質觀”?創(chuàng)造力的人格特質觀認為,創(chuàng)造性是一種一般的人格特質,就像IQ一樣。如果你是一個更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人,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都會顯得更有創(chuàng)意,那些沒有這種特質的人是不太可能變得有創(chuàng)意的。即創(chuàng)造力是遺傳的,一些人天生就更富有創(chuàng)造性。(參見:Sawyer,R Keith:《創(chuàng)造性:人類創(chuàng)新的科學》,師保國等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5頁。)則強化了這種天才論。事實上,天才的形成的確離不開一定的獨特天賦,但也需要后天的培養(yǎng)和環(huán)境等因素的共同作用。高爾頓在《遺傳與天才》一書中就曾指出,創(chuàng)造性成果主要來自于一般能力,而一般能力也是天才所必需的能力之一(Albert,1975;Cropley,1966)。?同注②,第5、3頁。除了一般能力之外,天才還需要具備其他因素。坦南·鮑姆(Tannenbaum,1983)就提出天才的五個因素,包括(1)個體在發(fā)生作用的領域中有優(yōu)越的一般能力;(2)該領域需要的特殊才能和能力;(3)優(yōu)越的環(huán)境條件;(4)好奇心、堅持性等非智力因素;(5)機遇。?Tannenbaum,Abraham J.Gifted Children: Psychological and education perspectives. New York: Macmillan College,1983.可見,即使是天才也是眾多因素造就的。而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天才論則僅僅把音樂創(chuàng)造力看作是少數(shù)人具有的獨特能力,并夸大了“先天因素”在音樂創(chuàng)造力中的作用,甚至忽略了作為天才也需要具備的其他因素。這一誤識也為那些缺乏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人找了不必努力的借口,比如常常有人會說自己“五音不全”,這同時強調自己沒有音樂創(chuàng)造力。而事實上,僅就音樂能力而言,“它和語言一樣,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基本認知能力之一,對音樂一竅不通的人也天生具有‘音樂細胞’”。即使那些根本不懂音樂的人也具有對節(jié)奏和音調的感知能力,能夠區(qū)分樂曲的開始和結束,能將接收到的聽覺信息分段并加以理解。?Sridharan,Devarajan et al.Neural dynamics of event segmentation in music: Converging evidence for dissociable ventral and dorsal networks.Neuron,2007,55(3),pp.521-532.現(xiàn)代學界認為,音樂創(chuàng)造力不僅僅是天才所具有的獨特能力,而是人人都具備的日常能力。?Richards,Ruth Ed.Everyday creativity and new views of human nature: Psychological,social,and spiritual perspectives.Washingto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07,p.167.即便是那些高音樂創(chuàng)造力個體的“偉大作曲家”,他們的確具備優(yōu)良的音樂天賦,但他們也必須通過嚴格而系統(tǒng)的訓練,掌握精通的音樂創(chuàng)造技能,同時伴隨特定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才有可能成為卓越的作曲家。因此,音樂創(chuàng)造力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天賦的制約,多大程度上受到后天學習的影響等,這些問題依然在爭辯中,但不可否認的是,音樂創(chuàng)造力并非僅僅是天才所具有的能力,而是每個人都具備的日常能力,只是這種能力的大小存在差異而已。因此,糾正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天才論,把音樂創(chuàng)造力看成一種日常能力,這對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可研究、可教育、可培養(yǎng)、可提高等具有極為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三)音樂創(chuàng)造力類型的“霸權”論
自近代以來,受到“歐洲音樂中心論”的影響,西方藝術音樂在世界范圍內廣泛傳播,尤其是西方古典音樂作品中的經(jīng)典作品使我們無法擺脫貝多芬崇拜時代的限制(庫克,1998)。雖然西方古典音樂創(chuàng)造的經(jīng)典范式僅限于正統(tǒng)的高雅藝術,但其長期“霸權”使我們難以從更廣泛的角度去認識其他類型的音樂和其創(chuàng)造力。?同注?,第21頁。而關于“創(chuàng)造力”的學術著作則“助長”了這種“霸權”論的泛濫,比如幾乎所有關于創(chuàng)造性的科學書籍都局限于那些西方文化高度重視的創(chuàng)意表達。?同注?,第6頁。中國自“學堂樂歌”以來,西方藝術音樂傳入國內,并逐步占領“陣地”,深刻影響著我們對于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觀念。這使得一些人誤認為音樂創(chuàng)造力就是西方藝術音樂的創(chuàng)造力,或者說占據(jù)主導地位的音樂創(chuàng)造力就是西方古典音樂的創(chuàng)造力。此外,受“莫扎特效應”?“莫扎特效應”是由加州大學的羅斯徹(Frances H.Rauscher)和戈登·肖(Gordon Shaw)博士通過音樂與空間—時間推理的實驗證明,包括莫扎特的音樂在內的所有音樂對人的大腦機能及其發(fā)展有著積極的影響。這也是加德納把音樂作為多元智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重要依據(jù)。參見:Jenkins,John S.The Mozart effect.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2001,94(4),pp.170-172.的影響,以莫扎特為代表的西方古典作曲家的作品,已經(jīng)跨越了音樂欣賞的范圍,廣泛使用在諸如胎教、提高智力、治療疾病,甚至提高牛奶產(chǎn)量等領域。不可否認,西方藝術音樂的確具有“強大”的音樂創(chuàng)造力。然而,世界音樂是多元的,是多樣的,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表現(xiàn)出不同的音樂創(chuàng)造力,世界音樂也需要改變西方藝術音樂的“霸權”地位。例如中國傳統(tǒng)民歌中,樂曲的形式從來都是多種多樣的。因為沒有最終形式,所以對樂曲的不斷改進就是一種創(chuàng)造(斯托克,1991)。?同注?,第23頁。因此,全球各民族的音樂都會在特定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影響下形成其特定的音樂創(chuàng)造力。柯凱樂(Kurkela)和瓦克瓦(Vakeva)在其所著《音樂史非經(jīng)典化》(De-canonizing Music History)一書中,就講述了不同的音樂風格和音樂傳統(tǒng)都有自己的經(jīng)典樂曲和自身的音樂創(chuàng)造力。?Kurkela,Vesa and Lauri V?kev?.De-canonizing music history.Cambridge Scholars Pubulishing,2009.因此,不存在適用于“全球”的單一的音樂創(chuàng)造力,音樂創(chuàng)造力蘊含在不同的音樂傳統(tǒng)和音樂風格之中,世界多元化和多樣化的音樂都具有其自身獨特的音樂創(chuàng)造力。這同時也表明每一種音樂都承載著自身文化的創(chuàng)造力,保護和傳承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就是尊重人類文明的多樣性和人類創(chuàng)造力的多樣性。
(四)音樂創(chuàng)造力產(chǎn)品的單一論
受西方藝術音樂的創(chuàng)作和傳播過程的深刻影響,在人們的音樂觀念中,長期認為音樂活動包含三個要素:即作曲者、演奏者和聆聽者。這種觀念是把作曲者的地位置于演奏者之上,又把演奏者和作曲者凌駕于聽眾之上,從而使得“音樂創(chuàng)造”這個詞僅僅指向作曲家,其產(chǎn)品也僅限于一度創(chuàng)作的產(chǎn)品。沃爾特斯托夫(1994)認為,作曲是由完整性規(guī)則所引導的過程,完整性規(guī)則詳細闡明了一場完整表演所需的音樂作品該有的那些組成。在此基礎上,高爾(1992)認為,作曲的一項功能就是制作出一個持久的人工制品。?同注?,第20、29頁。這種觀念加深了人們對于“作曲”作為音樂創(chuàng)造代名詞的誤解。這種誤解不僅無視演奏者的“二度創(chuàng)作”和聽眾的“三度創(chuàng)作”產(chǎn)生的“產(chǎn)品”,也無視現(xiàn)代音樂藝術發(fā)生、傳播過程中的音樂制作、發(fā)行和消費之中形成的“音樂產(chǎn)品”,當然也不包含傳統(tǒng)民族音樂生成中“瞬間(同步)”產(chǎn)生的創(chuàng)造性“音樂產(chǎn)品”。
從音樂表演的“二度創(chuàng)作”而言,它是賦予音樂作品以生命的創(chuàng)造行為。?張前:《音樂美學教程》,上海: 上海音樂出版社,2002年,第141頁。在表演過程中個體或群體的表演均伴隨著音樂創(chuàng)造,甚至觀眾和樂迷也通過社會協(xié)調形成創(chuàng)造性活動。如越南音樂家坎貝爾和泰徹(1997)就指出:“音樂創(chuàng)造和演繹這兩者在重要性上不相伯仲。作曲家從最初的一個想法,到最后一首曲目成型的整個創(chuàng)作過程,同演奏者對曲目進行再次塑造并加入個人詮釋演繹出來的過程一樣重要……歌本是死的,是演繹賦予其生命。”?同注?,第20、29頁。一首音樂作品既能以一種固定產(chǎn)品的形態(tài)存在,亦可以被視為一個不斷演化的過程,對作品的每一次重新演繹都會賦予其一次新的生命。在東方的許多傳統(tǒng)音樂中,音樂“產(chǎn)品”經(jīng)常是即興創(chuàng)作的,并且在每一次演繹中都會產(chǎn)生“新的產(chǎn)品”。從音樂欣賞的“三度創(chuàng)作”而言,現(xiàn)代音樂美學認為,音樂作品的意義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理解和欣賞的過程中不斷生成、不斷變化的。因此,音樂欣賞者不僅不是音樂作品被動的接受者,而且也是作為創(chuàng)造性的主體,在音樂意義的生成過程中發(fā)揮著積極的作用。?同注?。音樂欣賞是把一個外在于自己的客體變?yōu)橹黧w感受的一部分,這就是欣賞者的創(chuàng)造,由于音樂作品的“多義性”,欣賞者的體驗也具有豐富性和創(chuàng)造性,因而,人們常說“有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就說明,作為“三度創(chuàng)作”的音樂欣賞中也會產(chǎn)生音樂的“產(chǎn)品”,只是這種產(chǎn)品是一種觀念性的、精神性的產(chǎn)品,且具有多義性、多解性和不確定性,這也正是音樂藝術的獨特魅力之所在。而在現(xiàn)代音樂語境中,音樂創(chuàng)造完全超越了作曲家這個“本體”。如DJ(Disc Jockey)的創(chuàng)造和交互音頻設計師(Interactive audio designer)的創(chuàng)造所產(chǎn)生的“產(chǎn)品”,也已經(jīng)大大地超出了人們觀念中固有的“音樂作品”的概念。從這個意義上講,在今天這個多元化、高科技化、媒體化的社會中,音樂創(chuàng)造性的“產(chǎn)品”具有潛在的多樣性。21世紀任何有關創(chuàng)造力的嚴肅研究都必須解釋人類創(chuàng)造的全部。?同注?,第7頁。而這一觀念,極大地擴展了對音樂創(chuàng)造力“產(chǎn)品”的范疇,甚至會改變人們對于音樂和音樂價值與意義的當代理解。
(五)音樂創(chuàng)造力形成的個體生成論
人們常常認為,創(chuàng)造力是某種心智活動,是一些特殊人物頭腦中產(chǎn)生的真知灼見。雖然這種觀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創(chuàng)造力的生成還必須觀照其形成的社會文化系統(tǒng)。盡管創(chuàng)造力意味著新穎而有價值的觀點或行動,但衡量一個人是否具有創(chuàng)造力不能以他個人的解釋為準,而需要給創(chuàng)造力設定一個基于特定領域的客觀標準。因此,創(chuàng)造力不是發(fā)生在某個人頭腦中的思想活動,而是發(fā)生在人們的思想與社會文化背景的互動之中,它是一個系統(tǒng)性的現(xiàn)象,而非個人現(xiàn)象。?同注⑩。就創(chuàng)造力的結果—“產(chǎn)品”而言,馬克思就曾指出:“產(chǎn)品不同于單純的自然對象,它在消費中才證實自己是產(chǎn)品,才成為產(chǎn)品。因為產(chǎn)品之所以是產(chǎn)品,不是它作為物化了的活動,而只是作為活動著的主體的對象。”?同注?,第178頁。音樂不同于一般的自然物,它是人為的產(chǎn)品,而且是為人而存在的對象,它作為一種社會文化,其創(chuàng)造力的生成具有系統(tǒng)性。表面看來,音樂創(chuàng)造力是個體的一種音樂創(chuàng)造能力,然而,其能力的高低卻是被領域內的專家或大眾所評判的,因此不能忽略生成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社會體系。尤其是在特定文化環(huán)境中,是否被認為具有音樂創(chuàng)造力取決于音樂的功能。?〔英〕約翰·布萊金:《人的音樂性》,馬英珺譯,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7年,第16頁。
在音樂領域,作曲家通常被認為是最具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人,并且常常被視為先知:音樂總譜是其圣書,樂隊指揮是其牧師,而音樂創(chuàng)造力卻很少出現(xiàn),即便出現(xiàn),也是作曲家一個人獨自創(chuàng)作的結果。盡管音樂創(chuàng)作基本都是在獨處狀態(tài)下完成的,但如果在個體層面之外不去進行社會文化層面的分析,也將很難理解他們的存在。?同注?,第24、31頁。事實上,作曲家也不是孤立的,音樂創(chuàng)造的產(chǎn)生需要創(chuàng)作者和觀眾之間的互動和交流,它不是個人成果,它是整個社會對個人成果的評價。?同注?,第24、31頁。因為音樂創(chuàng)造行為本身就發(fā)生在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社會與不斷擴大的網(wǎng)絡空間創(chuàng)造范圍的關系之內。正如伯恩斯坦(Bernstein)的觀點:“音樂創(chuàng)造的聲音是由規(guī)范其溝通模式的論證規(guī)則之專業(yè)化程度所決定的。”?同注?,第24、31頁。對音樂創(chuàng)造力內涵的深入理解能夠使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音樂家之間以及音樂家、消費者和大眾之間關系的性質,并影響我們對整個社會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認知。音樂創(chuàng)造并非是價值中立的,同樣身為創(chuàng)造參與者的觀眾,他們也在自己的音樂生活和社會環(huán)境中尋找與其相關聯(lián)的意義。音樂創(chuàng)造力是基于特定文化背景中的,是整個社會文化系統(tǒng)交互性行為的結果,發(fā)生在多重意義的多元化社會空間之內。音樂創(chuàng)造力除了在音樂作品、音樂表演或產(chǎn)生音響的新形式中表達以外,還要從獲得音響的社會意義中體現(xiàn)出來。?〔英〕約翰·布萊金:《人的音樂性》,馬英珺譯,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7年,第16頁。從這個意義上講,音樂創(chuàng)造力不僅僅是個體生成的,更是社會系統(tǒng)中生成的,體現(xiàn)出整個社會系統(tǒng)的“創(chuàng)造性”。
結語
綜上所述,音樂創(chuàng)造力如同音樂本身一樣,是一個抽象而又復雜的概念。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研究涉及音樂學、哲學、心理學、教育學和認知神經(jīng)科學等眾多領域,不同領域關注的視角不同,因而其概念的界定也不盡相同。廣義而言,音樂行為本身就是一種創(chuàng)造,因而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概念是多元、多樣和多態(tài)的。同時,由于受到一些誤識的影響,加深了對音樂創(chuàng)造力概念的“誤解”。澄清音樂創(chuàng)造力來源的神秘論,有助于建立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科學觀”;澄清音樂創(chuàng)造力產(chǎn)生的天才論,才能將其作為人人都具備的日常能力加以培養(yǎng);澄清音樂創(chuàng)造力類型的“霸權”論,才能尊重音樂創(chuàng)造力形態(tài)的多樣性;澄清音樂創(chuàng)造力產(chǎn)品的單一論,才能理解音樂創(chuàng)造力產(chǎn)品的多重性;澄清音樂創(chuàng)造力形成的個體生成論,才能理解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社會交互性。因此,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概念不是孤立的、靜態(tài)的,而是不斷發(fā)展變化的,是發(fā)生在具有多重意義的多元化社會空間之內的。?同注?,第12、41頁。未來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研究,需要在“視界融合”的觀念中,認識音樂創(chuàng)造力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價值等級定位,在特定的社會文化語境中找到自己的身份認同,從而在不同的實踐中進行多樣化的音樂創(chuàng)造,表達多重的情感體驗。音樂創(chuàng)造力的研究不僅對音樂本身有意義,更為我們探索創(chuàng)造力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領域。?同注?,第12、4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