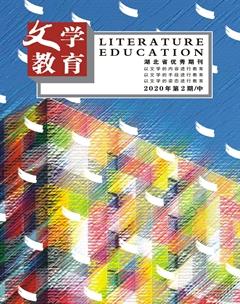劉錫誠先生微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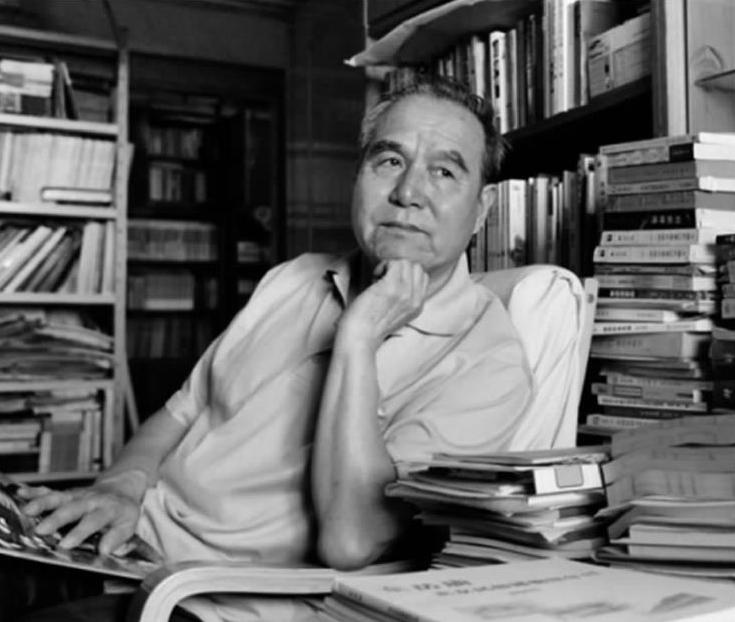

“淡生涯一味誰參透,草衣木食,勝如肥馬輕裘。”
——(元)不忽木 [仙呂]點絳唇 辭朝寧可身
劉錫誠先生常以“邊緣人”自居。按照先生的說法,“邊緣”就是退離中心,作壁上觀的意思。他曾言:“真正的文人多自謙,戒浮躁,胸懷平常之心,甘為邊緣人。粗茶淡飯,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會,靜觀人生百態,寫出多少能夠傳世的作品來。”[1]然而,回顧中國民間文藝學的發展歷程,想邊緣的人,卻不得“邊緣”,也沒有“邊緣”。
先生一“出道”,就站到了當時學術的制高點上。上世紀50年代,曾主修俄語專業的他在曹靖華教授指引下,與蘇聯民間文學結下“情緣”,后來又翻譯了大量蘇聯民間文藝學譯著,如《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蘇聯民間文學論文集》、《蘇聯民間文藝學40年》、《俄國作家論民間文學》等。“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先生對蘇聯民間文學作品及學術著作的翻譯,對發展中的中國民間文藝學頗具引領作用。
先生之所以選擇進入民間文藝學領域,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先生身上根深蒂固的“農民”情結,“我畢竟是農民的兒子,農村的生活和農民的口傳文學與民間文化的耳濡目染,融入血液,深入骨髓,時時撞擊著我的心胸,使我無法忘情。”[2]先生1935年出生于山東昌樂的一個農民家庭,1953年進入北大俄語系學習,畢業后旋即進入民間文學界,此后四十載春秋,先生先后在中國文聯民間文藝研究會、新華社、《人民文學》編輯部、《文藝報》編輯部以及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等單位任職。“發強剛毅,足以有執”,先生在《人民文學》和《文藝報》工作期間展現出的工作才能得到周揚的賞識,遂于1983年至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任常務書記,后再任副主席,先生一直主持該會工作,直至1991年調離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
“用之則行”,在三十余載“入世”光陰中,先生都克己勤勉,兢業為公。1984年,在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1987年改稱為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任職不久,先生就開始主持編撰后來被譽為“民族文化長城”、“世紀經典”的“中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無疑,此項工作足以使先生彪炳史冊。然而,輝煌背后,負重異常,“三套集成”的面世過程是艱難的。動議初期,國家文化部因民間文學專業的歸屬問題,并未直接簽署民研會的征求。正是由于有了先生和民研會書記處同志們的奔走斡旋,才使得文化部、國家民委和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共同簽發《關于編輯出版〈中國民間故事集成〉〈中國歌謠集成〉〈中國諺語集成〉的通知》,“三套集成”的普查與編撰工作正式在全國鋪開。官方文件簽署后,先生又主持召開了多次全國會議,討論“三套集成”的機構設置、工作步驟和人員培訓等問題。作為主要領導人,除了負責各項事務性的工作外,先生還就具體的采錄、編撰、翻譯工作做了學術層面的分析與指導,并起草編纂《中國民間文學集成工作手冊》,為“三套集成”工作的展開提供了科學明晰的理論依據。
在支持領導“三套集成”的工作之外,先生在民研會任職期間的其他工作也做得有聲有色。陳遼就曾說,劉錫誠主持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的七年(1983- 1989),是“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前身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歷史上既思想解放又實事求是、既紅火活躍又成果迭出的七年。”[3]確如此言,先生在任期間,為了加強民間文藝學理論研究,曾以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為中心,定期舉辦學術研討會,包括青年民間文學理論家學術會議、深圳全國民間文學理論學術研討會、《格薩爾》學術研討會、中芬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等[4],探討理論,獎掖后進,為民間文藝學專業培養了大量人才。同時,先生還任《民間文學論壇》等期刊的主編,給研究民間文藝的學者提供文章發表的平臺,如此貢獻,不一而足。
“舍之則藏”,1991年,先生已逾知天命之年,在退離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出世”之后,先生并沒有“藏”,沒有歸隱,去做云間的野鶴,去為世外的散仙,應該說,先生身居民間,卻心憂江湖,也心憂廟堂,毅然“華麗轉身”,先生以學術為民立言的人生至此真正開啟。
先生傾心于文藝評論、原始藝術、民間文藝、民俗學、非物質文化遺產等領域的研究,是一個功力深厚的“打通式”學者。1998年,先生的《中國原始藝術》一書出版,此書在當時的中國算得上是一部原始藝術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鐘敬文先生對此書予以高度評價:“系統地研究中國原始藝術,錫誠算是第一個,”[5]前事不忘,四年之后,也即2002年,先生的專著《象征——對一種民間文化模式的考察》出版,這是“象征”研究的又一部力作。
先生致仕之后,真正攪動起民間“風云”的,是2006年出版的百萬言巨著——《20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黃沙始到金”,此書一出,誰與爭鋒,諸多學人發文,認為此書填補了我國民間文學學術史研究的空白。高有鵬發文《一部學術史的大度與厚重》(2007),稱此書及時而詳細地梳理了從20世紀初葉到20世紀末民間文學學科漫長的歷程,它的大度與厚重是我們“難得的一面明鏡。”呂微言:“那些仍在守護著民間文學這塊教學和學術園地的師生們將是如何地盼望著先生的這部具有拓荒性質的鴻篇巨制,因為先生的這部著作不僅是他們研習的教材,更是支撐他們人生選擇的‘圣典”。[6]因為此書,呂微將先生喻作民間文學的西西弗斯。
如同西西弗斯推起巨石,先生著《20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也在試圖以一人之力扛起“巨石”,“單槍匹馬地去啃這塊被擱置久矣而至今無人問津的‘硬骨頭,以能梳理一下百年來民間文學運動和學術研究,從起伏興衰中尋找歷史的足跡和經驗,對學科的建設有所助益。”[7]先生無疑擎起了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這塊百年“巨石”。
如先生言,百年來,民間文學的發展以及學科的建設過程確實是“起伏興衰”。1918年成立的北京大學歌謠征集處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搜集民間歌謠的高潮。歌的搜集,學的探索,民的啟蒙,國的建設在時代潮流中被粘結在一起,民間文學確實有一個轟轟烈烈而又“偉大”的開端。但高潮之為高潮,在于它自含落潮的命運,時局的動蕩與歌謠研究會研究人員思想的分歧,使得持續七年的歌謠運動在1925年似流星墜逝,如天虹消散。文化大革命期間,民間文學被視為不健康的文學被主流意識形態予以排斥。1997年,教育部在調整學科目錄時,將民間文學歸并為社會學下的二級學科,在學科設置中呈現出“民俗學(含民間文學)”的方式,這實際上是直接取消了民間文學學科本身。當此之時,耳順之年的先生連續寫了《為民間文學的生存——向國家學位委員會進一言》(2001)、《保持“一國兩制”好——再為民間文學學科一呼》(2004)等一篇又一篇文章,與眾多代表一起呼吁國家學位委員會恢復民間文學二級學科的地位和其“文學”屬性,但此倡議卻如沉海之石,無有回音。“時窮節乃現”,先生對民間文藝學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足鑒。
其實,不管是出世還是入世,民間文藝學學科建設都是先生一直進行著的事業。眾所周知,清晰的學科定位、鮮明的研究對象、自洽的研究方法是一門學科獨立性與合法性的主要依據。“行成于思,毀于隨”,先生膏油繼晷,兀兀窮年,作為文章,以促思成。
在學科定位上,先生提出,文學性是民間文藝學的本質屬性,民間文學是文學,“我們是把民間文學當作一種特殊的文學現象或文化史現象來對待的。”[8]“我的民間文學觀,理所當然地是以文學的觀點研究和處理民間文學,這是我的基本立場。”[9]先生認為,民間文學的創作是不自覺的、是群體性的、是口傳的,具有美學屬性。
對于研究對象,先生自己的研究成果最能說明問題。原始藝術、民間口頭創作以及民間藝術三類人類精神活動現象,都在先生的研究之列。民間文學的常見體裁:神話、傳說、民間故事、史詩等內容的研究,先生都有涉獵。此外,學術史回顧也是不可或缺的研究對象,除了大部頭的《20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外,先生還作小文,論述先前學者,如顧頡剛、黃石、鄭振鐸、茅盾、胡適等人的民間文學研究。
關于研究方法,先生花費的心力甚多。1988年,先生發文《整體研究要義》,提出“整體研究”理念,主張民間文藝學研究“必須超越作品表面所提供的信息,把目光投注到中國文化的深處,投注到相關學科所提供的豐富的資料和方法,才能全面地把握住所要研究的對象的整體。”[10]也就是說,民間文學要借鑒人類學、社會學、宗教學和藝術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來充實自己。“有容乃大”,先生試圖以跨學科研究的辦法來使民間文學研究走向縱深。與段寶林的“立體研究”法一樣,這樣的研究法可謂“開風氣之先”,在當時甚至現在都不失為一種“時髦”且實用的研究法。“寬裕溫柔,足以有容”,這形容人的品德之言,同樣也適用于學術,個人的胸懷和視野亦然會影響到方法論的選擇,先生性情之平和寬裕也孕育出包容性的整體研究法。
然而,“少則得,多則惑”,整體研究法是否會使民間文學喪失獨立性?先生無疑注意到了這一點,遂一直堅持,民間文學要長遠發展,就應該牢記自己的文學屬性和意識形態屬性,尤其是在對待兄弟學科——民俗學時,學者必須將兩者區別開來,這也是對整體研究法的補充。
先生又承繼了五十年代郭沫若、周揚和老舍等老輩學者在成立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時倡導的詩學研究法。這個研究法沿用了蘇聯“社會—歷史—審美批判”的觀念,認為研究民間文藝學要秉承“采集、整理、分析、批判、研究”的方法,挖掘其中的“詩學特性”和“審美意識”,探索人類的精神世界。高山流水,知音自有,先生的老友——劉守華提倡的以“故事詩學”研究民間文學的理念就與先生的詩學研究法一致。
建立中國特色的民間文藝學也是先生的一大倡議。在《民間文藝學學科建設講演錄選》(2019)一書中,先生將自己60余年來關于建設民間文藝學有關的講演稿集中薈萃,此舉對民間文藝學學科建設有著重要借鑒意義。
應該明了,中國的民間文藝學有著自身獨特的國情。新中國成立初期,通過實踐檢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成為我國的指導思想,這兩種思想影響到文藝界。1953年3月29日,郭沫若在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的成立大會上,作題為《我們研究民間文藝的目的》的報告時就宣稱,“民間藝術的立場是人民,對象是人民,態度是為人民服務。”[11]先生很好地繼承了這一傳統,從1984年起就屢次提出建立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的民間文藝學,認為民間文藝學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堅定歷史唯物主義立場,要與時俱進。
“成功在久不在速”,總的來說,對于民間文藝學的建設,先生琢磨了幾十載!先生的著作《民間文藝學的詩學傳統》(2018)是為證。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如果說先生在兩次主政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期間是在為公務“躬行”,那么,先生這十余年來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應該是一種具有生命自覺的“躬行”。全球化、信息化、現代化浪潮的來襲,削弱甚至摧垮了民間文學所依存的農耕文明,這使得民間文學生存、傳承和延續的前景堪憂。痛感于此,先生作文,或呼吁社會,或提議獻策;或交游縉紳,或往來鴻儒,無不顯示出這位民間赤子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決心,以及對民間“園地”的堅守。先生的著作《非物質文化遺產:理論與實踐》(2009)、《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中國道路》(2016),印證了先生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理念。
先生從業已六十余載,歲月悠悠,星移斗轉間,民間文學學科內部經歷了幾次學術風向的轉變,從文本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語境研究和生活研究,先生都是親身經歷者,甚至是首倡者。有學者說,先生本人就是“半部活的當代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12]此言不虛。有學者言:“劉先生自稱是‘邊緣人,但是他對學術的執著、對民間文藝無私的投入,對學術前沿問題的思考,所有這些都表明劉先生實際上一直處在學術的中心,甚至成為我們民間文藝學的一面旗幟。”[13]所以,“邊緣”始終是這位民間赤子的心境,它體現的是一位知識分子的高爽器識與凜然風骨。
學問求深求真,生活求簡求易,深邃似海,而又淺白如溪,此言舍先生其誰?
參考文獻
[1]劉錫誠:《邊緣人》,《中華英才》,1998年第10期.
[2][4]侯仰軍:《整體研究與建構中國特色民間文藝學——專訪民間文藝學家劉錫誠》,《中國文藝評論》,2017年第3期.
[3]陳遼:《劉錫誠:三十五年四“轉身”》,《揚子江評論》,2012年第6期.
[5]鐘敬文:《我的原始藝術情節》,《文藝界通訊》,1998年第10期.
[6][12]呂微:《中國民間文學的西西弗斯——劉錫誠<20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讀后》,《民俗研究》,2008年第4期.
[7]劉錫誠:《20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緒論,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頁.
[8]劉錫誠:《民間文學理論的建設問題》,原載《民間文學》1984年第7期.
[9]劉錫誠:《在民間文學的園地里——我的學術自述》,見《民間文學:理論與方法》,中國文聯出版社,2010年第1頁.
[10]劉錫誠:《整體研究要義》,載《民間文學論壇》,1988年第1期。收入《民間文學的整體研究》,臺北秀威咨訊出版中心,2015年版.
[11]劉錫誠:《民間文藝學的詩學傳統》,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年版第9頁.
[13]萬建中:《求真、求新、求深:劉錫誠的學術貢獻與學術追求》,《民間文化論壇》,2015年第3期.
周爭艷,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研究生院)文學所民間文學專業2019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間文學理論,神話學。
劉錫誠,男,1935年出生于山東昌樂,文學評論家、民間文藝家、文化學者。1957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歷任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編輯研究人員,新華社翻譯、編輯、記者,《人民文學》編輯部評論組長,《文藝報》編輯部副主任、主任,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駐會副主席兼黨的領導小組組長、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研究員,《民間文學》、《民間文學論壇》、《評論選刊》主編。主要社會職務有:中國俗文學學會副會長、會長,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旅游文化學會副會長。著有《中國原始藝術》、《20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民間文學:理論與方法》等專著20余本,學術論文10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