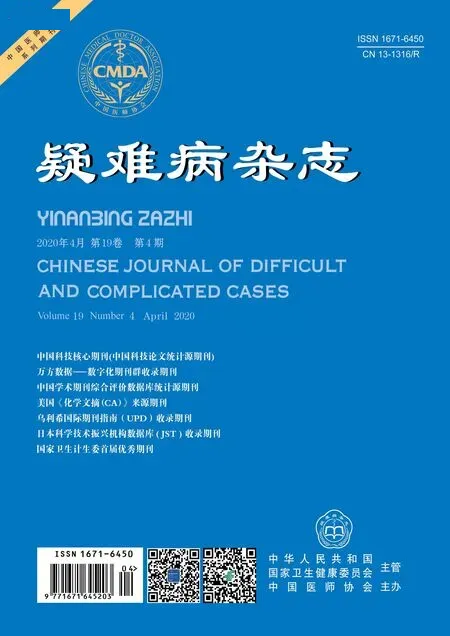氧化應激作用在子癇前期發病機制中的研究進展
李嘉健綜述 孫曉燕審校
子癇前期(preeclampsia,PE)是人類特有的妊娠期疾病,以高血壓和蛋白尿為特征,出現于妊娠中晚期。發病率因地理區域、季節、營養和種族而異,全世界有3%~8%的婦女受其影響[1]。迄今為止,子癇前期的發病機制仍未完全闡明。但“兩階段模型”被大多數人認可[2]。第一階段為癥狀前期,即胎盤血流灌注不足,從而為氧化應激的發生創造了良好的環境;第二階段為癥狀期,即母體發生全身炎性反應,包括血管內皮損傷、血栓形成和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激活,最終導致器官灌流不足和血液黏滯。氧化應激發生在該進程的每一階段,表明氧化應激在子癇前期的病理生理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可能是子癇前期胎盤和內皮功能障礙的關鍵原因。現對子癇前期發病過程中各階段氧化應激的參與情況,特別是其在妊娠初期滋養細胞侵襲、內皮功能障礙和母體全身炎性反應中的作用進行綜述。
1 子癇前期概述
子癇前期的定義為妊娠20周后新出現的產婦高血壓(收縮壓/舒張壓>140/90 mmHg)和蛋白尿(>300 mg/24 h)。嚴重的情況下,產婦可能并發肝臟病變(HELLP綜合征)、腎功能障礙、水腫、彌散性血管內凝血(DIC)等嚴重合并癥。對胎兒而言,子癇前期的主要并發癥包括胎兒生長受限導致的低出生體重、早產和胎兒死亡。該綜合征是當今工業化國家孕產婦和圍產兒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3]。終止妊娠,胎兒胎盤娩出是目前惟一有效的治療途徑。慢性宮內缺氧和醫源性早產也給新生兒帶來了巨大的風險。
2 氧化應激與正常妊娠

在正常妊娠期間,孕婦血清中ROS的生成增加,這是一種由正常的全身炎性反應引起的現象,與細胞成熟、細胞復制、胚胎發育和妊娠維持有關[5]。妊娠的特征是多個系統的動態變化,導致包括胎盤在內的不同器官基礎氧和能量消耗增加。胎盤最初處于低氧環境,但隨著發育成熟,其血管化發展為富氧環境[6]。胎盤富含線粒體,血管豐富,消耗孕婦基礎代謝率的1%左右,母體氧分壓高,導致活性氧產生增多,造成了“生理應激”[3]。
隨著妊娠的進展,對自由基損傷的防御機制也會增強,活性氧可被維生素C和E等抗氧化劑快速捕獲,或被多種防御系統抗氧化劑代謝,如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谷胱甘肽過氧化物酶(GPx)、過氧化氫酶、硫氧還原蛋白、過氧化物還原蛋白。但當ROS的產生超過抗氧化防御系統的代償能力時,就會發生氧化應激,進而引起炎性反應和毒性反應。
3 子癇前期的“二階段學說”
正常妊娠期間,子宮螺旋動脈重塑以確保子宮內膜和絨毛間隙的血管化及血流灌注。這種改變是以末端血管管腔的擴張及內部彈性成分和平滑肌成分的喪失為特征。第一階段的重塑是在低氧環境下完成的(1%~ 2%的氧分壓),隨著胎盤血管化的發展逐漸恢復到常氧狀態。而子癇前期患者表現為子宮螺旋動脈重構障礙,進而絨毛外滋養細胞浸潤異常,胎盤植入母體子宮壁過淺,即“胎盤淺著床”,最終使胎盤灌注減少[7]。間歇性的動脈血流會產生反復的缺血再灌注,誘導產生氧化應激。胎盤的氧化損傷導致炎性反應、細胞凋亡及細胞碎片釋放到母體血液循環中,包括一些抗血管生成因子,如可溶性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受體-1(sFlt-1)、可溶性內皮素(sEng)、細胞因子和氧化劑[8]。這些胎盤因子和碎片是母體內皮功能改變和妊娠炎性反應加劇的根源,進而進入第二階段,母體以全身血管炎性反應和收縮為特征的大規模系統性內皮功能障礙。
4 氧化應激和子癇前期
4.1 胎盤血管重構異常與氧化應激 子癇前期發病與滋養層細胞浸潤不足和螺旋動脈血管重塑受損有關。絨毛外滋養細胞通過母體蛻膜浸潤子宮螺旋動脈的整個過程,需要胎盤滋養層細胞與母體蛻膜細胞之間嚴格的相互作用和溝通,即不同細胞外蛋白酶的表達和作用,如基質金屬蛋白酶(MMPs)、和解整合素金屬蛋白酶(ADAMs)、具有血小板反應蛋白基序的和解整合素金屬蛋白酶(ADAMTSs)和組織蛋白酶[9]。子癇前期與胎盤組織中這些蛋白酶的表達下調、活性降低有關。據報道,具有Kazal基序的富含半胱氨酸的逆轉誘導蛋白(RECK)是一種鑲嵌于質膜的糖蛋白,可抑制MMPs和ADAMs的活性,進而控制滋養層細胞的侵襲性,促進氧化應激[10]。此外,滋養細胞和蛻膜細胞也表達蛋白酶抑制劑,如金屬蛋白酶組織抑制劑(TIMPs)和半胱氨酸(組織蛋白酶抑制劑)[11],而TIMPs和RECK的差異分布在子癇前期發病機制中也起著重要作用。

4.2 免疫調節異常與氧化應激 研究顯示,子癇前期婦女體內的免疫調節和免疫耐受異常,母體針對胎兒發生免疫應答,進而干擾滋養細胞侵襲和血管形成,導致氧化應激,引起母體全身炎性反應。研究發現Th1/Th2細胞免疫失衡、Th17/Treg細胞比例失調、蛻膜NK細胞調節異常等,均會導致滋養細胞侵襲失敗,螺旋動脈重構缺陷進而胎盤灌注減少,活性氧生成,加劇氧化應激[15]。此外,胎盤巨噬細胞系也與子癇前期發病機制有關,分別為母體胎盤部分的蛻膜巨噬細胞和胎兒胎盤的Hofbauer細胞。正常妊娠時蛻膜巨噬細胞多為M2表型,發揮免疫抑制作用,有助于螺旋動脈重塑和免疫耐受。而子癇前期表現為M1表型占主導地位,產生促炎細胞因子,加劇氧化應激。胎兒Hofbauer細胞數量下降,CD74表達下調和IL-10分泌減少,促進氧化應激和炎性反應[16]。Campbell等[17]發現,針對血管緊張素受體AT1的自身反應性抗體在子癇前期母體中水平升高,可抑制滋養細胞侵襲,進而促進氧化應激。補體激活在維持健康妊娠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很多學者發現補體系統的異常激活或調節不當則可能激活某些補體成分C3a,Bb等,進而導致經典途徑或替代途徑激活,氧化應激加劇,引起母體的全身炎性反應,導致子癇前期的發生[18-21]。
4.3 內皮細胞功能障礙與氧化應激 子癇前期胎盤灌注的改變引起胎盤微環境的改變,如ROS的產生、胎盤因子的釋放及內皮細胞的活化,最終加劇氧化應激,導致普遍內皮細胞功能障礙[22]。內皮功能障礙涉及以下多種機制。
首先,胎盤因子和合胞體滋養層微粒(STBMs)在母體循環中的釋放會引起內皮細胞炎性反應,從而加劇氧化應激。研究發現細胞因子IL-6、IL-1、TNF-α等諸多炎性標志物在子癇前期患者體內均升高[23]。STBMs還通過激活Toll樣受體(TLRs)和NF-κB,誘導單核細胞、NK細胞、樹突狀細胞和中性粒細胞增殖,從而使血管對血管調節物質的反應性改變、凝血系統激活、毛細血管通透性增加、NO生成減少及ONOO-生成,進而加劇氧化應激和全身炎性反應[24-25]。
其次,內皮功能障礙的機制之一還涉及可溶性fms樣酪氨酸激酶(sFlt-1)的釋放[3]。這是一種抗血管生成蛋白質,可拮抗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和胎盤生長因子(PLGF)等促血管生成因子。VEGF與受體Flt-1的相互作用在新生血管生長過程中起著關鍵作用,但該作用可被sFlt-1抑制,導致子癇前期母體循環中游離的VEGF水平較低,進而加劇氧化應激和ROS造成的內皮損害。此外,可溶性內皮素(sEng)也與內皮功能障礙有關,可通過改變血管內膜而加劇sFlt1的作用[26],進而加劇氧化應激和內皮損害。

4.4 線粒體的氧化應激 線粒體產生的氧化應激也被認為是一個潛在的治療靶點。子癇前期患者存在線粒體功能障礙,線粒體脂質過氧化增加,對氧化物的易感性增強。Teran等[29]研究發現,有線粒體功能障礙家族史者,子癇前期的發病率更高。而且在子癇前期婦女及其一級親屬的線粒體中,負責能量生產和氧化電子交換的基因表達異常,如細胞色素C氧化酶。實驗發現,與正常妊娠相比,用子癇前期婦女血漿處理過的內皮細胞,其線粒體內ROS明顯升高。而用一種線粒體靶向超氧化物歧化酶抗氧化模擬物MitoTempo,預處理內皮細胞后降低了細胞線粒體ROS的生成,并抑制了ROS誘導的細胞死亡。線粒體靶向抗氧化預處理在相同濃度下比一般抗氧化劑更有效,直接靶向治療方法具有重要作用[3]。
4.5 遺傳易感性與氧化應激 子癇前期具有明顯的家族聚集傾向,子癇前期婦女的一級親屬比無子癇前期家族史的婦女患病風險高5倍,二級親屬比無家族史婦女的風險高2倍,說明遺傳易感因素可能在子癇前期的發病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且其遺傳基礎是多基因的[30]。與氧化應激通路有關的遺傳易感基因包括編碼eNOS、COMT、NQO1、VEGF等的基因[31-32]。此外研究發現[33],亞硝基氧化還原狀態不平衡也可能是子癇前期的誘因之一,在子癇前期小鼠模型中轉錄因子STOX1對ROS和活性氮(RNS)的生成有相反的效應。STOX1過表達改變了ROS/RNS平衡和線粒體功能。RNS在STOX1轉基因胎盤中占主導地位,而ROS與NO反應產生ONOO-,導致氧化應激和血管功能障礙。氧化應激引起的血脂異常也會損傷內皮細胞,因此參與調節脂質代謝的基因也為子癇前期的遺傳易感基因,如編碼載脂蛋白E(ApoE)和脂蛋白脂肪酶(LPL)的基因[34]。母體和胎兒LPL基因型之間的相互作用可以改變子癇前期母體的脂質分布和疾病嚴重程度。LPL Asn291基因缺失及變異與子癇前期血漿LPL活性降低和血脂代謝異常有關[35]。
5 子癇前期的抗氧化體系
5.1 傳統抗氧化劑 作為生理保護劑,抗氧化劑可以中和活性氧造成的氧化損傷。與正常妊娠相比,子癇前期抗氧化防御能力降低,可能是由于自由基清除劑的效率降低和抗氧化酶的活性降低[36]。提高子癇前期婦女的抗氧化能力是目前子癇前期治療的熱點之一。流行病學研究將飲食中抗氧化維生素的缺乏與子癇前期風險的增加聯系起來,并提出抗氧化的維生素可能是預防子癇前期的方法[37]。硫酸鎂(MgSO4)是子癇前期治療的一線用藥,可降低子癇前期紅細胞膜的脂質過氧化,并保護內皮細胞。在胎盤外植體中,MgSO4可以防止缺氧引起的脂質過氧化水平升高[38]。此外, MgSO4可以降低人體合體滋養層質膜中的脂質過氧化,在子癇前期婦女中具有抗氧化作用[39]。有人提出,MgSO4可通過在細胞膜疏水微環境中與羥自由基(OH)和脂質過氧化物形成復合物,來降低自由基的生物利用度[40]。
為了減輕子癇前期的氧化應激,許多研究也評估了其他各類化合物,如維生素、N-乙酰半胱氨酸、β-胡蘿卜素等。維生素C和E是常見的抗氧化劑,前者能清除水相中的自由基,而后者能防止脂質過氧化。補充維生素C和維生素E是預防子癇前期氧化應激和內皮功能障礙的替代療法。然而,大量隨機對照試驗發現,補充這些維生素并不能預防子癇前期[41]。這與Ten?rio等[42]研究結果一致,其研究表明,維生素C和E、硒、l -精氨酸、大蒜素、番茄紅素和輔酶Q10的抗氧化治療對預防子癇前期無效果。N -乙酰半胱氨酸是谷胱甘肽的副產物,對谷胱甘肽的維持和代謝具有重要作用。研究發現,補充N -乙酰半胱氨酸可改善子癇前期患者的肝、腎功能,降低血壓,降低蛋白尿,改善氧化應激的程度[43]。其他研究表明,由于類胡蘿卜素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特性,攝入類胡蘿卜素對成年人的健康有積極的影響[44]。同時,將β-胡蘿卜素灌注于暴露在過氧化物環境中的人離體胎盤小葉,可以抑制過氧化物誘導的血管收縮并減少脂質過氧化物和血栓烷的分泌。褪黑素是一種有效的抗氧化劑,可直接清除自由基[45]。據報道,子癇前期胎盤褪黑素受體減少,而在用氧化應激誘導物處理過的人胎盤外植體中,褪黑素降低了胎盤的氧化應激[46]。在體外缺氧/復氧條件下,褪黑素調節炎性反應和自噬,減少人滋養細胞的凋亡。因此,外源性褪黑素治療可作為子癇前期的輔助治療手段,減輕氧化應激,從而提高胎盤細胞存活率,改善妊娠和胎兒結局[47]。
5.2 新型抗氧化劑——氫氣 氫氣是一種新型抗氧化劑[48],近年來已被證明具有治療各種氧化應激相關疾病的潛力。一項應用低子宮胎盤灌注壓的大鼠模型的研究發現[49],在子癇前期發作前預防性地給予氫分子可通過降低氧化應激而緩解高血壓,改善蛋白尿和腎臟組織學變化。同時大鼠母體循環內血管內皮生長因子水平升高,糾正了血管生長失調。而且氫氣還可減少子癇前期婦女滋養層BeWo細胞和絨毛組織中的sFlt-1,但對正常妊娠婦女的胎盤組織中sFlt-1無影響。這些結果提示,對子癇前期高危患者使用氫氣可能對母親和新生兒有潛在的臨床益處。管中等[50]發現,用不同濃度含氫培養基處理重度子癇前期胎盤滋養細胞后,滋養細胞的增殖活性顯著增強,且呈濃度依賴性。氫氣可抑制細胞凋亡,使細胞周期中G1期比例減少,S 期比例升高。另一項研究表明[51],高水平的維生素C和E會抑制滋養層細胞的增殖能力,并刺激促炎因子TNF-α的分泌,治療效果差,而高濃度的氫氣不會產生有害影響。因此,作為新型抗氧化劑,氫氣對子癇前期患者的防治有潛在的意義。
6 總結與展望
氧化應激是正常妊娠的一部分,但其加劇會導致子癇前期,并在各個病理階段起到關鍵作用。氧化應激在子癇前期的發病過程中處于中心地位,它參與了子癇前期病理生理第一階段,與滋養層細胞侵襲和血管重塑有關。同時氧化應激通過釋放促炎因子、細胞碎片等到血液循環中,參與第二階段的內皮功能障礙和全身炎性反應。認識氧化應激在子癇前期發病機制與病理過程中的作用是子癇前期抗氧化劑治療的基礎。多種抗氧化劑的使用旨在減少氧化應激對子癇前期的有害影響。預計會有更多的研究進一步探討抗氧化治療子癇前期的潛在作用和機制,可作為一個未來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