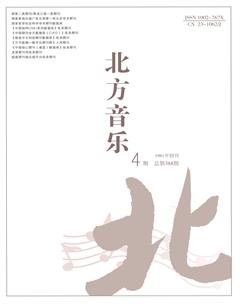淺析人聲及音樂在電影中的作用
【摘要】電影聲音通常被分為人聲、音樂、音響三大類。其中人聲又可分為對白、獨白、旁白、解說詞,每一種人聲都有其特殊的作用,但無非為塑造人物形象、表達人物內心世界、敘述劇情等作用;電影音樂具有創造結構意義的節奏并刺激觀眾的情感反應、概括與暗示主題、表達地點感和時代感以及揭示人物內心世界等作用。
【關鍵詞】電影聲音;人聲;電影音樂;音響
【中圖分類號】J617?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文章編號】1002-767X(2020)04-0233-02
【本文著錄格式】付曉鵬.淺析人聲及音樂在電影中的作用[J].北方音樂,2020,02(04):233-234.
電影聲音的出現對于電影的發展具有強大的推動作用,雖然包括卓別林在內的一大批電影藝術家曾反對電影聲音,但他們卻無法阻止電影從默片時代向有聲片時代的邁進,更無法消除有聲電影帶給觀眾奇妙的觀影體驗。盡管卓別林曾在無聲片陣地堅守,但他也不得不接受電影聲音所帶來的刺激,因而有了他的第一部有聲片《大獨裁者》,然而人類第一次接觸到有聲電影遠早于此。本文將重點討論人聲及音樂在電影藝術中的作用。
一、人聲
通常,電影聲音習慣性被分為人聲、音樂、音響。人聲又被分為對白、獨白、旁白、解說詞。每一種人聲對于電影的作用是不盡相同的。對白是指影片中人物之間的對話,是影片中表現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的關鍵因素。在《海嘯奇跡》中,當盧卡斯和母親想要爬上大樹時,盧卡斯試圖幫助受傷的母親,但卻被母親嚴厲拒絕,此時,盧卡斯和母親之間的對白就明顯表現出母親要強的女性形象。影片中人物性格的塑造最終是要為劇情的發展及主題服務的,而對白在此時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影片《辛德勒名單》中,觀眾通過前面劇情的鋪墊,對于辛德勒有了一定的認識,從辛德勒與會計的第一次對話直接明了地表明來意開始,影片中對白就推動著劇情向前發展。倘若沒有辛德勒與會計之間的對話便不會有故事的進一步發展,因而人物之間的對白對于故事劇情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獨白與對白是不同的,獨白是指劇中人物在影片中對內心活動所進行的自我表述,獨白主要是以角色本身為交流對象的,常用以揭示人物內心世界。在影片《茉莉花開》中,當陳沖扮演的母親和章子怡扮演的茉對話說到茉的孩子像茉以后,茉獨自一人抱著孩子自言自語到:“像我有什么好的,我的命這么不好的。”此處用獨白表現出了茉一方面對于自己命運的感慨,同時也表達了對女兒命運歸宿的期盼;在電視劇《孝莊秘史》中也有大量的獨白,每一次獨白的運用都是人物內心世界的一次自我表達,是讓觀眾明了又不讓劇中其他人物知道的一種表述。另外,當影片中想要表現一個人非正常精神狀態的時候,也常出現獨白。例如魯迅筆下的祥林嫂,當祥林嫂受到接二連三的打擊之后,她的精神已經失常,而此時的獨白一方面是為了表現祥林嫂失常的精神狀態,同時也表現了祥林嫂對于阿毛的思念。旁白是一種獨特的人聲運用方法,由畫面外的人聲對影片的故事情節、人物心理加以敘述、抒情或議論。張藝謀執導的影片《我的父親母親》中運用了大量的旁白來講述招娣和先生的愛情故事,影片中旁白的使用不僅可以使觀眾更加明了故事線索,向觀眾傳遞更豐富的信息,表達特定的情感,從而啟發觀眾對于影片更深的思考,同時旁白的使用對于影片的敘事表達也具有強烈的銜接作用,就如同觀眾經常在影片中看到用字幕對于劇情發展的交待一樣。解說詞和旁白的相像之處就在于它們都是以畫外音的形式出現,所以觀眾經常將解說詞和旁白分不清楚,上文提到旁白是對影片中故事情節、人物心理加以敘述、抒情或議論,而解說詞則是對于畫面中沒有的信息進行補充說明,給畫面定向,明確主體方向,并且解說詞常用于紀錄片中。觀眾在觀看《舌尖上的中國》時,所接觸到的畫外音就是解說詞,此時解說詞的作用一方面是對于片中所呈現的食物制作背景的介紹,另一方面是對于觀眾無法直接理解的畫面的解釋說明。在紀錄片創作過程中,若創作者所要講述的故事背景無法再現,則常常以解說詞的形式來對于背景進行介紹。當然,觀眾經常在紀錄片當中聽到一些聲音,當觀眾無法理解這個聲音的時候,此時解說詞就起到了解釋說明的作用。雖然每一種人聲所具有的功能是不同的,它們所表現的意象也不盡相同,但它們最終的目的是相同的,那就是突出影片主題。
二、音樂
在電影藝術中音樂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是電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電影音樂既有著和純音樂一樣相對完整的獨立性和藝術性,又在電影中起著獨特的作用。總的來說,電影音樂的作用可總結為四點。
詳細說來,第一,故事是電影表達的基礎,電影音樂是以電影故事為載體,在影片中,音樂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故事劇情的不斷發展發生著變化,故事的起承轉合也伴隨著音樂的起承轉合。影片中,往往在剛開始敘事的時候,音樂是較為緩和的,而當矛盾沖突較為激烈的時候,音樂則是緊張刺激的。在李安執導的影片《臥虎藏龍》中,影片開頭音樂較短,這短暫的音樂卻給觀眾制造了中國民族神韻的意境美,用音樂將觀眾帶入影片中,但在玉嬌龍的臥室中,玉嬌龍放下床簾準備入睡,一段秀媚的旋律想起,這是玉嬌龍性格的象征,但就在此時一個黑影閃過,一個蒙著黑面紗的蒙面人到貝勒爺家偷青冥劍,這時候音樂情緒由原本的秀媚一轉成為緊張,此時的音樂給觀眾外松內緊的感覺。在隨后的打斗場面中,使用中國打擊樂器,鼓聲的敲擊速度和力度隨著畫面中的打斗場景而變化,并與畫面中的打斗場景融為一體,制造出緊張刺激的感覺。正因為影片中有不同節奏感的音樂,不同節奏的音樂又創造了具有結構意義的節奏,因而電影故事在本身緊張的基礎上又增色幾分。在電影音樂隨著劇情起承轉合的過程中,電影音樂同時具有著刺激觀眾情感反應的作用。嵇康曾提出“聲無哀樂論”,即音樂本身是沒有情感的,音樂之所以能夠感動眾人的原因在于人們聽到音樂能夠激起聽者內心深處對于過往的想念。電影劇情就如同引起人情感共鳴的事件,在此基礎上,音樂恰如其分的刺激使得觀眾的情感共鳴上升為情感宣泄,情感隨著劇情以及音樂的變化而發生著變化。筆者曾在課堂上向學生播放了短片《媽媽的飯》,當短片最后結尾的時候,學生們被感動地紛紛落淚,但當筆者關掉音樂之后,同學們的情感反應并沒有像有配樂時那么強烈。因而伴隨著劇情的發展,音樂除了創造了具有結構意義的節奏還刺激著觀眾情感反應;第二,電影具有概括與暗示主題的作用。使用音樂來概括與暗示主題是電影常用的表達方式,例如在張藝謀執導的影片《我的父親母親》中,導演用音樂與色彩的相互配合完成了對于影片主題的闡釋,影片用暖色調暗示著父母愛情結局的美好,用低沉的音樂來表現父母愛情過程的艱辛,色彩與音樂的結合暗示著雖然父母的愛情結局是美好的,但也歷經“千難萬阻”;第三,電影音樂可以用以表現時代感與地點感。影片《茉莉花開》分別講了茉、莉、花一家三代女性的故事。影片中使用了三段不同的音樂來表現了三個不同的時間段,影片中鄒杰騎著自行車載著莉在一片金黃的油菜地約會,此時伴隨著兩人喜悅喜慶的是音樂《喀秋莎》,歌曲《喀秋莎》在此時不僅表現了莉和鄒杰內心的甜蜜、投身祖國建設的豪情壯志,同時也交代了故事發生的時間背景為1950年代;影片中間部分,伴隨著“花”和同學們合唱《敬愛的毛主席》的歌聲,時間背景已經到了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此時音樂不僅是劇情的轉折,更是對于時間的交代;影片中第三次出現交代時間背景的音樂是在“花”和男友回城的時候,此時音樂為鄧麗君所演唱的《小城故事》,導演用這首音樂不僅表現了“花”與男友回城的歡喜,也交代了當時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除了時代感,用音樂表達地點感導演交代地域背景的常用手段,影片《紅河谷》講述了發生在西藏江孜的真實故事,曲作者巧妙地加入了很多西藏原生態民歌來表現故事發生的地點。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各個民族都有其獨特的音樂風格,這些音樂出現在電影中為我們判斷影片故事背景提供了依據,例如當我們在影片中聽到信天游,就會不自覺地將其與陜北聯系在一起;聽到蒙古族長調,就會將其與內蒙古聯系在一起;當聽到木卡姆,就會與新疆維吾爾族聯系在一起,這些帶有濃厚地域特色的音樂在傳遞某種特點感情的同時,也向觀眾交代著故事發生的背景;第四,電影音樂具有揭示人物內心世界的作用。影片中除了用對白來表現人物性格,用獨白來表現人物內心世界以外,音樂也是塑造人物性格、表現人物內心世界的重要手段。電影音樂表達了導演及作曲家對于影片中特定人物的理解與態度,對于觀眾而言,音樂的使用可以幫助觀眾更全面地理解人物,使得劇中人物更加立體化。斯皮爾伯格執導的影片《拯救大兵瑞恩》的開頭是老年瑞恩在家人的陪伴下來到烈士墓地,悼念當年為救他而犧牲的戰友們,導演在對一段的處理上沒有使用人物的對白,觀眾只能看到瑞恩神情悲傷的走在前面,家人緊隨其后,這個時候導演使用了一段深情而極富感染力的音樂,企圖用這段音樂來表達瑞恩那時那刻復雜的心情與情感。
三、結局
電影從無聲到有聲是一次偉大的革新,電影聲音的出現推動著電影更貼近于現實,人聲、音樂或是音響,每一種聲音在電影中都有著自己獨特的作用。不管是為了塑造人物形象還是為了推動劇情的發展,電影聲音已然成為電影藝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為電影藝術的發展增光添彩。
參考文獻
[1]葉朗.美學原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2]狄其安.電影中的音樂[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 2008.
[3]彭吉象.影視美學(修訂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4]王培新.電影音樂藝術的審美價值探析[J].北方音樂,2019,39(7):53,58.
[5]王紅霞.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電影聲音技術發展史[J].電影藝術,2018(5):39-45.
作者簡介:付曉鵬(1989—),男,漢族,陜西西安人,昆明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美學專業18級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