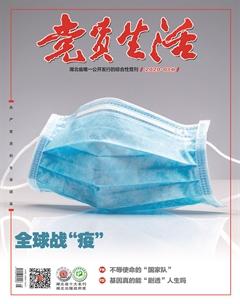能做到65歲的工作越來越少了
馬立明
自人類進入現代社會、建立職業用工制度以來,“畢業后工作、60歲退休”成為一種得到公眾認可的工作制度(在中國,一些男性退休年齡延后到65歲了)。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認為,職業生活被認為是人生命歷程的主要意義,沒有之一。而職業身份,與一個人的自我認知與社會評價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然而,當我們步入全面網絡化的21世紀,突然發現人類的工作模式出現了變化。以下的一些現象,持續地動搖著我們對職場價值的信仰:
1. 在全世界范圍內,勞動的機會似乎在不斷減少。
2. 知識的更新迭代在加快。
3. 高強度的用工模式。
4. 結構性的失業。
這些現象構成了我們社會的新聞圖景:勞動者起早貪黑,風雨兼程,又總是身不由己,甚至事與愿違。各處飄散、枯萎,這似乎是職場江湖的寫照。
有人將失敗歸結于個體的不努力,但這難免有點簡單化。遭遇職場困境的,不乏非常優秀的人,包括“985”的碩士、博士,還有曾經有過輝煌實戰經驗的“老江湖”。當此類事件具備一定普遍性之后,它已經具備了社會學意義——它指向的是,我們的社會處于一個什么樣的階段,勞動者到底該如何自我定位?
必須認識到,我們已然進入一個看上去很美,但實際上很荒蕪的后工業時代。隨著自動化與人工智能的深化,作為社會中最主要的職位提供者之一的工廠,能提供的就業機會已經大大減少。依托互聯網進行的創新產業、文化產業、服務業、金融業等行業,被認為是新經濟的代表,也是后工業時代的入口。
這種后工業時代,盡管很環保、很便利、很“輕”,甚至創造出一些令人震驚的財富神話,但是也隱藏著極高的風險。烏爾里希·貝克曾經預言這種工作體制的風險性,因此他在《風險社會》中提出,工業社會逐漸消亡,新的“風險社會”日益凸顯。
而新經濟是否能規避這種風險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后工業時代,事實上很難復制工業時代的大規模生產。當集體化大生產讓位于原子化的小作坊,在實現了“人的解放”的同時,也意味著人進入懸空的狀態。懸空狀態的特征是什么?似乎人人都能輕易找到一份工作,卻不知道未來在哪里。大量的勞動人口,慌張地面對著職業的不確定性。
人類是需要確定性的動物。看起來充滿機遇,但欠缺持續性的后工業時代,事實上并未讓一個人變得更舒適,相反,它進一步加深了人們的焦慮感。
大量青年徘徊在新經濟的入口處,嘗試找到迅速變現的方法;而找到變現方式的中年人,則受困于不可持續發展的狀態,遭到了失業的威脅;即使是成為網紅的幸運兒,也在思考過氣之后如何自保。
有研究人工智能的專家樂觀表示:未來的世界,工作交給機器去做,人類就不需要干活了;人類可以從事藝術、文學等創造性職業。這看起來是美好的愿景,但是,這些職業能帶來實實在在的收益嗎?他們的作品就一定有市場嗎?更進一步說,“不被需要的人”同時也變成了“沒有價值的人”,他們的價值怎么體現?對于大部分只適合程序化勞動的人,其未來何去何從?
后工業時代并沒有一個清晰的藍圖,因此它在帶來愿景的同時,也在制造著惶恐與焦慮。越是智能的技術,越成為確定性的夢魘。至少,種種跡象告訴我們,可以干到65歲的工作越來越少了。
摘自《騰訊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