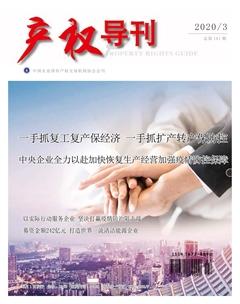技術會把人類本身送進博物館嗎?
禾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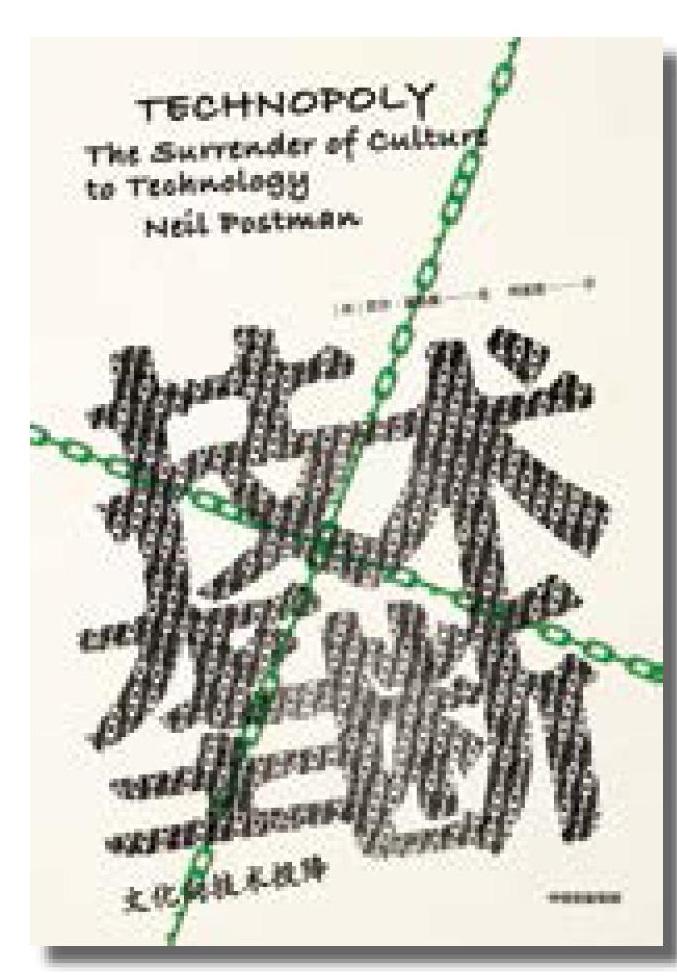
沒有人比家長更能體會到咄咄逼人技術帶來的傷害了——越來越多的孩子對眼花繚亂的智能手機游戲缺乏自控力——孩子們就像是智能時代的“小白鼠”,因為手機,家長與孩子間的矛盾越聚越多,最后如火山爆發滑向極端的例子亦不鮮見。然而,盡管許多家長對此深惡痛絕,但技術界依舊麻木不仁,反倒在追求更能令人著迷的軟件上一路狂奔。
作為美國媒介環境學派精神領袖人物的尼爾·波斯曼,其聞名權因典型的批評風格。1982年尼爾出版了《童年的消逝》,對電視文化狂泄炮火。1985年他又出版了《娛樂至死》,將矛頭對準低俗化、淺薄化的大眾娛樂。1992年他推出這本《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志在給那些技術狂熱者一記悶棍。在這本書中,尼爾痛陳技術壟斷就是“文化的‘艾滋病”,直陳“技術壟斷是對技術的神化,也就是說,文化到技術壟斷里去謀求自己的權威,到技術里去得到滿足,并接受技術的指令。”
“他們用笑聲取代了思考”
技術真的有那么可怕嗎?尼爾的答案是肯定的。
尼爾預見到了技術的快速發展,但無法想象出技術對社會帶來的深刻變化。別只顧指責孩子們對智能手機的依賴,成人對于手機的迷戀亦走火入魔。曾有人試驗,當把手機從身邊拿開后,情緒很快跌落到極點。
毫無疑問,技術發展大大改善了人們的生活。但技術讓人們越來越方便的同時,也讓人比以前更加忙碌,壓力也更大。過去尚有余暇與爸媽在一起吃飯聊天,現在得“找點空閑”,才能“回家看看”。
早在1931年,英國作家阿道司·赫胥黎就為人們描繪了一個未來被技術牢牢掌控的社會。在赫胥黎描繪的未來世界里,科學技術高度發達,但絕大多數人卻無法逃脫這樣的尷尬命運:從胚胎受精到日常工作,從生活到娛樂,一切在嚴格的科學技術規制之中,井井有條的背后讓人感到一種不寒而栗的僵硬氣息……更讓人感到可怕的是,生活在那個世界里的人大都認為這就是人生的本來面目,自己的生活就是幸福的模樣。
而在更為極端的科幻作家看來,如果不能得到更好地約束控制,智能技術或將反客為主,將人類改造成自己的工具。屆時,在智能“生物”(人工制造但通過技術實現自我不斷改進)眼里,人類只有大腦勉堪使用。如此說,未來人類能夠留在這個世界上的或許只剩下一個個使勁販賣思考苦力的頭顱。而完整的人,或許只有在博物館福爾馬林的溶液里偶可觀瞻。
腦洞大開的好萊塢科幻電影,早已設想了諸多驚悚的未來,雖然每次人類最終戰勝了智能,但我們無法預知,技術發展是否真的會遵從人類書寫的腳本。在談到未來那個科技高度發達的“美麗新世界”時,赫胥黎一針見血地指出,“人們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聲取代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笑以及為什么不再思考”。
尼爾認為,技術壟斷將會導致“信息的失控、泛濫、委瑣化和泡沫化使世界難以把握。人可能淪為信息的奴隸,可能會被無序信息的汪洋大海淹死”。今天的現實早已印證了尼爾的預言:十幾年前信息尚屬稀缺品,反窺當下,信息早就泛濫成災。美國統計學家納特·西爾弗曾在《信號與噪聲》一書中指出,在大數據時代,“人類一天創造的內容甚至超過人類有史以來的所有內容”。
今天技術對人類深度影響的案例比比皆是:有人開車跟著導航走,結果掉進溝里、闖進田里,更有甚者卡在鐵路上。隨著5G時代的快速切入,無人技術的廣泛應用,人類未來必將越來越多的工作交給智能機器,自此也進一步切斷了人類與自然間的直接聯系。
如同溫水煮青蛙,技術在改善人類生活的同時,人類對技術的依賴必將更加強烈,這意味人類祖先積累的自然生存本能也會加速消退。未來的人類也許會蛻變為一種嚴重依賴各類技術的“恒溫動物”,整日龜縮在技術打造的“恒溫箱”里。
“周圍滿是獨眼龍似的先知”
許多人有過這樣的體驗:前往醫院看病,哪怕一個極為普通的病,醫生也會開一大堆化驗單。患者認為這是加重醫療負擔,但站在醫生角度,只有窮盡這些手段,才可能逃避誤診漏診醫療責任。尼爾借此案例導出,技術正在影響并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即思考問題的方式不再從人性本身出發,而是基于技術角度的考量。當人性讓渡于技術,意味技術正朝著凌駕人類的方向肆意狂奔。
就技術如何改變人類的思維,尼爾打了幾個形象的比喻。“1500年,即印刷機發明之后50年,歐洲并不是舊歐洲和印刷機簡單的相加。電視問世之后的美國不只是美國加電視的美國”。每一種新技術的出現,都是舊技術與社會的脫鉤,新思維的嵌入。過去我們有輛自行車就覺得已經夠快,現在坐上了高鐵,還希望研制出跑得更快的高鐵——“快”字內涵隨著技術的突飛猛進,也快速顛覆著我們的原有生活習慣。
尼爾指出,“每一種工具里面都嵌入了意識形態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種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種方式構建世界的傾向,或者說它給一種事物賦予更高價值的傾向;也就是放大一種感官、技能或能力,使之超過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的傾向”。新技術的思維誤區,根本一點在于人類對技術的選擇性審視。在資本的助推下,技術收益被放大,其負效應則被淡化或者無視,尤其是對人文影響的負效應。因之,尼爾的批評尖銳刺耳:我們身處狂熱特烏斯們的包圍之中,周圍滿是獨眼龍似的先知,他們只看到新技術之所能,卻想不到新技術幫倒忙的后果。
也許有人會質疑,每個人自呱呱墜地之時起,便陷入技術包圍圈之中,難道過去就沒有技術壟斷憂慮嗎?這當然是尼爾思考的問題之一。尼爾將人類技術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即工具使用文化、技術統治文化和技術壟斷文化。對三個階段,尼爾作了清楚地界定,即“工具使用文化從遠古到17世紀,技術統治文化濫觴于18世紀末瓦特的蒸汽機的發明(1765年)和亞當·斯密(國富論)的發表(1776年),技術壟斷文化濫觴于20世紀初”。尼爾把當時已經高度發達的美國看成是“唯一的技術壟斷的文化”,并斷言,未來將有更多國家會加入這一陣營。
無論是工具使用還是技術統治時代,技術與人類還是依附關系,人類主導地位牢不可撼。技術壟斷時代則不同,智能技術的突飛猛進,早就打亂了人類既有的想象空間,許多時候人類來不及思考,新的技術已經鋪天蓋地而來,新技術正在悄然占領主導地位,而人類也在悄然淪為技術的“奴隸”。至于技術壟斷之后還有什么文化,尼爾沒有進一步交待,也許在他看來,如果技術壟斷趨勢不加以扭轉,人類將會被技術套牢,后果不堪設想。
事實上,所有技術是對大多數規律的觀察總結,也就是說沒有百分百的技術。或者說,基于概率學,大多數總是人們關注的重點。不過,對這種大多數,曾出版《概率論》的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并不認同,反倒認為,“概率的本質是不同事件之間的邏輯關系,這種關系并不是一個確定的東西,更不可能是基于不簡單的數字來衡量。要理解概率,只能訴諸理性,而歸納得到的信息充其量只能為理性的信念提供參考,而不能成為概率本身”。
尼爾擔心,技術壟斷有朝一日成為顛覆人類的奇點。確實,既然沒有技術能夠做到百分百的完美,那么各種技術難以避免的缺陷,會不會聚少成多,最后因藕合效應放大缺陷,至而成為孕育奇點的沃土呢?
“技術壟斷的故事沒有一個道德核心”
尼爾的這一論斷擲地有聲。在他看來,技術壟斷過于“強調效率、利益和經濟進步。”當技術與這些賦予所謂文明或幸福內涵的指標緊密聯姻時,彼此便會唇齒相依,抱團發展,至而忽視技術應當蘊含的人文內涵。
尼爾忠告人類,“一種新技術的利弊長短不會勢均力敵”。關鍵還在于,許多時候人類對于新技術利弊并沒有真正做好思想準備,人文學科沒有跟上新技術的發展節奏。如核技術既可以為人類帶來難以想象的清潔能源,同時也可為人類的自我毀滅埋下禍根。雖然核能和平應用越來越廣泛,大國核武庫表面也得到控制,但核擴散風險始終未見消減,核武技術發展也從來沒有停歇。
再比如,短短數十年,互聯網技術發展實現了巨大飛越。回過頭看,互聯網所帶來的似乎只有技術二字,互聯網本身對于其可能給人類帶來的負面影響缺乏自制力,如前面所講的令無數小孩深陷其中的手機游戲。前幾年,社會對網癮少年尚且給予高度關注,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問題雖然有增無減,質疑聲音卻已消停。
對于人類正在墮入的技術壟斷魔癥,尼爾認為當務之急是重建人文學科,讓“人文”二字成為技術發展的內核,這也就是尼爾所說的“道德核心”。為日新月異的技術裝上“道德”內核,讓技術充滿濃濃的人性溫度,這是尼爾所期待的未來。尼爾告誡世人,當“我們容許一種技術進入一種文化時,就必須要瞪大眼睛看它的利弊。”
這種審視思維不只是當前流行的所謂可行性研究,而是上升到人文學科層面。不過,現實的最大困難在于,著重于精神修煉的人文學科對許多人而言似乎太過虛無縹緲,反倒是沉甸甸的物質更實在、更令人有一種想要擁有的沖動。
困難很大,但至少我們開始正視這一難題。還有一點也很重要,那就是在技術發展的同時,非常需要有人放慢腳步,靜心思考。只要人類沒有放棄思考,赫胥黎描繪的那種新世界就不太可能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