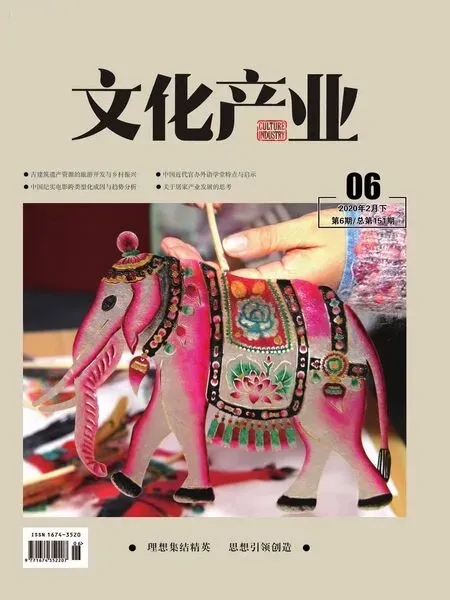中國紀實電影跨類型化成因與趨勢分析
◎王廣振 王 洋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山東 濟南 250100)
近年來,中國電影市場發展勢頭強勁,中國電影發展的現實主義傳統已經不再僅僅局限于第六代導演,許多影片開始呈現出強烈的紀實主義風格。如《我不是藥神》《紅海行動》《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這些受到市場歡迎的影片都是基于真實事件改編而成,事件和人物原型皆來源于現實。而這些紀實影片也擺脫其單一的“紀實性”,開始與類型片的敘事方式相結合,呈現出跨類型化的特征。
跨類型化是電影類型化研究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即類型混合和類型借用[1]。在中國跨類型化的現象中,最突出的即為“跨類型喜劇”,即借用喜劇片的詞義元素和句法規則,實現某一類型片的事件推動。如電影《我不是藥神》來源于真實事件,用藝術化、娛樂化的手段直面社會現實中的敏感話題,強化、突出矛盾。
對于紀實電影而言,其對于某些議題的深切關懷在一段時間內,并不會產生太大的變化,甚至原封不動。但是在形式上,這部分電影會不斷引用、借鑒其他類型電影的內在形式實現自身意識的增長,并且在這個過程中逐漸衍生出自身的一種程式。紀實電影跨類型化的過程與其他典型類型電影相比,在表現靜態人文關懷的同時,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動態吸納系統。一般的電影研究者認為,一種電影類型一旦建立起來,它會暫時穩定下來,而紀實電影的動態特征則在歷史研究中極為突出。
一、紀實電影跨類型化發展現狀
紀實電影與客觀世界相對應,本身就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內涵,其實就是脫胎于現實主義題材的電影類型。真實事件是電影創作的重要資源,紀實電影以事件為藍本改編而成,在尊重客觀事實的基礎上注入創作者的主觀想法和意愿,運用電影的技術手段和某些虛構元素,實現事件的重新組合。創作者通過跨類型化和電影技術手段對事件細節和人物心理進行虛構,即將嚴肅的政治事件用娛樂化的方式表現。
中國的紀實電影發展歷程與現實主義傳統密不可分,其歷史最早可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的《閻瑞生》,第一代電影工作者通過社會新聞的極大影響力以保障影片的觀影人數;20世紀30年代興起的“左翼電影運動”推動了“革命現實主義”的發展,出現了一大批具有強烈社會批判藝術的影片;經過60年現實主義傳統的發展,中國第六代導演對現實生活的反映和社會問題的諷刺批判已經發展為較成熟的模式。
新世紀以來,中國紀實電影的商業化程度進一步加強,這得益于中國第六代導演對中國現實主義題材電影的進一步延伸和發展。

中國導演的現實主義傳統
在主旋律電影上,由香港導演林超賢執導的兩部電影《湄公河行動》和《紅海行動》在票房上表現最佳。國慶期間上映的《我和我的祖國》建構在建國后7個重大歷史事件背景之中,以普通人的視角來講述我們與祖國之間的聯系。此外,《建國大業》《南京!南京!》《建黨偉業》《百團大戰》等根據中國建黨、建國的歷史事件改編的主旋律電影也都在尋找新的表達方式。
除了主旋律電影外,新世紀關于犯罪類題材的紀實電影也得到了觀眾的關注。早期影響力最大的是導演李楊拍攝的《盲井》和《盲山》,影片分別以1998年的礦井殺人案和1994年的“鄭秀麗被拐事件”為原型改編,其中《盲山》摘得2003年柏林電影節的個人貢獻銀熊獎。其后,“打拐”類型的電影興起,《親愛的》以2011年民工彭高峰尋子為原型,上映后獲得3.45億票房;彭三源編劇并執導的《失孤》以“雷澤寬尋子15年”為原型,由劉德華和井柏然出演,最終獲得2.16億的票房。導演高群書一直聚焦于真實事件的改編,由其執導的《千鈞·一發》《西風烈》和《神探亨特張》都是改編或取材于真實事件或人物,其中《神探亨特張》根據便衣民警張惠領的事跡改編,獲得第49屆臺灣金馬獎最佳影片獎。
其他犯罪類紀實電影有的取得票房上的成功,有的飽受爭議引發社會討論但卻票房寥寥。《左右》由王小帥導演,影片沖破了傳統的家庭倫理觀念,獲得第5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銀熊獎最佳劇本,但在國內卻僅僅收獲了200萬的票房。《解救吾先生》改編自“吳若甫事件”,最終收獲1.96億的票房,實現了票房和口碑的統一。
對于“第六代”導演而言,他們更加喜歡在客觀的電影鏡頭前解構真實事件,用直白的影像方式批判或贊美生命。“觀眾在看電影時所體驗到的幾近真實的情景,絕對比閱讀小說、觀賞戲劇或欣賞人物畫為甚。”[2]紀實電影來源于現實,更能提供給觀眾最直觀的沖擊,喚起情感的共鳴。而紀實電影的跨類型化使得其不僅是現實的漸近線,而且成為面向大眾生產的文化產品。
二、紀實電影跨類型化成因分析
在2019年國慶期間上映的影片中,具有紀實性質的《我和我的祖國》和《中國機長》獨占鰲頭,進入中國內地票房前十名。紀實電影逐漸升溫,究其原因,紀實電影逐漸轉向類型片方向發展的起因可以歸為三個方面:
(一)內容為王:事件故事化與故事生活化
從內容上看,真實事件本身具有改編成電影的因素,包括敘事性結構、戲劇化表達等,真實事件改編成的電影同時更能取得觀眾的認同感、更加貼近觀眾的生活。
1.事件故事化
由于故事化的真實事件與電影故事之間具有相似之處,兩者都具有極強的故事屬性,所以電影中的人物關系和敘事情節可以取材真實事件。通過對真實事件的挖掘,導演可以找到足夠多的細節成為電影故事的基礎與刻畫人物心理的重要原材料,對事件的戲劇沖突轉換有著更完整的邏輯框架,故事也更貼近生活。
“電影觀眾是在一種恍若如夢的狀態中注視著銀幕上的畫面的。”[3]觀眾接觸到的物質世界是具體而真實的,通過一系列的偶然事件和分散的物象形成對現實的體驗。電影表現的主體部分就是物質世界的細節,真實事件擁有著更多物質世界的細節,當其被改編成電影時,就成為電影懸念和沖突細節的重要元素,觀眾通過銀幕得到的畫面和事件過程,再加上自己的推斷和理解,形成了完整的故事情節。
2.故事生活化
故事生活化即事件對觀眾生活的貼近性,影片改編的真實事件大多是新聞報道,人們更方便在故事中身臨其境,也更容易與時代背景、熟悉的社會場景相聯系。《親愛的》改編自“彭高峰尋子故事”,自新聞報道之后在社會上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力,在微博上也被多次轉載。正是因為觀眾在心理上對“尋子”的貼近感,才能使得觀眾置身于真實事件之中,引起觀眾的共鳴。
“社會體驗并不受文本的控制,它決定了文本與社會關系的結合,并驅動大眾的生產力。”[4]美國大眾文化理論家約翰·費斯克針對大眾文本提出了“生產者式文本”的觀點,電影即是這類生產者式文本,它們并不是意義封閉的文本,觀眾能夠輕松理解電影文本中的意義,并在電影消費過程中生產出自己的意義和快感。《我不是藥神》觸及醫保問題,這是與每個人息息相關的,觀眾對電影故事會有自己的理解和感受,產生解決社會問題的破冰效應。
(二)媒介融合:資源互文性與信息視覺化
從傳播媒介來看,媒介融合的狀態下,事件作為一種資源可以在媒介世界中共享并產生互文結構,使得電影成為表現社會現實的重要方式,同時電影作為視覺化的產物,在讀圖時代更能取得觀眾的青睞。
1.資源互文性
在信息化時代,信息以開放式的形態普遍存在,通過資源傳播方式的相互滲透,實現信息資源的共享和廣泛性的覆蓋。事件與電影的共享實現了內容上的融合。制片人在主動挖掘事件的同時,將電影進行跨類型化的處理,將電影作為媒介傳播中的重要平臺,實現事件的更廣泛傳播。媒介融合實現了事件與電影生產的互文性,從而形成大眾文化的完整文本。
真實事件作為大眾文化原型是資源初級文本,改編電影是資源和信息在文本基礎上的拓展和意義延伸。“所有的文本都是不完整的,只能在互文關系和接受模式中加以研究。”[5]《我不是藥神》的改編,讓社會關注到醫保問題,關注到慢粒白血病,引起社會對醫患關系的再思考,實現了事件的再發酵。
2.信息視覺化
信息爆炸的時代,人們在讀圖心理的支配下,將視覺感官放在重要位置。信息急速傳播帶來的是人們心理疲勞程度的加劇,因而人們更加傾向于快餐式的閱讀,選擇更加直觀、簡單而形象的視聽信息作為了解世界的重要途徑,所以圖像成為人們獲取信息、傳遞信息的特殊方式,類型電影恰恰迎合了信息受眾的娛樂本能,影像媒介成為文化消費主體最受歡迎的選擇。
理查德·厄爾豪斯認為:“通過電影,我們將進入第四維度:時間維度。雖然形象藝術常常試圖創造三維幻想,但大多數情況下它依然呈現的是一個二維的視覺效果。攝影無意識地創造了三維幻想,但電影進入了第四維度,因而走的更遠。”[6]在電影中,出于敘事的需要,影像不僅可以將媒介的特性發揮到極致,同時事件的某種因素可以被凸顯或削弱,放大觀眾的感官刺激。在《紅海行動》中,導演在敘事過程中將人文情懷和戰爭元素轉變為視覺因素,《我不是藥神》將事件轉變為犯罪片的戲劇沖突,吸引對事件感興趣的觀眾進入電影的四維空間中。
(三)市場主導:成本優勢性與風險可控性
電影跨類型化本身就是為了推動商業化,而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是節約成本的有效途徑。首先,對真實事件進行跨類型化電影改編可以降低成本,同時,紀實電影大多為劇情片,事件源于現實空間,需要重新架設的電影空間較少。電影制作方更希望在創作階段就使用成熟的故事和成本更低的紀實風格來達到節約成本的目的,紀實電影為其提供了絕佳的選擇。《親愛的》以簡單的視角和貼近生活的場面設置,使用不到2000萬的制作成本,取得了2億的國內票房;《我不是藥神》制作成本雖然過億,但其票房突破28億,凈收益達到10億以上。
改編電影不同于劇本創作的電影,它以真實生活為基礎,通過填補電影市場空缺而獲得市場地位。真實事件改編作為電影的標簽,在熒幕上進行藝術再現之前甚至創作之前,就已經經過市場的一輪檢驗,事件本身就已經通過文字或者口頭傳播被廣泛宣傳。換言之,了解事件的觀眾已經成為電影的已存市場,他們會成為電影的關注者,即使他們沒有走進電影院,一個經由市場檢驗過的事件相對于架空的劇本而言,它的風險已經大大降低,這也與文學作品改編電影的潮流相符合。
在電影出現之后,觀眾會對電影產生“移情”效應和好奇心理,將對文字的熱情轉移到電影的快餐式消費文化中,在兩個小時后獲得娛樂和認知的快感。所以說,由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其實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通過了市場的淘汰機制,它在市場上流通時的風險也是可控的。
三、紀實電影跨類型化發展趨勢
紀實電影在跨類型化發展過程中,從關注底層邊緣人物發展為關注普通大眾,從反映社會現實發展為調動觀眾的情感體驗,從紀實性電影逐漸發展為動作片、犯罪片、戰爭片、愛情片等,主要表現為三個發展趨勢:
(一)選材趨向大眾化
票房是電影市場誕生后形成的伴生物,它使得電影在市場層面表現出影視媒介的“他律性”,即受到觀眾的直接約束和控制,票房使得電影與經濟利益完美地捆綁在一起。
紀實電影作為電影市場的一部分,深受票房“他律性”的影響,其本質上屬于現實主義電影,大都用來描述社會底層的邊緣人物,而且敘事風格平淡,所以為保證票房的回報率,其在跨類型化的改造中必然選擇具有社會影響力的真實事件,即選材的大眾化,選擇在大眾中能產生廣泛影響力的事件進行戲劇改編。事件影響力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真實事件本身的影響力,二是真實事件觸及大眾生活的程度。
《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屬于前者,“湄公河大案”和“也門撤僑”其事件本身就具備廣泛的影響力,在與犯罪片、動作片、戰爭片等大眾喜聞樂見的類型片跨類型結合后,成為大眾樂于接受的題材電影。后者的影響力主要體現在民生問題,《我不是藥神》能引起如此大的反響,與其觸及醫療的民生問題密不可分。在某種程度上,電影表現的不僅僅是一個事件,而是關系到千家萬戶生活的一部分。
(二)敘事趨向情感化
《嘉年華》《我不是藥神》等成功影片中都飽含著一個與觀眾息息相關的民生問題或社會問題,而像《親愛的》《滾蛋吧!腫瘤君》等影片中雖涉及社會問題,但它們更傾向于表達情感,喚醒觀眾感情的認同感。
第六代導演在現實主義電影制作當中更加傾向于進行個性化的表達,在影片中注入自身的思考和意向,借此來展示中國當代最真實的面貌和最真實的社會問題,帶給觀眾最直觀的認識和反思。而在電影改編進行跨類型化處理的過程中,影片不僅成為展示現實的鏡子,更成為人們情感表達的宣泄地。在公路片《落葉歸根》中,老趙也與宋丹丹飾演的中年婦女存在感情戲;在《日照重慶》中,觀眾感受到了林波對父愛的追尋和對愛情的堅守;在《滾蛋吧!腫瘤君》中,觀眾被熊頓樂觀積極的態度所感染;在《解救吾先生》中,華子作為犯罪片中的“匪”也展現出對母親的愧疚、不舍而決絕的情感;在《嘉年華》中,觀眾痛恨官警勾結,為受害者感到氣憤。
所以,在真實事件改編過程中,導演為獲得票房,在采用類型化的敘事過程中,通過人物心理的展現帶動觀眾的情緒,讓觀眾成為電影的一部分。
(三)內容趨向主旋律
在紀實電影的發展歷史中,主旋律電影一直穩步前進。從最初《驚濤駭浪》等大抗洪事件的改編,到《鄭培民》《沉默的遠山》等對人物事跡的改編,再到《建國大業》《建黨偉業》等建國建黨歷史的改編,最后到如今《我和我的祖國》《紅海行動》等事件的改編,主旋律事件改編的電影一直是宣傳意識形態和社會正能量的堡壘。
2010年前的主旋律電影一般采用紀實風格的敘事方法記錄真實事件或人物,而《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我和我的祖國》等影片不再僅具有紀實的特征,影片的戲劇化改造和跨類型化處理更明顯。導演通過戰爭片、動作片的類型處理展現中國的大國形象和綜合國力,通過兄弟情義和家庭羈絆體現鐵漢柔情。
因此,在國內紀實電影中會出現更多體現中國大國形象和綜合國力的主旋律類型化電影,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良好統一。
四、結語
中國紀實電影在商業化過程中得到了市場的良好反響,并呈現出類型多元化發展的特征。紀實電影在中國本土的成長順應了中國文化產業發展中“內容為王”和媒介融合的總體趨勢,同時也有利于在市場主導的電影產業中規避風險。這些影片將生活中的普遍社會問題帶入到電影市場中,產生了眾多具有強烈紀實風格的亞類型電影,觀眾在觀看影片時帶入自己的情感和思考,對電影的現實關懷傳統以及電影市場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