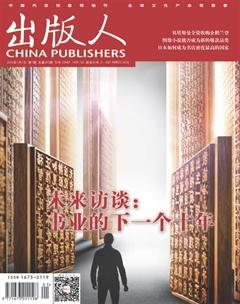王斌:迎接人文精神回歸的時代
黃璜

中信出版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王斌
執掌帥印17年的王斌,代表著中信出版集團的靈魂。在他的帶領下,中信出版社從默默無聞變為中國出版界的一面旗幟,擁有無可爭議的行業影響力。2019年7月,中信出版正式登陸創業板,成為又一家成功上市的出版企業。上市開啟了中信出版新的歷程,也讓王斌更多地思考中信出版乃至出版業的發展,此前接受《出版人》雜志專訪時,王斌提到,“我們要不忘初心,用更大的使命擔當,以目標為導向,讓資本服務于文化產業,認真地去做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事。”如今,站在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的起點上,這位出版業的意見領袖將如何理解未來十年出版?從他口中,或許我們也可以窺見出版業未來的機會。
《出版人》:在一個新的十年即將開啟之際,您如何總結出版業過去的十年?
王斌:總結過去十年應該放到時代的大背景下去看。總體而言,這十年是出版業從傳統產業向現代產業轉型的十年。
放眼全球,出版業在多數國家是一個停頓甚至衰落的行業,但在中國卻呈現出另外一種景象。過去十年,我國出版業的發展令人矚目,它的規模、影響力和繁榮程度都達到了歷史新高。
這十年間不論是大眾出版、學術出版還是教育出版,大家都在探索新的知識傳播形式,以及一切與新技術的融合。雖然到了今天,出版業并沒有形成革命性的產業格局,但是這十年的探索并沒有停頓。這個過程產生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大家對未來有了清醒的認識,那就是出版與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的深刻融合。
這十年里,出版企業的改革沒有停止過,在轉型升級、媒體融合、技術的進步和資本的助力下,一批重要的國有出版企業引領著行業的發展,并已具備國際競爭力。他們的成長壯大,既是產業改革的產物,也是行業發展的成果。在國家戰略和社會效益優先的推動下,出版業進入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
內容的價值在過去十年也得到了彰顯。在信息爆炸和擁堵的大環境中,圖書的生產邏輯和品質使有價值的內容成為稀缺資源。這十年,盡管整個行業面臨多重挑戰,但記錄和回應時代的優秀創作仍然是堅固的核心。我們雖然沒有站在技術的前沿,但我們堅守了生產知識和傳播知識的傳統理想。我認為這是出版業發展的基石。
國際合作的內涵也發生了改變。我們需要維持和世界知名出版機構的合作,尤其是出版巨頭。但這不僅僅是出于單純的商業目的,它同時也肩負著文化傳播與交流的使命。我常在內部會議上說,引進書的時代結束了!我是希望傳遞一個明確的信號,我們要加強策劃選題的能力,以幫助自身生產有價值的本土內容,還要和國際巨頭共同策劃、共同出版、共同講述中國。在這一方面,國家戰略也為我們指明了方向,譬如“一帶一路”倡議和傳播優秀中國傳統文化的理念。
回顧這十年,出版業有探索,也有困頓。比如,缺乏有突破的創新、優秀的新作品不夠、行業整體運營和管理水平不高,人才和機制依舊是短板,技術的應用依然不足。
《出版人》:面向未來,您認為哪些因素是中國出版業的基礎?
王斌:第一個是出版品種和規模。中國是出版大國,要有與之匹配的豐富的圖書品種,這是天然的需求。另一方面,大眾出版的不確定性表現在每一本書都是一次風險投資,因此通過擴大品種來降低風險,是其內在的生產規律。它同時也給行業帶來奇妙的活力。過去十年,書業品種的快速增長有低效和同質化等問題,但品種豐富也激發了創造力,擴大了規模,提高了競爭力。我認為這是發展的基礎和優勢。
第二是領頭企業的成長和壯大。十年的改革發展已經造就了一批優秀的出版企業,而他們也將影響產業未來的走向。出版是社會效益優先、兼顧經濟效益的行業,這意味著出版企業要考慮的是更長周期的事,要有強大的生存能力和發展能力,避免短視和平庸。同時,大企業可以整合更多的社會資源,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大企業具備更強的容錯和糾錯能力,而出版就是要在不斷的試探和糾錯中孕育和培養豐富性。此外,大企業更有魅力吸引優秀的人才。基于這幾個因素,我認為具有典范作用的大企業是出版業未來發展的重要支柱。
第三個是新時代的敘事。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下,文化影響力變得越來越重要,對經濟、社會和未來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國家戰略和對時代的敘事能力已經成為新的競爭力,成為未來行業發展的新動能。未來,出版業的大環境與過去十年會有顯著不同,過去核心是產業化,通過自身改革所釋放的活力推動產業發展,未來則將是國家戰略推動行業的發展,通過敘事釋放的文化影響力最大化地服務于社會、服務于經濟、服務于大眾。
《出版人》:您認為圖書或者出版在未來十年的核心價值是什么?
王斌:下一個十年出版業的核心價值將會體現在兩股強大力量的并存里。一是印刷機的力量在未來十年依然強大,它代表的是人文精神,是人類歷史中那些閃光的、傳承的強大力量。當中國經濟開始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我們將更需要人文的力量,需要在歷史中學習,需要從更高的層次去安放內心。圖書價值會在這里進一步體現,出版會變得更優雅、更古典、更堅實。我經常在內部和編輯說,我們要準備好迎接人文時代的到來,要堅信書籍的力量會在未來得到更大的彰顯。因為我覺得中國人需要精神的回歸,中國社會需要沉淀。我認為只有人文精神能解決這些問題,這也是下一個十年的核心價值。
另一種力量是數字網絡代表的創意和創新力量,這是未來活力的源頭。印刷機的力量很強,它催促人們去閱讀和思考,以數字網絡為代表的技術力量在改變了人們的閱讀習慣和思考方式。這兩種力量不是分化,也不是博弈,而是互補和激發。不能忽視的是,連接這兩股力量的是人。人才仍然是未來十年出版業發展的核心價值。一定要培養具有行業洞見和國際視野的人才,他們擁有先進的商業理念、經營管理能力,以及對古典和新技術的充分理解。
《出版人》:關于紙書會不會消失我們已經討論了20年。如果未來臨界點到來,出版企業要面臨的是生存問題還是發展問題?
王斌:出版尤其是大眾出版的數字化在中國是特別緩慢的過程,要經過好幾代才能完成。我認為下一個十年紙書依舊不會被顛覆,更不會消失。不論技術怎么發展,紙書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不會離場。
出版業與互聯網一直糾纏競合,回望十年前、二十年前,出版人有一種“防御心”,覺得“狼來了”,互聯網則覺得自己可以輕易地顛覆出版業,那時候雙方充滿“生死敵意”。隨著時間推移,雙方發現都奈何不了對方,出版業發現對方其實是個機器人,根本咬不動,互聯網則覺得一拳是打不死出版業的,可能要一萬拳。大家就開始僵持,但是僵持的過程中也是一個重新認識彼此的過程。我們講生存,其實考慮的是成本,如果成本足夠低,那就一定出現一方把另一方吃掉,如果成本足夠高,一定會達到均衡的狀態,再往后就是融合。雙方在僵持中突然發現說咱倆其實可以一塊過,你能幫我賣書,我有些內容你也可以拿去玩。到今天,書業一半以上的銷售都在網上,數字化程度雖然低,但沒有什么書是網上看不到的,盡管可能是盜版,從這個角度來看,紙書與數字出版已經開始在融合階段了。

從企業的角度來說,未來少部分企業面臨的是發展問題,大部分企業面臨的是生存問題。中國經濟高速發展這么多年,產業基礎和水平都有極大的提升,但用先進的現代產業體系標準來看,我們還處在一個較長期的發展階段,對于出版業更是如此,很多企業在這個過程中面臨的更多的不是發展的問題,是生存的問題。
《出版人》:對于涉足內容的互聯網公司,出版業應該普遍采取怎樣的態度?競爭、合作、依附或是其他?
王斌:出版業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我們不能用傳統工業化時代的邏輯做書,把它銷售出去就結束了,正如凱文·凱利所說,圖書應該是一個流程,每本書都是一個影響力中心,應該聚集用戶、關聯用戶。所以,出版業的新經濟模式一定要把讀者變成用戶,然后為用戶精準地提供內容和閱讀服務。
這件事其實是痛苦的轉型,首先要充分利用互聯網和數據等技術手段,其次要改變業務模式,還要具備服務能力。但這些基本問題解決之后,出版業會煥發更大的生命力,以其思想、知識和高品質的內容重新獲得用戶的注意力,在社會重新形成新的影響力。我們發現,這個過程和互聯網企業的發展方式和發展路徑是不同的,當移動互聯網變成基礎設施之后,垂直的獨特的內容企業會更有價值,這是一個相互融合發展的過程,又是一個涇渭分明的不同理念和發展模式。所以我們不會去依附于互聯網企業。回到企業層面,一定會有千億市值的出版企業,一定會有具備世界影響力的文化企業出現。這是時代給予出版業的機會,相信出版業一定能夠對時代做出回應。
《出版人》:人工智能、區塊鏈、物聯網、AR/VR等時下備受關注的新技術,您認為哪一項會對出版行業帶來最直接、最革命性的影響?
王斌:所有的技術都會對出版業產生影響,這是大前提,但我個人認為,真正的人工智能會對包括出版在內的內容產業帶來深刻的乃至顛覆性的影響。我是人工智能最堅定的擁躉,我相信人工智能在很多領域完全戰勝人類指日可待,而這,也恰恰反向印證了人文精神的價值。
人工智能和人腦一樣,一開始也像一張白紙,通過看、讀、聽、學,通過視網膜反射到大腦皮層,產生記憶積累,形成了思維方式和知識儲備,具備了一定的思考能力。過去我們講人工智能,比如說無人駕駛,是先把地圖精準到網格,再把所有的數據抓過來,規劃出最佳路線選擇,再給車裝傳感器,讓這車跑起來。這種理念已經被迭代,現在則是自我學習、 自我訓練的過程,是把一張地圖的數據交給人工智能,讓它自己跑一萬次,和人一樣,進行自我學習、自我反饋,不斷完善和不斷進步。因此,我堅信對出版影響最大的是人工智能,它將改變我們看待世界、看待自我的邏輯和定式,人工智能突破了人類的局限,這種影響會在下一個十年逐步地凸顯出來。
中國出版業有上百萬種書,這是大數據,這個大數據如果只是產品數據,數據量也不大,但如果是內容、文本、語義的數據,那就是海量數據,如果我們用神經網絡的方式將這個數據疊加上去,意味著我們可以提供一個最好的人工智能和數據庫,我們現在所習慣的點對點單對單的服務方式一定會被影響。這種改變什么時候會到來?當技術成本低到企業可以商用時,行業就會改變,而當它高到無法變的時候,它會引領我們的理念,會有先行者去嘗試。
《出版人》:中信出版做了哪些面向未來的布局或嘗試?
王斌:中信出版在中信大廈89層做了一個“數據雕塑”的項目,一個緩慢流動的雕塑,這是一個集數據、創意、技術和藝術的項目。這個作品的數據的采集和所模擬的內容可以是內容、符號、統計……這些模擬的數據可以來自一年四季的風,可以是中信書店采集的閱讀數據,或者是社會調查等,數據在這里重組,被圖像表達出來,模擬成雕塑展現在墻上,這樣,內容的數據不僅變成了可視化信息,而且還轉變了我們對理解的渴望,轉化為一種詩意的體驗。
這就是人文地理,技術能夠將人文思想實現出來。就像這個數據雕塑一樣,我們現在也可以在把書放進屏幕,通過神經網絡的方式來展現,比如用中信銀行當天的交易數據來做影響變量,這就厲害了,意味著你看到的或者感受的東西是跟你的客戶在一起的。它既是具象的也是抽象的,但這種美感和不確定變化,其實是一種哲學,一種人文,強調著與人類追求無限可能性有關的技術,藝術與自然的共生相互作用。
中國文化中有大量的東西可以用這樣的手段去表達,使他們可觸達和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這種出版就是內容的活化與再造。所以我說未來人文精神還是第一位的,它是技術活力的來源,但它又需要技術去實現。技術時代需要人文的參與,沒有人文,那將是枯燥甚至無意義的。
我們在響應國家“一帶一路”倡議,也在考慮這樣的一些項目,真正能夠跟其他文化建立理解的是一些共同語言,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幾千年傳承下來的歷史,我們要用現代語言去表達出來,用人文的精神、態度,用技術去實現,這是我們要做的。
《出版人》:出版業還會有“風口”嗎?下一個大的機遇會在什么領域?
王斌:我們期待的爆發式增長的風口,下一個十年也許不會再有了,不會再有那種八九級可以“把豬吹上天”的大風了,但是會有三四級的風一直吹拂。我對未來的出版秉持樂觀態度,認為這是這是未來十年的一個主色調。從更深刻的角度去洞察的話,未來十年中國社會會有人文意識的覺醒、整體素養的提升、社會的學習成本下降、跟經濟的融合會更密切,出版的價值和作為會更大一點、更合時宜一點。所以出版還會持續地發揮作用,正如我們當年一樣,民眾對圖書的饑渴帶來了產業爆發,只是現在這種缺失需要長線喂養,不會再猛烈爆發,但會一直持續。
基于這種邏輯,未來十年書店會是一個非常精彩的故事。如今書店還處在低迷階段,低效且展示價值有限,很多書店都要關門了,但我覺得書店需要借助內容、技術和資本的力量,回到人文體驗和現實生活中去,創新出自身更大的價值。下一個十年,出版產業的格局會通過這兒去改變。有人和我說過“一面書墻毀了出版業”,這話我很認同,書在這里是裝修用的、拍照用的,所以我不贊成所謂“最美書店”的評選,因為其中有太多的誤導,好像一家書店只要裝修得好、設計得好,就是最美了。大家有沒有從書的品質、文化活動的品質和有沒有靈魂去考量呢?估計大家都沒這個興趣。書店需要重生,但不是最炫設計,而是需要回歸到人文本身,回歸到城市,回歸到人的社區生活中。
為什么我們需要回歸?一個經濟體未來最大的發展動力在于創新,創新的根本在于人,人又是通過大城市來聚集的,而大城市的人文環境是這些創意人才的基本要求,人通過美食、戲劇、演出、體驗等得到精神滋養,激發出靈感和創造力。而這樣的人文環境和生態需要培養,這恰恰是書店應該做的。人需要學習,需要教育,通過素質的整體提升來提高人文環境,使得人有創造力,再回饋給整個經濟。而這只有在國家戰略下,去提高中國社會的人文精神與創造力,才能帶動整個經濟活力,國家也才能進入到發達狀態。從這個角度來說,書店的價值遠沒有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