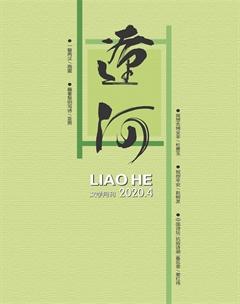一瞥兩漢

商震,1960年生于遼寧省營口市。詩人。作家。出版詩集《半張臉》、隨筆集《三余堂散記》等各類作品集十余部。有作品被譯介到俄羅斯、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國家。現居北京。
呂文之相
呂文這名字太普通了,任何時期把名叫呂文的人聚集在一起都能裝滿一火車。人的名字嘛就是個符號,簡單點兒的易記、易寫,普通點兒的還可以隱于市。
我要說的呂文,其本人也許算是普通,但真不簡單。他是秦朝末年人,據說是呂不韋的侄重孫,是單父人,單父就是今天的山東單縣。呂文原本是當地的一個富豪,因與人結仇,為避禍舉家遷往沛縣。當時的沛縣縣令是呂文的至交好友。
呂文到了沛縣,借縣令之勢辦了一個喬遷大宴,沛縣政府官員、富豪鄉紳均送賀禮前來赴宴。辦宴席簡單,收賀禮安排座位是件麻煩事兒,縣令就把這事兒交給了當時縣政府的秘書科長蕭何。蕭何聰明,為了讓縣令高興就臨時定了規矩,送賀禮不足一千銅錢的都坐到堂下去吃飯,也就是坐到大廳去;一千銅錢以上的人,才能進包廂。這個規定讓當時的一個小吏、泗水的亭長(也就是鄉鎮公安派出所所長)劉邦很生氣,就跑過來故意搞怪。他分文不出,卻在禮單上寫:“賀錢一萬。”蕭何雖然瞧不起劉邦這樣的人,但也不敢惹他,就把這事而告訴了呂文,呂文聽說后心生怒氣,心想,一個鄉鎮派出所長,竟敢在縣太爺坐鎮的宴席上撒野,難道想到我這兒收保護費?他帶著怒氣出來要把劉邦趕走。可是一見到劉邦,倒吸一口涼氣:“我的媽呀!這人咋長成這樣!”劉邦長得啥樣?司馬遷在《史記》上說劉邦“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隆準”就是大腦門高鼻梁,可能還是蒜頭鼻。“龍顏”不好解釋,不能說面部長得像龍。但是“龍顏”這個詞,自從有了皇帝之后就一直被延用,用爛了也用。估計司馬遷也不知道劉邦長得什么樣,那么劉邦是皇帝,皇帝的面目嘛,就是“龍顏”吧。接下來就很具體地說劉邦是一臉大胡子,存疑的是劉邦左腿有七十二個黑痣,司馬遷肯定是看到西漢時的一些史料和傳說寫入《史記》的,但呂文是不可能一眼就看到劉邦腿上有黑痣的。《西漢演義》上如是說:“呂文見邦狀貌,甚奇之,常曰:劉季雖貪酒好色,人多輕之,但時未遇耳!若一發跡,其貴不可言。”遂請其入包廂就餐,后來呂文再邀劉邦到家吃飯時,就對劉邦說:我會看相,你相貌非凡,將來是不得了的人物!并說:我把二女兒呂雉給你做媳婦,你可不能推辭啊!
劉邦被呂文的真誠、熱情、面相學、忽悠術給弄懵了,心說:我還能富貴?還能做人上人?之前劉邦從來沒想過要大富大貴,更不會想到將來要當皇帝。但是,若真能像這呂老頭兒所言,我富貴了,做人上人了,豈不更自由地縱橫酒色、呼朋喚友、天高地遠嗎?好!然后揖手一拜說:呂大叔,您的話我信了,將來我富貴了不會忘了您。只是您這女兒嘛,我不敢娶。劉邦確實沒想過要結婚,那時他已經有一個非婚生子劉肥了。他禮貌地對呂文說:“吾有三事未立:第一,幼而失學;第二,力弱無勇;第三,貧不能自贍。有此三事,豈敢屈公之女耶?”劉邦說的這三件事是真實的,不是推托。但呂文深信他的看相本領,對劉邦說:“吾意已決,愿君勿阻。”
呂文究竟懂不懂面相學?面相學是否真的有這般神奇?我還真不敢冒失。不過,在生活中確實看到了人的面相有差異,善相有善舉,佞人有惡為。“君子坦蕩蕩”就不多說了,君子就是說話清澈,面目透亮、舉止磊落;而一些卑瑣之人的面相,也容易辨識,比如目光游移,表情晦暗,皮笑肉不笑,臉上透著陰氣,等等。但是,貌似君子而內心卑鄙的人,就不是我們這些肉眼可以看出來的了。米蘭·昆德拉說過一句話,原文我記得不準了,大意是:令人作嘔的不是他的相貌丑陋,而是他戴著的漂亮的面具。
若說呂文看了劉邦的面相,嫁對了一個女兒是偶然或傳奇可以理解,歷史故事嘛,大多是不可考的傳說。重要的是呂文又給一個人看了相,又嫁出一個女兒。
沛縣人愛吃狗肉,于是殺狗的屠夫就比較多。其中有一個殺狗的屠夫叫樊噲,來找劉邦喝酒,被呂文看到了。《西漢演義》如此描寫:“呂公相其人,身材凜凜,相貌堂堂,聲若巨雷,暗想此人一盛世諸侯也。”這呂文看相,與擺地攤看相的不一樣,擺地攤的人常說的是:天庭飽滿,地閣方圓,鼻直口闊,雙耳垂輪,等等。而呂文只看這個人的身體強壯,五官周正,說話聲音大,就認定將來要當諸侯。于是,邀其喝酒,開口就說:“請問君有內助否?”噲曰:“某少貧賤,無父母,尚未有配。”呂文說:“我有個女兒已經許配給劉邦了,還有一個在家,就許配給你了。”樊噲雖是糙人,此時也會想:這個老呂頭兒,家境很富裕,還和我們縣長有勾搭,怎么就想把女兒嫁給我們這些不著調、不靠譜的窮光蛋呢?不會是女兒長得太丑或有啥缺陷吧?劉邦看出了樊噲的心事,就勸道:“這個老頭兒會相面,看出來咱倆將來能保護好老婆孩子,你就不用推辭了。”
就這樣,呂文通過相面認了兩個女婿,而且真被他相準了,劉邦真做成人上人,當了皇帝。樊噲追隨劉邦一路廝殺也真做了舞陽侯。劉邦死后呂雉主政,樊噲的老婆呂媭也封了侯,還開啟了外戚專權的先河,呂氏家族一時雞犬升天。
呂氏家族,權傾朝野,也真是風光了幾十年。至于后來被劉氏集團所滅,那是另外的話題。歷史進程的軌跡本來就是這樣:一個族群放肆的瘋狂過后,就是慘烈的滅族之災。
我曾買過一本《麻衣神相》,讀的時候字面意思懂了,但不會操作。拿著書對著鏡子自觀自相,發現沒幾樣能和現實中的我對應得上,看來單憑書本知識是得不出真知的。
呂文的相面術有多高深,不可查考,能看到的記載就是給劉邦、樊噲相過面,而且相得都很準。不能說呂文是碰巧了,應該說,是呂文的社會經驗幫了他,他相信:相由心生。
蘇武之節
在我十歲左右聽媽媽常常哼唱一首歌,叫《蘇武牧羊》。那時,我只知道《王二小放牛》,不知道蘇武是誰,更不知道蘇武為什么要到北海邊去牧羊。后來逐漸長大了,讀到了一些講述蘇武故事的書,才知道蘇武牧羊是怎么回事了。從那時起,就對蘇武肅然起敬。初中的課本里有蘇武牧羊的一篇課文,為了表現出我比其他同學強,就央求我媽把《蘇武牧羊》的歌詞抄寫給我,并跟著媽媽學會了這首歌。這首歌,我現在時而也會哼唱幾句。我把媽媽抄給我的歌詞錄在這里吧,因為現在我看到的這首歌的歌詞與媽媽抄給我的不太一樣。
其實,把霍去病當作民族英雄來敬仰是應該的,當作青年才俊去熱愛是應該的。當作仁義禮智信的楷模是說得過去的,當作一心為國兩袖清風的好干部也是說得過去的。
霍去病深諳兵書戰策,且能靈活運用,十七歲初次征戰即率領800驍騎深入敵境數百里,把匈奴兵殺得四散逃竄。在兩次河西之戰中,霍去病大破匈奴,是個少年老成的軍事家。史上說霍去病是衛青的外甥,其實,霍去病是平陽公主府的女奴衛少兒與平陽縣小吏霍仲孺所生的的兒子。這位小吏不敢承認自己跟公主的女奴私通,于是,霍去病只能以私生子的身份在衛家降世。其父未曾盡過一天當父親的責任。但霍去病長大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有一次出征時順道到了平陽(今山西臨汾)。霍去病命下屬將霍仲孺請到休息的旅舍,跪拜道:“去病早先不知道自己是大人(大人,漢唐時指父親)之子。”霍仲孺愧不敢應,匍匐叩頭說:“老臣得托將軍,此天力也。”隨后,霍去病為霍仲孺置辦田宅奴婢,并在領軍歸來后將同父異母的弟弟霍光帶到長安栽培成材。霍去病從來不沉溺于富貴,將國家安危和建功立業放在一切之前。漢武帝曾經為霍去病修建過一座豪華的府邸,霍去病卻斷然拒絕,說:“匈奴未滅,何以家為?”
以上這些,都是值得我們為霍去病塑像的。唯獨用他名字中的“去病”來暗示自己“去了病”是錯的。霍去病究竟得了什么病,史書上沒有詳細的記載。《史記》:“驃騎將軍去病從軍有功,病死。”這是歷代史書中對霍去病死因的唯一記載。但是,還有一種傳說:匈奴人將病死的牛羊等牲口埋在水源中,使水中滋生細菌,漢軍攻伐在此水源下游飲水,致使漢軍多不戰而亡。這樣的事,史料上是有記載的。大概霍去病也是飲了這種水導致染病,醫治無效身亡。我相信這個傳說。
回到蘭州霍去病雕像的話題上。蘭州是通往西部的重要通道,塑霍去病的雕像,讓大家記住這個民族英雄和青年軍事家是理所當然的。
項羽之仁
司馬遷在《史記》中把“鴻門宴”一章寫得十分精彩。魯迅先生說的“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我想,大多是緣于“鴻門宴”這一章。
眾所周知,司馬遷寫《史記》是四處采訪、道聽途說得來的史料。據史料記載,正是司馬遷采訪了樊噲的孫子樊他廣,才得以完成“鴻門宴”一章。我們首先要堅定地相信“鴻門宴”這件事確實發生過,然后,再確認“鴻門宴”這一章是司馬遷創作的。這一章在《史記》中文學性最強。毫不諱言,我讀“鴻門宴”就是當小說讀的。
文學創作要有一定事實依據,這是常識。“鴻門宴”的事實依據就是樊他廣的口述和民間流傳的一些只鱗片羽。我甚至猜測,樊他廣給司馬遷講述時,就摻合了他的主觀感情色彩,已經進行了一次口頭創作。因為樊噲究竟和他孫子講了多少現場的情況不得而知,更重要的是,以樊噲當時的身份,能知道多少“鴻門宴”的內幕?
“鴻門宴”只有是以事實為依據的文學創作,才是史家絕唱。我不想討論“鴻門宴”這一章的史學或文學問題,我想談談項羽集團經過了那么多策劃、費了那么多周折,擺下了“鴻門宴”,為什么沒殺成劉邦?
項羽是貴族出身(這個貴族不是今天的某某某擁有的財富數字,也不是官至幾品),家教良好,知書達理。劉邦是沒落地主家的浪蕩子弟,讀書不多,卻頗懂江湖。
“鴻門宴”上,項羽集團的人都刀出鞘、弓滿張、箭在弦,唯項羽沒有下定決心。首先,項羽讀書太多,讀書是讓人講感情的,所以項羽對劉邦講起了感情,畢竟他們曾經是結拜兄弟,那個時候的結拜兄弟常常比一奶同胞還親。其次,劉邦肯來謝罪,對他服軟,項羽就覺得再殺他無甚道理了。項羽沒有把劉邦當作政治上的對手,而把劉邦當作一個無罪之人。把政治上的競爭對手當作無罪之人,是政治弱智,是政治家的婦人之仁。所以,項莊手上的那把劍一直沒有刺到劉邦。劉邦撿了條命。不,劉邦撿了一個漢朝。
按說,政治家首先是不能有感情,不能按道理行事。懂道理、講感情是做個普通好人的標準,做不了政治家。政治家講的是利益,只要能奪得政權、鞏固政權,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什么背信棄義的事都可以做。但那時的項羽還不是政治家,講感情、講義氣、講道理,尤其是不能識破劉邦身上的無賴本性,沒能識破劉邦在他面前裝孫子,是為了換回小命,回頭要消滅他。可以設想,如果“鴻門宴”中把項羽和劉邦的角色互換,項羽會活著出來嗎?肯定不會。漢朝建立后,劉邦的所做所為,已經證明了劉邦是個無情、無義、無理的政治家加流氓、無賴。
我說項羽是不成熟的政治家,是因為他用俗世好人的感情和倫理來面對競爭對手。當劉邦單身脫逃后,亞父范曾一聲長嘆,對項羽說:你這個小子呀,不值得我給你出謀劃策啊,將來與你爭天下的必是這個劉邦。我們就等著做劉邦的俘虜吧。
那時的項羽確實年輕,才26歲,而劉邦已50歲了。除了年輕外,項羽還剛愎自用。政治家無妄地放大自己的身形,就會忽略對手的韜光養晦、臥薪嘗膽。剛愎自用是政治家給自己挖的陷阱。
項羽失去了“鴻門宴”上殺劉邦的機會,最后導致烏江自刎。那年,項羽僅30歲。有人說,項羽是無顏見江東父老,我相信。講感情的人都講顏面,有虛假的自尊。如果項羽是個真正的政治家,就不會有什么“無顏”一說,回江東召集兵馬,重整旗鼓再與劉邦拼爭就是了。
在項羽自刎前,有這樣一個有趣的場景。劉邦的五位騎兵將領追殺他,其中之一叫呂馬童,曾經在項羽集團工作過。項羽看到呂馬童追到眼前,對呂馬童說:“聽說劉邦要用千兩黃金買我的人頭,還封萬戶侯,我把這個好事給你吧!”然后,拔劍刎向自己的脖子。看看,死之前還要做一次俗世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