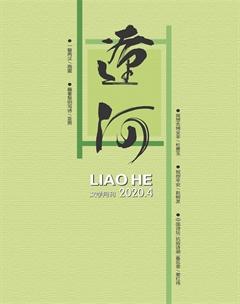雁去雁來雁有聲
路軍
三月春天的氣息如發酵的酒香,四處充盈,汴梁城內的許多街巷,亦是繁花點點,年輕的女子攜兒帶女,在郊外的溫和清麗的風中牽著紙鳶,放飛禁錮一冬的舒展心情。浩渺蒼茫的天空,云卷云來,不時,可以看見一些南來的大雁,千里之途,那雙翅膀依然健朗剛勁。
而此刻,在城北汴河北岸角子門,輜重冗繁,侍從、護衛士兵的犀利眼神不時掠過天空北飛的大雁。千里驛路上,他們仿佛一只只來來去去的大雁,縹緲的身影,負載沉重的歲月印痕,在浩如云煙的歷史冊頁上,書寫后世不能忘記的篇章。
1
“三月乙巳,命兵部員外郎、直史館任中正為契丹國母生辰使,”這是契丹與宋和好的1006年的春天,任中正將帶領他的和平使團,越山跨河,前往與中原風情迥異、游牧與農耕文化交融的異鄉,去給那個叱咤風云的鐵娘子蕭綽祝賀生辰。
溫潤的南風綠滿了田野河岸,冰封萬里的黃河,匯聚了冰雪融化的力量,東流不息。再也看不見“征人臨迥磧,歸雁別滄州”的蒼涼荒蕪景象了。黃河之北,沃野平疇,橫亙綿延的太行山好像萬里屏障,守護廣袤縱橫的大河之北的平原。遠在千里之外的燕山,云煙藹藹,遠橫塞外。
在任中正的記憶里,這片飽經憂傷與磨難的土地發生的一些往事并不遙遠:
亂兵焚毀村落的創痛悲鳴,邊民失魂落魄、驚恐異常的眼神一次次灼痛他的內心。北歸的大雁,在干戈爭鋒的凄厲寒光中黯然避走他鄉。河流縱橫、湖泊眾多的的黃河以北的大地,幾無安寧。萬心歸一,離亂的腳步總有一天卸掉沉重的滄桑,荒蕪殘破的家園會迎來炊煙平和的重生。
如今,驛路上巍峨聳立的鎮州城(今河北正定)敞開了和平之門迎接任中正一行。城樓上執戈而立的士兵的臉上抹了一層金色的光影,他們青春飽滿的眼神流溢三月的濃郁平和的暖意。箭失流觴的陰云飄散而去。城外的郊野田疇,農耕的牛兒躬身曲背,繃直的繩索后,鐵梨劃開肥沃的畦田。
任中正眉宇之間,繁復交織的情緒如萬里長空上的云朵,時而歡暢,時而凝眉思索。他怎么能忘記979年六月的那一個清晨呢?十余萬宋兵擁塞了鎮州城外,從太原前線遠涉而來的士兵疲倦之態蔓延不已,厚重的甲胄上遺落的血痕已經風干枯瘦,馬不解鞍的戰士,兵鋒將指向遠方烏云彌漫的幽州城,契丹與宋第一次正面的爭鋒帷幕,在河之北的廣闊原野與山巒溪澗拉開。然而,剛剛血戰之后的士兵、戰馬,已經如弓弩之末,急需糧秣補充,此刻,后勤補給的車隊還遠水難解近渴,慌亂怯戰的情緒悄悄地蔓延。古語說“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兵心不寧,已經埋下了慘淡的伏筆。契丹此時早已經枕戈待旦,擰成了一股繩,在燕山之南的幽州如猛虎列陣。
北方高粱河之戰一觸即發的時刻,任中正還不過青春華發,一介書生。其時,中原有很多的讀書士子期望戎裝躍馬塞外,揮舞劍戈建功。“我欲思投筆,期封定遠侯”不僅僅是寇準一個人的心聲,任中正這樣的七尺男兒,也曾熱血沸騰。
誰也不曾料到,統一南方戰爭中令敵人望而生畏、所向披靡的大宋步兵,手握寒光閃閃的鋼刀劍戟在與疾如閃電、驍勇異常的契丹鐵鷂子騎兵的沖擊中,陷入了血戰。清波蕩漾的高粱河已經如失色殘陽,倉皇失落的驢車背影猶如一道無言以對的瘡疤,即使時隔多年,還在不甘屈辱的士子們心中浮蕩。古老的幽州,抹不掉的傷痛。“氈寒驢重幽州雪,劍曉龍吟易水煙。”“匈奴恨未滅,獻策言可膚。幽州恨未復,上書言可取。”一些書生恨得咬牙切齒,希望北圖契丹,以消恥辱。
契丹與宋長達25年的拉鋸戰,如兩個窘態各異的摔跤手在平沙曠野、老林深山、長城內外、黃河兩岸殊死博弈,怒目圓睜,氣喘吁吁,滿頭是汗,可是,誰也不肯松手。河之北,地無安寧,民無安生。
眼看著熟透的原野,醉上心頭,農耕的男兒站立田疇,揮舞快鐮,那院落的谷倉已經在心頭貯滿金黃。誰也不會想到,說不定哪一個時刻,鼓角爭鳴,谷粟踐踏,契丹鐵鷂子重騎兵迅疾如風,村落在火光中沉沉地哭泣。處于黃河南岸的曹州,是任中正的家鄉,契丹騎兵千里奔襲的陰云好像沉珂壓在他和鄉親們的心頭。那是一首首無言凄愴的詩歌。
現在,籠罩心頭許久的陰云在一陣急遽的風中散去,澶淵之盟僅僅過了一年多,他成了第二批前往塞外中京城覲見契丹國母蕭綽生辰的使遼使。
2
任中正的行途已經感受到了和平溫潤的舒暢與新鮮,南來的大雁,在藍天中排成一行,向遠方的湖泊池沼、草木深處飛去。他感覺自己也像一只大雁,心輕如絮。一年前的情景浮現在他的眼前。
1005年,春意闌珊,契丹與宋剛剛罷兵,急不可耐的趙恒就下令:“春正月……壬子,詔河北諸州強壯,除瀛州城守得功人,第其等級以聞,余并遣歸農,令有司市耕牛送河北。”執戈握劍矗立城樓的背影不再沉重,廝殺戰場的好兒郎們,卸掉笨重的鎧甲,嗅到了久別許久的故園的輕柔炊煙滋味,雙腳踩在寬闊原野的脊背,皂隸趕著牛兒送給農人,揮鞭響徹天際的不絕聲響,與他們農耕的新夢一起在藍天飄旋。歸來的大雁,將在希望的土地上繁衍生息。
1005年這個春天,好消息不斷,風卷云舒:“通互市,茸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輾轉遷徙的流民再也不像無家可歸的離雁,春天里的好消息,如一曲曲魂牽夢繞難以割舍的鳴笛,再遠的路途,也要回到家鄉,回到土地上。
一年多時光倏忽而過,1006年的春天,任中正不能不感嘆和平的力量:殘缺坍塌的城墻挺起了腰骨,步入街巷,茶坊的怡人清香,酒肆的陸離光影,瓦肆勾欄雜技藝人的南腔北調,小攤小販的悠長吆喝……都是春三月溫暖怡人的景象。
夜里,異鄉館驛的夢很沉很香,任中正猶如一只大雁,時而飛躍燕山,翱翔寥廓茫茫的草原;時而飛過黃河,回到家鄉曹州,棲息在湖畔葦叢、傾聽天籟回響。
晨曦之光劃過窗欞,驛路上的腳步聲穿過原野,任中正的目光已經落在遠方的霸州榷場,1005年“二月……置霸州、安肅軍榷場”的詔令依然回旋在在無邊無際的曠野。契丹與宋既為中華之兄弟,幾十年的隔閡需要雙手緊緊相握,需要民眾往來溝通,更需要經貿的暢通無阻。遼闊的邊境之地,荒涼寂寞許久的榷場大門重新敞開。千里驛路上,任中正已經不是孤雁。契丹的馬隊駝陣,踏著春天的悠長身影,和著粗獷綿長的塞外古謠,如群雁南飛,來到邊境的榷場,與來自宋國的商旅匯合。神奇的瞬間,鮮活的歷史畫面,南腔北調的碰撞交融,在1006年的春天發酵,如酒香彌散而來。
拒馬河,新城,涿州,幽州,異鄉的路越來越遠,身上的思想行囊越來越沉,越來越厚重。
1005年,宋與契丹的友好之策接踵而至,“甲午,詔緣邊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沒蕃漢口歸業者,給資糧。弛邊民鐵禁。”而任中正在契丹境內所見,與拒馬河之南的景象何其相似?行路月余,廣闊無邊的四月平原,禾苗鋪展成綠色的織毯。一些裸露許久的荒地,被來自中原的鐵梨勾勒出一幅幅歡快活潑的農耕圖。
這些情景,裝在任中正的腦子里,也書寫在行旅記錄中。一百多年的時光,多少《使遼語錄》在千年歲月的光影流轉中散逸沉落,甚至零落成泥碾作塵。余存至今的不過滄海一粟。好在,浩瀚的《宋史》冊頁,還留下了任中正的列傳。
昔日戰場上不共戴天、殊死拼殺的敵手,短短一年,已經成了和平親密的兄弟。實際上,在宋不斷拋出耀眼悅目橄欖枝的時候,契丹人自然也不甘落后,以禮相待。
千里驛路,從1005年冬天開始,一直持續了17年,契丹人都會派出使臣前來汴梁給趙恒祝賀承天節。喧囂熱鬧隆重的背后,則是和平交往的延續,不同文明的交融和互通。
就在任中正使遼之前的1005年的十一月。契丹使臣耶律留寧等人前來給趙恒祝賀生日,此時,身為兵部員外郎的任中正的資歷與官職還邁不進巍峨壯麗的崇德殿內參加慶典,那鐘磬齊鳴、管弦合悅的樂聲飄揚在古老的街巷深處,好像一只只盤桓空中的大雁和鳴。他是否會想到有一天,自己會成為一只北飛的大雁,前往遙遠的塞外,在異域他鄉、威嚴肅穆的朝堂,祝賀蕭綽生日呢?
契丹使節耶律留寧承載著深情厚誼的禮物名單,成了滿城佳話。“御衣十二襲,皆裘紬綿刻絲透背紗縠,貯以金銀飾箱。金玉水晶鞍勒馬八,散馬四百,弓矢賓鐵刀,鷹鶻臘,契丹新羅酒,青白鹽果實百品,貯以梀檽器。”名族風情濃郁的精美輕柔的衣衫,在燈光流影中如迷幻的仙衣;鑲金飾玉的名貴寶馬洋溢草原雄風;“鷹鶻”即海東青,翱翔我國東北大海之濱的猛禽凝固成了一枚枚枯干的臘肉。一些名目,任中正還是第一次聽說。它們沿著古老的驛路,來到中原,草原文化的光影在斑斕多姿的都市汴梁閃亮登場,雖然,最初的舞臺不過深宮內巷,但它的獨特奇異的生命因子,一定會與浩蕩奔涌的漢風融合在一起。在深厚肥沃的中原沃土上生根發芽。使遼回來后,在太宗朝,曾拜兵部尚書、遷禮部尚書。這是后話。
3
在契丹中京城殿內,使遼任中正見到了傳說中飛揚跋扈的蕭太后,此時,她年逾五旬,那雙犀利深邃的眼神依然如蒼鷹逐雁。他不禁感喟嘆息:假如年紀輕輕的耶律隆緒沒有蕭綽這樣文韜武略的母親站在幕后出謀劃策,契丹與宋的歷史將如何書寫?
遺憾的是,迷霧重重的歷史長河,許多真實被掩埋。當年,蕭綽與韓德讓的春花雪月的傳說在中原成為街談巷議,插科打諢的怪誕變異的音符自然也傳至深宮內的太宗皇帝,這么一位荒淫誤國的契丹皇后與南唐后主李煜誤國有何不同?李煜尚能吟詩弄月,在“菊花開,菊花殘。塞雁高飛人未還,一簾風月閑。”等等的意象中流連傷感,而蕭綽不過子幼母寡,這可是上天賜予的千載難逢的北伐時機嗎?迷幻陸離的光影如誘惑人心的罌粟,遠在中國北方大雁北飛的草原、湖畔、高山閃耀。
986年的春天,南雁北飛的季節,隔著奔騰如虎的黃河眺望遠方,任中正與許許多多的宋人一樣,希望雍熙北伐一血四年前高粱河之戰的恥辱,一舉定天下。二十多萬的驍勇兒郎在春季盎然的三月,兵鋒直指契丹燕云十六州。
不久,慘淡陰郁的烏云彌漫黃河兩岸,任中正耳畔飄落的則是七月里飄雪一般的陰涼與落葉蕭蕭。聞名天下的名將楊業與他的萬千健兒隕落陳家谷,兵敗的消息在街巷阡陌如山壓頂。當時的政治家張齊賢據此反思道:“堯、舜之道無他,在乎安民而利之爾。民既安利,則遠人斂衽而至矣。陛下愛民人、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任中正咀嚼反復,怎能體味不出那番拳拳之心呢?當年唐朝名臣魏征勸諫李世民“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與民生息,固本強基,韜光養晦,有朝一日,實力享譽天下,何愁邊遠之邦不納貢稱臣,簞食壺漿來歡迎王師呢?
1006年的五月,中京城內,歷史的謎團得以紓解。汴河兩岸瓦舍勾欄、酒肆茶館內的荒誕不經的傳說在南風浩卷中漸漸清晰:
當年十二歲的耶律隆緒加冕草原,蕭綽面對困境說出的“母寡子弱,族屬雄強,邊防未靖,奈何?”如試金石,也如凝聚民心的呼喊,立竿見影。耶律斜軫、韓德讓立表忠心:“信任臣等,何慮之有”。面對危局,民心凝聚,眾志成城。蕭綽也并非像宋人人云亦云那樣只會“麗宇芳林對高閣,新裝艷質本傾城”的狐媚之人 ,而是“明達治道,聞善必從,賞罰信明”的女中豪杰。
往事飄忽,歷史不再回頭。
在中京城內的文化殿,任中正第一次見到權傾契丹、顯赫灼人的大丞相韓德讓等能臣武將。當年驍勇異常而又謀略過人,令宋兵宋將吃盡苦頭的耶律休哥已經離世,遙想當年,若不是他“均戍兵,立更休法,勸農桑,修武備,邊境大治”,獨擋南面危局,高梁河之戰,雍熙北伐失敗的歷史極有可能改寫了。還有那個“與韓德讓、耶律斜軫相友善,同心輔政,整析蠹弊,知無不言,務在息民薄賦”的丞相室昉,小小年紀的耶律隆緒身邊有這么多的股肱之臣傾力輔佐,看似傾斜的天平已經平衡。
從更為遼遠的歷史來看,契丹人并非莽夫逞勇之眾,他們并不排斥來自中原的文明之風,設立南北官制,興學,科舉取士,重用遠見卓識的漢人為官,獎勵農耕,等等措施,都在北方種植下了厚重的文明種子。耶律隆緒本人,精射法,曉音律,好繪畫,漢學水準不亞于文藝范十足的宋朝皇帝。在給蕭綽祝壽之時,耶律隆緒對于中原學識深厚的使臣的尊敬與渴慕之意,溢于言表。這些,都給任中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雁去雁來,中國的北方,漢風席卷,草木繁盛。
4
完成使命的任中正在六月草長鶯飛的季節,攜帶契丹人的深情厚誼,返回汴梁城,綿長悠遠的驛路上,他猶如一只離家的歸雁,在中國北方的廣袤山巒、草原荒漠,留下了一串串堅實的足印。
回到中原的任中正愈發受到趙恒以及之后宋仁宗趙禎的信任,官爵越來越高,1016年十一月,身為工部侍郎的任中正與文武百官第一次來到崇德殿內參加契丹使臣耶律延寧、張岐祝賀宋真宗的生日禮儀。粗獷溫潤的草原之風在古老的時光中舒展。繁復秩序的禮儀,異域風情的精致禮品,契丹語與漢語之間的交流融合,觥籌交錯的宴飲光影,和平之門敞開了,就不再關閉。
中華文明的冊頁上,任中正他們與眾多的契丹使臣就像來來去去的大雁,跨越浩渺蒼茫的時空,銜著一粒粒文明的種子,落入風情迥異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