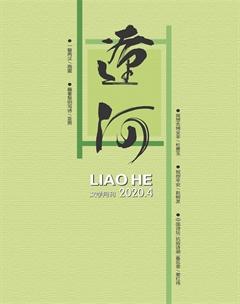有人@我
鄭德庫
手機響時,她正在澆花。
她一聽就知道是微信,微信的鈴聲沒有電話的急切,而是一種扯閑篇的曖昧和誘惑。
“難得還有人惦記。誰@我呢?”
她想過去拿手機,可又有點兒狐疑,傷腿也疼。她扶著墻壁停下,像只貓盯著風吹落葉似的盯著手機。
手機就那么響著,似乎透出一種誘惑。
她猜測可能是誰,一直猜到鈴聲戛然而止。
這時她才慢慢踱過去,拿起手機一看,“農民工”,她長吁口氣,心底暗生一股暖意。
微信的昵稱是簡筆畫,雖然可自由隨意命名,但還是能從中窺視出一個人的修養和趣味。
這位“農民工”是她的師范同學,當初的昵稱那叫一個高大上,從“壁立千仞”到“壁立”,又到“霹靂”,再到“咔嚓一聲雷”,最后成了實實在在的“農民工”。她在笑話他的同時,也把自己的“悠然閑者”變成了現在的“山榛子”(因真實的名字里有個珍字)。
讀師范時,她是班級的團支部書記。他是白丁,真正的白丁,連團員都不是。屈指算來,班級四十多位同學,只有四位還沒入團,一個資本家弟子,一個地主女兒,一個右派的女兒,加上一個他。按說1977年恢復高考一張卷考上來的,雖是中師,可也算人尖子,怎么連個團員都不是?別是有什么瞞著吧!
她不動聲色,利用暑假和另一名同學去他的家鄉外調,從大隊干部到樹下納涼的老大媽都問了,還真沒啥問題,就是人噶點兒。不料,村里的信息傳遞忒快,兩人被剛剛趕海回來的他截到家里,嚼了一頓極新鮮的赤甲紅螃蟹。
畢業后,她留校,他分配到中學,后來他又改行當了警察。各干各的工作,各過各的日子,再沒有更多的交集。
沒想到多年后的一次偶然,兩人有了一段親密接觸。
市里組織政工部門的人外出考察,當時她是高職專科學校的黨委副書記,正處;他則是給領導寫材料的秘書科長。兩人這一路,出行同車,吃飯同桌,挺惹人眼球的。不過她看出他嘴上挺能裝,可骨子里卻是極本分的,四十多歲了還很青澀,也許他根本就沒把她納入男女關系范疇。
她暗自生氣,行為就出人意料,甚至出于自己的意料。在張家界景區門口,同行人的眾目睽睽下,她挽他甜甜蜜蜜地照了一張合影。
得,就這一下,雖沒將他拴在她石榴裙下,卻使他成了實實在在的跟班。
最可笑的是,過小溪時,她把兩臂吊在他脖子上賣萌,他抱著她,一如傻姑爺抱媳婦,身體僵硬得像根木頭。然而她無意間做了件煞風景的糗事,讓他扳回了一局。
回程時,她被反關在機場的廁所里出不來,只好喊在外邊看包裹的他。兩人一里一外,好一頓忙活,才把卡住的門拽開。“我告訴你,回去可千萬不能跟同學們亂講。”她一再懇求,他只是笑。
從那以后,兩人的聯系多了些,同學們聚會也愛往一起湊,說話也隨便了。有同學看出端倪,相相面說:“你們倆有情況啊!”
可直到退休,她和他也沒有什么新情況。挺大歲數了,兩人還能把握人生的底線。不過回想起來,她的心里就隱隱泛出一絲的恨勁兒,牙癢癢地想咬他一口。
半年前,她遭遇了車禍,骨折,左腳的半邊骨肉分離。同學們知道后,該看的看了,該打電話的打了,很快一陣風似的就過去了。
這時的她算是嘗到了寂寞的滋味。
謝天謝地,“農民工”總算@了一下,可她偏偏又沒接。再看屏幕,也沒有文字留言和語音留言。她就等他的微信。等了好長時間,她放下矜持@他,沒人接。再@,還是沒接。她想這是報復我呢!兀自搖頭。
過了一個多鐘頭,手機再次響起,還是“農民工”打來的,她第一時間接通。
“想死你了!”先是馮鞏式的一貫招呼,接著就問恢復得怎么樣。
“還行,能下地了。”
兩人一頓漫無邊際的閑聊。這時的她似乎他說什么都愛聽。
話繞回來,她就問今天的微信怎么回事。
“嗨,我著急上河邊呀!”
她知道他每天要到遼河邊走一萬步。
“遼河邊怎那么勾魂?”
“我每天都和一美女幽會。”
“她漂亮嗎?”
她知道他又開始胡謅了,就順著往上碼。
“高個,豐滿,有點兒西方人的特點。”
“你們幽會干什么呀?”
“就是四目相對,有一天看著看著美女還哭了,對了那美女可能有腰脫。”
說得像真事似的,這一下她疑惑了,忙說:“老了老了你可別整出什么花花事呀!”
微信斷了,她呆呆出神等待。
過了好一會兒,微信又來了。這回發來的是一張照片,遼河航標的美人魚雕塑,下面還有文字注釋:1、美女哭了是那天下雨;2、從美女的造型可看出有腰脫。
嘿!原來是這個美女。
好一會兒她才回到現實,繼續澆花。一邁步,咦?傷腿竟不疼了。她又試了兩下,挺奇怪的,腿還真不疼了。
她就想哪天得請請@她的這位“農民工”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