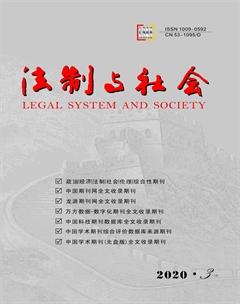駕駛培訓中學員造成交通事故的賠償責任承擔
葉子暉
關鍵詞駕駛培訓 替代責任 追償權
據公安部的統計數據,2019年全國新注冊登記機動車3,214萬輛,機動車保有量達3.48億輛;機動車駕駛人達4.35億人,其中汽車駕駛人3.97億人。可見我國機動車駕駛培訓行業存在巨大需求。學員接受培訓單位(駕校)教練員的指導,學習駕駛機動車技術及相關交通安全知識、法律規范等,而學員發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損害的情況也越來越頻繁出現,對于被侵權人與學員、教練、培訓單位間法律關系的認定,直接影響了各方責任的承擔。司法實踐中,對于此種類型的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先由保險公司在交強險及商業三者險范圍內承擔賠償責任并無太大爭議,本文要討論的主要問題是在保險范圍以外的賠償責任:第一,學員、教練員與培訓單位間構成何種法律關系,如何進行責任承擔?第二,是否因雇傭或掛靠的情形而導致不同的責任承擔方式?第三,培訓單位對教練員是否具有追償權?
一、相關法律規定及理解
《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20條規定:“在道路上學習機動車駕駛技能應當使用教練車,在教練員隨車指導下進行,與教學無關的人員不得乘坐教練車。學員在學習駕駛中有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或者造成交通事故的,由教練員承擔責任。”《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交通事故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7條規定:“接受機動車駕駛培訓的人員,在培訓活動中駕駛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損害,屬于該機動車一方責任,當事人請求駕駛培訓單位承擔賠償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可見,現行法排除了學員對其培訓過程中造成的交通事故的自己責任,即學員無需對因自己學習駕駛行為造成的第三人損害承擔賠償責任。
對上述兩條規定,最高院認為,前者規定由教練員承擔的系“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而并非損害賠償責任。學員并非是獨立駕駛教練車,不具備對車輛的支配力,亦不享有運行利益。對教練員來說,其在車輛內不僅需教授駕駛技能,還需對可能發生的不規范操作或者危險行為進行處置,故實際支配車輛的系教練員,由其承擔發生交通事故的后果。而教練員又受雇于駕駛培訓單位,因此培訓單位應當負責,教練員并非賠償責任主體。上述結論的推導過程中還適用了《侵權責任法》第34條第1款關于用人單位工作人員執行職務造成第三人損害由用人單位擔責的規定。這也是大多數該類型案件的裁判思路。
二、培訓單位成為賠償責任主體的理論依據
(一)運行利益與運行控制理論。
一方面,培訓單位與學員簽訂培訓合同,由學員支付培訓費用,學員在教練指導及安排下通過駕駛教練車履行培訓合同,故培訓單位享有車輛的運行利益。另一方面,雖然學員也從駕駛活動中獲益,但行駛路線、行駛速度、行駛方式聽從于教練員的指揮,教練員可通過制動裝置對車輛施加直接控制。故教練員系車輛實際支配人,其行為又系執行培訓單位安排的工作任務,因此培訓單位應為賠償責任主體。最高院即采此觀點,否認學員駕駛行為的獨立性,對于交通事故教練員其實是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而后培訓單位基于雇傭關系承擔替代責任順理成章。上述理論能夠解釋培訓單位替代責任發生原因,有助于促使培訓單位加強管理,教練員認真教學,防范風險。但在細節上仍存在一些疑問,比如說交通事故侵權應采過錯責任原則,那么在認定侵權責任時實際上主要是以學員駕駛行為過錯來劃分事故責任,教練員對于其指教方面的過錯并不在對外關系中體現,實際上按照現行法規定教練員及駕校對學員行為系承擔無過錯責任,此點應予以注意。
(二)雙重替代責任理論
有學者認為,學員作為駕駛人造成了交通事故由駕駛培訓單位來承擔替代責任是一種特別的法律現象,前述理論還不足以作出充分的解釋說明。學員經過一段時間學習或就獲得了對車輛進行操控的能力,教練員通過口頭或者動作指導以及操作副駕駛座位處安裝的制動裝置來進行輔助;且運行利益與風險一致說僅能作為賠償主體認定的正當性補充,否則培訓單位地位將淪為保險人。因此其提出教練員與學員之間系一種介于監護關系與師徒關系之間的指教關系,存在兩重的替代責任:即教練員對學員侵權行為承擔指教型替代責任以及培訓單位為教練員職務行為承擔用人單位替代責任。此觀點在判斷事故責任構成方面可資借鑒。
事實上,在交警部門進行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時,少數情況下會對學員及教練員在事故過程中的過錯行為均進行分析定責,但此僅系對事故原因力的劃分,并不會影響賠償責任主體的認定。
三、教練車掛靠對責任承擔的影響
社會生活中,教練員與培訓單位的關系并不僅限于單純的雇傭,存在大量由教練員或者第三人購買教練車輛后,登記在培訓單位名下并與之簽訂車輛掛靠協議的情況。與受雇傭的駕駛員相比,掛靠情形下教練員對教練車的使用有更高的自主權,并且在更大程度上自負盈虧,此時是否在責任承擔上存在不同?
《交通事故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3條規定:“以掛靠形式從事道路運輸經營活動的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損害,屬于該機動車一方責任,當事人請求由掛靠人和被掛靠人承擔連帶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但該條規定僅適用于道路運輸經營權的掛靠行為。道路運輸經營活動與機動車日常使用相比系一項危險性較高的活動,故行政法上設置了相應的市場準入條件,掛靠人與被掛靠人共同行為使得掛靠車輛的事故風險性及危害性提高,從過錯的角度看屬于雙方過錯的結合,故對外應承擔連帶責任。對內,則可根據各自在交通事故中過錯進行分擔。司法實踐中也存在類推適用此條規定處理學員駕駛事故的損害賠償的案例,但該類推適用的合理性值得討論。
對于駕駛培訓來說,無論是否存在掛靠,均系由教練員通過隨車指導以及必要時操作副駕駛的安全裝置等方式來對學員學習駕駛過程進行風險控制,至于其與駕校間對學員交納的費用如何分配僅系內部的權利義務劃分。在駕駛培訓活動中涉及的車輛掛靠很難被定性為運輸經營,教練車系作為教學工具發揮作用。故而,該掛靠行為并未顯著增加學員學習駕駛機動車產生的危險程度。形式上,學員仍是與培訓單位簽訂培訓合同,教練員并非以個人身份而是以駕校指派人員身份進行培訓,在培訓過程中發生問題也經由培訓單位進行協調處理;同時培訓單位作為車輛名義上的所有人,具有購買或者敦促掛靠人購買充足保險以分擔風險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因此對外適用《交通事故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7條規定由培訓單位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已足,不應類推適用前述連帶責任的規定。審判實踐中亦存在該掛靠教練車行為不影響教練員與駕校間成立職務行為的觀點。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公安部、交通運輸部等部門聯合推進了小型汽車駕駛證自學自考的試點工作,這意味著在試點地區符合一定條件的駕駛員即可獨立從事隨車指導他人進行學習駕駛的活動,此時若發生交通事故,可直接適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20條規定,由隨車的指導人員承擔責任。
四、培訓單位擔責后是否對教練員享有追償權
首先,《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中采用雇員、雇主概念,規定雇員在雇傭活動中的侵權行為由雇主承擔賠償責任,同時規定了故意或重大過失情況下雇員的連帶賠償責任,并在此種情況下賦予雇主對雇員的追償權,既排除了一般過失情況下的追償權,同時也隱含了非完全賠償之意。《侵權責任法》第34條第1款并未沿用特定情況下連帶責任的規定,對是否存在追償權也并未明文規定,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委員會關于該法草案審議結果的報告中指出,追償權問題“宜由法院在審判實踐中根據具體情況處理”,并未否定特定條件下的用人單位的追償權。自2019年12月28日起開始征求意見的《民法典(草案)征求意見稿》第1118條第1款第2句也規定:“用人單位承擔侵權責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工作人員追償。”從相關條文的立法演進可以看出,在排除雇員連帶責任前提下,肯定追償權,同時亦避免了對雇員苛以過重的負擔而導致權利義務失衡的做法,為立法者所采納。
其次,在教練員與培訓單位存在車輛掛靠或者說是內部承包的情況下,雙方一般會在協議中就此類賠償義務進行約定,那么可以按照合同法規定對于協議的效力進行考察,若不存在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及公序良俗的情況,且權利義務不顯失公平,則可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肯定培訓單位對教練員部分的求償請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