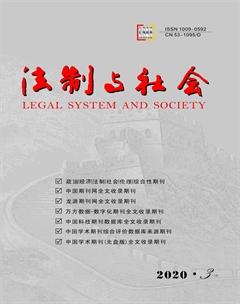大理州鄉村集市秩序重構探究
鄧薇
關鍵詞大理州 鄉村集市 秩序重構
一、大理州鄉村集市秩序重構的必要性
(一)固有特征
鄉村集市自產生之初,便是為了滿足一定地域范圍內農民的生產及生活需求。鄉村集市的經濟功能一定程度決定了其特征。通常而言,大理州鄉村集市具備交易規模小且分散、周期性、高度自發性、多民族參與等特點。
1.交易規模小且分散
鄉村集市為解決一定地域范圍內鄉民生活的交易需求而產生,其輻射半徑一般較小,且具有一定的規律性。依據施堅雅等人的研究,我國鄉村集市的分布具有較強的規律性,其輻射半徑一般為附近的幾個村莊。從經濟功能角度分析,鄉村集市的規模主要由鄉民的具體需求決定。鄉民消費能力普遍較低,需求產品較為單一,多為農副產品及生活必需品。單一且少量的商品需求決定了鄉村集市的規模,此外,交通是否便利也鉗制了鄉村集市的規模。
2.周期性
鄉村集市不同于城市集貿市場,其具備明顯的周期性。目前,大理州范圍內集市多為定期集市。依據街期不同,大理州集市可以分為一日一集、三日一集、四日一集、五日一集、六日一集、七日一集、十日一集、一年一集。縱觀大理州集市,四日一集及五日一集者較多。
不同的集期折射出不同半徑范圍內鄉民對集市貿易的需求。一般而言,鄉民對集市貿易需求越多,集期越密集。
3.高度自發性
鄉村集市是自發產生的。鄉村集市的最初形態為“市井”,是按井田而劃分的集市,因而具備較為典型的自然經濟的特征。鄉村集市的運轉也大多是自發的。我國古代國際治理體制中“皇權不下縣”的特點促使鄉村集市的自發運轉。所謂“皇權不下縣”是指國家的正式政權機構只設在縣一級,縣以下實行的是鄉村自治。鄉村集市的自發運轉并非無效率且無序的運轉,而是該種運轉很大程度上依靠鄉民的道德倫理及信任度,是一種自律自覺的運轉。新中國成立后,國家高度關注鄉村,鄉村集市的運轉也開始逐步改變自發運轉的狀態。
4.多民族參與
大理州地處西南邊陲,形成以白族為主的多民族聚居狀態。大理州鄉村集市涵蓋多村落,其中少數民族較多,州內大部分鄉村集市均有少數民族參與。少數民族市場主體對于鄉村集市的需求既具備一般物資交易需求,也具備其民族習慣的特定需求。例如巍山縣大倉街集市回族居多,其集市交易商品便具備典型的回族特征,牛肉及牛肉制品、油香等商品較多。此外,少數民族文化也深刻影響了大理州各鄉村集市的文化,形成具備不同少數民族特征的鄉村集市文化。
(二)變遷后的新困境
1.大理州鄉村集市的存與廢
關于鄉村集市的變遷,部分學者認為鄉村集市終將走向消亡,被現代經濟形態所取代。但在調研過程中,大理州鄉民對于集市的經濟需求及精神依托均切實決定了鄉村集市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充盈的活力。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大理州鄉村集市也在不同程度上發生了變遷。該變遷涵蓋市場主體、商品、集市功能等多方面。
總體而言,大理州鄉村集市逐漸成為一定地域內的經濟交換、社會交往、信息交流的中心,它將居住在一定地域范圍內不同地點的人聯結起來,形成一個集市社會。如何有效治理集市社會,必須建立在充分認識鄉村集市的重要性的基礎上。
2.大理州鄉村集市的新問題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高度關注鄉村,鄉村集市的運轉也逐步改變自發運轉的狀態,但長期的自發運轉所形成的非正式制度又從另一角度給國家管理集市的正式制度帶來了挑戰。此外,外地流動經營者的大量涌入也打破了鄉村集市固有的圈子,隨之而來的商品質量與監管、社會信任與重構等問題不斷涌現。
二、大理州鄉村集市秩序重構的路徑
(一)推進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耦合
非正式制度,或稱“非正式約束”“非制度化規則”“社會潛網”等,是社會共同認可的、不成文的行為規范,主要包括文化傳統、倫理道德、習慣習俗和意識形態等無形的約束規則。相較于人們自覺地、有意識地設計并創造出來的政策和一系列法規規則的正式制度而言,非正式制度在鄉村集市中具備存在范圍更廣、滲透性更強、執行高度自覺等特征。這與鄉村集市的高度自發性特征關系密切。鄉村集市的產生于運轉均離不開非正式制度。
鄉村集市產生之初,是為解決鄉民基本的生活需求與交易需求,特定的輻射半徑決定了集市參與者的“熟人”關系。大理州鄉村集市中的交易商品多為農副產品,經營者也多為集市輻射半徑內的村民。賣者與買者基本熟識,鄰村居民、同村居民,甚至是同宗親戚。已經形成的熟人社會中特定的信任網可以自然而然地適用于大理州鄉村集市,買賣雙方無需為商品質量、價格或口角爭端而擔憂,長期形成的熟人信任關系有效調控了個人行為與組織行為。
但是,隨著外來集市參與者的涌入,固有的熟人信任關系被打破。外來商品經營者與本地商品經營者之間、外人商品經營者與本地消費者之間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矛盾。如何調和非正式制度在熟人關系網外無法有效調控的現狀與本地集市參與者渴望集市有效運行的矛盾,是調控大理州鄉村集市應該面對并解決的問題。
此外,國家調控市場也面臨如何正視與梳理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關系的困境。大理州鄉村集市自發形成并自覺運轉,無論是商品經營者的攤位擺放、集市布局,或是集市交易規則,都充分體現了鄉村集市的自覺性。支撐鄉村集市自覺運轉的非正式制度根深蒂固,且部分非正式制度與法律法規等正式制度并不完全統一。例如大理州鄉村集市的攤位擺放。在調研中發現,多數本地經營者普遍堅持自己已經在固定地點擺放了幾十年或是十幾年,因此只愿意繼續遵循傳統,而非聽從城市綜合執法等部門的調控。面對大理州鄉村集市的現狀,為尋求集市變遷后合理的秩序重構,國家對集市的管理應該在追求執法的統一性與嚴肅性的基礎上,充分尊重非正式制度的傳統有效性,從而實現良性管理。
(二)培養鄉民對集市的公共精神
農民公共精神發育于鄉村公共生活之中,是村民在處理個人利益與村莊公共利益關系過程中所具有的關心與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政治利他、愛心和奉獻等公共價值。良好的社會治理能否實現則取決于眾多因素,如政治制度和政府體制的精心設計、經濟發展的速度和穩定性、技術的變化、領導人的素質等,但是,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公共精神。大理州鄉村集市是鄉民聚集的典型公共空間,鄉民關系交錯,鄉民對集市公共精神的缺失將導致集市管理成本增加,管理效能降低。同時,低效的管理又將反作用于集市,壓縮集市公共空間,從而進一步導致鄉民公共精神缺失。
此外,大理州鄉村集市具有多民族共同參與的特征,通過集市這一公共空間因勢利導,培養多民族鄉民的公共精神,能充分提高多民族地方治理效能,提升民族凝聚力。根據調研,目前大理州鄉村集市本地鄉民參與者年齡普遍多為四十歲以上的中老年人,年輕人受多元文化影響,對于鄉村集市的精神依賴逐步降低。但鄉村精英階層一般出自年輕人,且鄉村精英作為公共精神領袖的力量不可忽視。為重構大理州鄉村集市的秩序,應考慮從鄉村的內在化特征合理引導,培育年輕鄉民參與集市,鞏固鄉民的公共精神。
(三)汲取地方文化,發展特色集市
鄉村集市是一個集政治、經濟、文化等為一體的公共空間,新時期的鄉村集市不僅是物品交換的集散中心,還是鄉民的社交和娛樂中心。故此,鄉村集市是一定地域范圍內鄉村文化聚合的載體。充分汲取地方文化,豐富大理州鄉村集市的文化內涵,不僅能有效聚合鄉民對鄉村集市的精神依賴,更能培育特色鄉村集市。鑒于大理州旅游資源豐富,年輕游客眾多且追求小眾需求等特點,大理州集市可以充分提煉地方文化,發展特色集市。特色集市在具備文化內涵的同時,通過商品媒介滿足本地鄉民基本需求,并有利于吸引游客共同參與集市,從而讓鄉村集市煥發生機。
大理州鄉村集市眾多,集市治理應合理思考在集市變遷的大背景下如何重構集市秩序。在有利于鄉村集市的長期有序運行的基礎上,由有序的鄉村集市培育鄉民公共精神,提高多民族聚居區的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