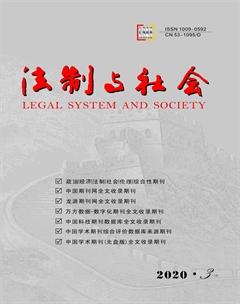論我國音樂版權保護現狀及解決路徑探析
熊穎
關鍵詞音樂版權 侵權現狀 版權保護
一、事件回顧及相關問題的思考
(一)事件回顧
2019年6月,著名經紀人ScooterBraun以3億美元的價格,通過其控股公司Ithaca Holdings收購了Taylor Swift前公司BigMachine Label Group。由于該公司擁有她前6張專輯的錄音版權,在8月25日,TaylorSwift表示,將會通過重錄前六張專輯來拿回自己的錄音版權。然而在11月7日,TaylorSwift在Tumblr上發表聲明稱,除非她同意不重新錄制前六張專輯,否則BigMa.chine Label Group以及其前老板和Scooter Braun不允許她在AMA和天貓“雙十一”晚會演出自己的老歌,甚至連個人紀錄片中也不能出現之前音樂的片段。
(二)相關問題引發的思考
對此事件的反思。根據美國有關法律法規,當歌手寫出她的第一首歌時,就有以下幾個權利:復制權、發行權、表演權、演繹權、展覽權以及錄音的數字音頻傳輸表演權。在這幾項權利中的復制權與發行權,根據美國法律的規定,音樂作品一旦公開發行,只要符合一定條件,任何人都可以不經Taylor Swift許可進行翻唱,但是這里的翻唱范圍僅限錄音,不包括公開表演。這跟版權是否出售給其他人無關,只要發行了的音樂作品,都可以都適用這個法規。因此我們可以得知,Taylor Swift只是不能表演,進行翻唱是完全合法合規的。但當第三方想要復制發行Taylor Swift前6張專輯,其并不需要獲得Taylor Swift授權,僅僅需要錄音版權人的授權,而對于錄音中的音樂作品,只需要向TaylorSwift支付版權費即可。另外其表演權有沒有被出售也是讓人關注的問題,如果TaylorSwift的表演權完全出售給IthacaHoldings了,那么即使是Taylor Swift重錄前六張專輯,也只能通過專輯出售的方式宣傳歌曲,而無法在公開場合表演。對于演繹權、展覽權、錄音的數字音頻傳輸表演權這三項權利沒有特別的規定,基本和表演權相同,取決于Taylor Swift賣出了多大的比例。
二、我國音樂版權的侵權現狀
在我國,音樂人簽約唱片公司后,其作品的版權被買斷是一件十分普遍的事情。甚至在一些唱片公司的合同的約定中,由于音樂人簽訂的合同是委托創作合同,其從一開始就失去了談判權。音樂家們通常只能保留與著作權有關的人身權,而失去收益分配權。目前主要分為以下幾種情況:
(一)唱片公司利用絕對優勢占據主動地位
在現實生活中,大多數音樂人的合作模式和版權費分配比例很容易受到唱片公司和版權集體管理組織的限制,其交易缺乏靈活性,尤其缺乏對后續音樂使用的控制。在與唱片公司采用獨家授權或買斷式合作后,音樂人幾乎放棄了對音樂權利的后續控制。根據我國著作權管理條例有關規定。,音樂人一旦與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簽約后,即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在授權期內對音樂版權的控制力與主動性。在1998年,花兒樂隊簽約新蜂音樂的合同中約定,公司以每首3000元人民幣的價格買下花兒樂隊在公司所有歌曲的詞曲著作權和錄音制作者權等所有相關權利。這就意味著,哪怕是大張偉本人演唱、錄制自己的歌,也要獲得前公司授權。
(二)政府及有關機構未發揮有效作用
依照法律法規的規定,國家版權部門監督音著協的業務行動、資產利用和財務的管理。若出現了侵權行為,音樂著作權利人、使用者以及社會成員可以向政府反映,政府會依照法律處理。但事實上,政府對其監督的消息是十分困難的。一方面,音著協長期處于壟斷地位,但只對著作權人作品的財產權進行信托管理,而鄰接權人的權利集體保護組織卻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設立和運行,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約了相關音樂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從執法效果上來看,雖然我國在新世紀初就先后頒布和修訂了《著作權法》《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互聯網文化管理暫行規定》等相關法律法規。但數字音樂的侵權行為依然難以遏制,尤其是網絡侵權現象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三)音樂人本身版權保護意識薄弱
根據2019年11月6日發布的《音樂人生存現狀與版權認知狀況調查研究報告》顯示,目前約29%的音樂人未能從音樂獲得一分收入,除此以外,有近七成的音樂人從事兼職工作,否則便無法負擔起日常生活。與此同時,在音樂人的收益來源調查中顯示,版稅收益是主要音樂收益來源的,僅占比5.91%。而在2019年11月9日中國傳媒大學張豐艷教授團隊發布的《2019音樂人生存狀況報告》數據顯示,近40%接受調查的音樂家表示,他們經歷過侵權行為,而將近一半的的音樂家表示無法單獨維權。49.8%的受訪者當談及被授權給版權代理機構時,不知道他們授權的是什么業務,高達72%的中國音樂人,從來沒有聽過版權講座,不知道版權的價值。從這些報告數據中可以看出,目前音樂人對于版權的保護意識并不強,甚至可以說是相當薄弱。
三、各國音樂版權保護實踐及立法現狀
長期以來,中國都是處在一個盜版的惡劣環境之下,不管是哪一種音樂載體或者播放設施,幾乎都是盜版。針對此種情況,中國政府在2015年先后出臺了多項政策來保護正版音樂合法權益。在有關政策的嚴格實施下,過去數字音樂盜版猖狂的現象得到了有效的改善,音樂產業的版權意識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總體上來說,我國在諸多與音樂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中,商業化程度仍落后于全球總體水平,這也使得音樂創作者的版權價值無法得到最大化保護。因此借鑒其他發達國家成熟完整的版權保護體系,了解并學習其對于音樂版權的保護歷史及發展機制,使我們能汲取一些經驗與教訓。
(一)美國的音樂版權保護
以美國為例,美國的版權法對于音樂作品的保護是晚于對文學作品的保護的,經過了幾百年的時間,美國在憲法及相關法律上不斷地進行完善。1998年,美國通過了《版權期限延長法案》,該法規可以看出,歌曲屬于音樂作品,是美國版權法的保護客體。實踐中也有很多相關實例。例如,歌曲“祝你生日快樂”只有6個音符,但無論是在影視作品、廣播電臺,還是在各種公共場合使用歌曲,該曲目都要收費。但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國內1986版的經典電視劇《西游記》的音樂制作人許鏡清老師,他為該劇創作了《女兒情》《敢問路在何方》等耳熟能詳的名曲,許多影視作品借用了許老師的音樂,但他收到的版權費屈指可數。
(二)韓國的音樂版權保護
韓國的音樂產業是韓國國民經濟支柱產業之一。但是與此同時侵權與抄襲事件層出不窮,面對此種狀況,韓國國會于2018年1月31日通過了“禁止外國文化產品和復制音樂”法案。該法的制定是韓國從政府層面應對文化產品侵權行為的一項措施,該法的制定是韓國從政府層面應對文化產品侵權行為的一項措施,但并不是韓國政府第一次實施版權保護,作為一個高度重視文化產業發展的國家,其不論是在立法體系還是公民教育上,一直在不斷完善其版權保護政策。從2009年開始,韓國每年都不在美國貿易代表部的知識財產監視對象國行列,這說明韓國對于知識財產的保護獲得了一定的成效,也從另一方面證明這些國內國外的雙重措施有利的保護了韓國的文化產業的知識產權。
四、對我國音樂作品版權保護的建議
(一)做好相關的組織建設
2019年4月2日,國際唱片協會IFPI發布的《2019年全球音樂產業報告》的數據顯示,目前我們的音樂付費比例很低,2019年只有5.2%,這意味著我們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雖然目前國內有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但近九成的音樂人目前還不是其會員,還是需要依托組織來幫助音樂人改變這一現狀,需要凝聚集體的力量。對此,2019年12月13日至14日,第七屆中國國際音樂產業大會開幕式暨高峰論壇正式發布了中國音樂家版權保護與服務平臺,該平臺將促進建立良好的在線音樂版權秩序和運營生態,逐步實現數字音樂的合法運營,并以此來保護中國音樂創作者的合法權益。
(二)平衡音樂人與公司的利益分配關系
唱片公司是音樂人的營銷資產,音樂人依靠唱片公司的推廣、渠道、資源快速找到受眾群體,依靠唱片公司獲得音樂版權代言、演出等收入;唱片公司則利用音樂人的作品來進行收益。從長遠發展趨勢來看,未來現代音樂行業將趨向于不再完全由唱片公司控制。越來越多的唱片公司呈現出多元化經營模式和專業化水平的趨勢。現如今,當音樂家有更多的選擇時,唱片公司應該更加積極地尋求轉型,提供不同的合作模式和更專業的服務,以此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趨勢。
(三)尋求多樣化的收入方式
現如今由于唱片公司版權條約過于苛刻,越來越多優秀的音樂人往往選擇不簽訂合同,他們要么切換到一個更寬松的一家公司,要么找到自己的第三方分銷平臺,有些人甚至選擇直接與音樂平臺合作。韓國的Musicoin就值得我們借鑒,它是韓國的一個獨具特色的音樂發行與消費系統,該平臺像出售股票一樣出售版權,其可根據持股比例收取版權使用費,且支持個人間的交易,粉絲們除了可以重新評價一首歌曲的著作權并獲得股份、每月收取特定比例的著作權費,未來產生的利潤也會回歸歌手,這種模式對于粉絲和歌手是雙贏局面。
五、結語
自從2015年版權被不斷規范以來,越來越多的音樂人也開始逐步重視版權管理,不再輕易選擇將版權轉讓,對于詞曲著作權,音樂人對于相關法律規定都比較熟悉的情況下,在簽訂合同時也更加謹慎。在這種環境趨勢下,我們應該探討未來的音樂人新的營利模式,一方面,音樂人應該加強自身的法律意識,積極維護自己的權利;另一方面,廣大唱片公司應該探求多元化發展方式,只有這樣才能夠更好地規范音樂行業,讓二者真正實現互利共贏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