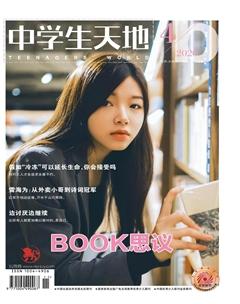假如“冷凍”可以延長生命,你會接受嗎
每次談論起哲學,總會有學生提到這樣一些問題:
“生命存在的意義是什么”“為什么要死亡”“人死后會去哪兒”……
生命因其有限性,令人敬畏并被人珍視,但人們對于永生的追求和探索卻從未停止過,早在秦朝,秦始皇就命人研制長生不老藥。現代科技一直在研發能延長人類壽命的藥物,醫學界甚至推出了冷凍人技術——在人被宣布醫學死亡后將身體冷凍,待到醫學發達到一定程度再進行解凍。
對于這些延長壽命甚至改變生命規律的舉措,有人表示贊同:“這能給對生命還留有遺憾的人一個新的機會。”也有人對此深感憂慮,認為“這些技術向人們兜售虛假希望”。你對此是怎么看待的呢?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和生命有關的話題。
討論話題前,先來了解一個思想實驗:
假設未來有一天,人類攻克了各類疾病,并最終戰勝了死亡。不過很快人們發現,因為航天技術沒有取得巨大的突破,所以還是只能生活在地球上。但是由于地球的資源有限,壽命的無限延長使得人類的整體消耗也不斷增多,最終可能造成各種資源枯竭……于是,人們制定了一個殘酷的法令:在資源沒有增長的情況下,一個人活到200歲的時候就要接受人道的“安樂死”。不過,你可以選擇一次性連續活200年,也可以選擇分成幾次活,比如先活30年,然后被冷凍100年,再活30年,接著接受第二次冷凍、第三次冷凍……畢竟在冷凍狀態下,人的消耗是很少的。
郁喆雋: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集專業深度與大眾普及于一身的“哲學小王子”。
郁教授的第1問
在這種情況下,你會選擇一次性活200年,還是分段活呢?
吳合:我會選擇一次性活200年。Live one life是一句雋永的格言,在我看來200年的時間足以彌補先前有些無法在有生之年完成的遺憾。
呂樂韜:相比一次性活200年,分段活于我而言就像是獲得不同的人生。我可以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王小波曾說:“我活在世上,無非想要多明白些道理,遇見些有趣的事。”我喜歡體驗新事物,也喜歡斷舍離,并不希望被過去羈絆。
季煒豪:我在想,200年不間斷地活著會更符合生命的自然規律。可睡眠告訴我,間斷與延續,并沒有多大區別。在我所了解的世界之外的一切,被哲人稱為“存有”。就算我醒著,某些地方的日新月異,也就是那無窮無盡的存有,我都無從了解。這一無從了解和所間隔的歲月有何不同,我想是量變所引起的質變,是多年來的小變引起的大變。
郁教授:睡眠和冷凍是一個很好的類比。因為睡眠的時候我們的意識是暫時中止的,而且只有醒來之后才能確認自己醒了。所以很多哲學家經常懷疑自己處在一場連續不斷的夢境中,如果把這個思想實驗的冷凍修改為沉浸式的虛擬實境,你愿意進入這個虛擬實境嗎?
請問一次性活200年的好處和壞處是什么?
郁教授的第2問
程思睿:一次性活200年的好處是我可以擁有一段完整的生活和記憶,延續著的也是同一種人格,而分成好幾段活看起來更像是一種對現實的逃避——一個人可以在他面對痛苦的時候選擇逃避這個世界。當然,一次性活這么久可能也有不好的地方,我們得擁有足夠的勇氣來面對一切困難。但是與能否再被解凍的不確定相比,世界,這個雖然充滿不確定性但仍遵循著某種自然規律發展的存在,更讓我有勇氣面對它。
呂芷涵:好處是能順應時代的步伐,一步一個腳印,連續地走完自己的一生。所有的情感都有充足的時間去醞釀,所有的理想都有充足的時間去追逐。到死的時候,記憶都是連貫的,回想起來也能算是蕩氣回腸。壞處是200年說實話也挺長的了,也許真的會活膩。雖然科技發達了,但也得上班工作,沒點人生理想,那就是當200年咸魚,毫無意義。
張驥:能夠一次性活200年,延長了生命的跨度,滿足了人類最原始的生存欲望,使人能夠較長時間擺脫生老病死的枷鎖,有更多的機會去感受世界和享受人生。但同時,一次性活200年也許會使人們失去對這個世界的興趣和新鮮感,過度占有、使用資源,以及引發一系列道德危機。
郁教授:“完整”是一次性活200年的最大好處。冷凍(一種人為的中斷)就破壞了人生的連續性,因而可能會出現很多預想不到的事情。思想實驗里并沒有說,如果外部環境發生了巨變,被冷凍的人不一定有機會被“化凍”……
郁教授的第3問
分成幾段活的好處和壞處又是什么?
蔣宇穎:好處是可以擁有更多可能性,見證更多變化,這在某種程度上大大滿足人們對于長生的向往。壞處是為了活著而活著。冷凍后的身軀依然是30歲、60歲、90歲的甚至更老的身軀,看似延長了壽命,實則身體機能沒有改變,思想也依然停留在過去,屆時孤身一人處于未來,能否融入未來,接受未來的文化習俗、新興思想,都是未知的。
吳合:“好的東西要節省著用”,從小媽媽就這么說。除了“分期付款”式的對生命的“節約使用”,這樣的選擇也賦予了人們操縱生命的權利。浮士德在對人生最滿意的時刻喊出“停一停吧,你真美麗”,是因為覺得一生充實了。而現在我們沒必要出賣靈魂借墨菲斯托之力,就可以多次擁有嶄新的生活,讓200歲的人生無數次綻放“第二春”,豈不美哉。當然也有壞處,除了可能事與愿違,被人遺忘,永遠被冷凍之外,我認為最關鍵的是發自內心地感到失望和疲勞。在冷凍之時,相信很多人是因為逃避的心態而沉睡,而萬一醒來之后發現問題仍然存在,那么他們注定只能在一次次的逃避與睡眠中消磨200年。
郁教授:吸引一個人分段活的最主要動因還是對新奇事物的渴望——希望在醒來之后接觸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而不是一直死氣沉沉地活在一個令人厭倦的環境里。當然,新奇本身包含了改善的意思。如果越來越差,或者基本沒有變化,也就沒什么新奇之處了,可是又有誰能夠保證會越來越好呢?
郁教授的第4問
假設接受冷凍有風險,那就是可能會被“處理掉”,而不再有機會被解凍。那么,在被冷凍之前,你想對世界說什么?
呂芷涵:我想對世界說,人心不足蛇吞象,這種“安樂死法”,總有一天會讓世界陷入混亂。
謝玉成:我對世界無話可說,畢竟這是對一個冰凍人的不負責任,但如果我能自愿選擇的話,我會把我的狗交給有緣人,請人按時給我的花澆水,我的手辦也要存放好別染了灰塵。最后告訴我的親人,我愛他們。
金珠淇:出生在這個科技發達、人類壽命能夠延長的時代,我已經感到萬分幸運。想起這樣一句話:“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既然已經痛痛快快地活過,那么醒不醒來都已經變得沒有那么重要。只愿在我靜靜沉睡之時,萬物祥和,人間靜好。
郁教授:“被處理掉”的假設并不虛幻: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一些在很小年紀就患上絕癥的人,其實就是這樣一群可能面臨無法醒來的人。甚至可以說,不僅僅是疾病,所謂死亡如達摩克利斯之劍,時時懸于每個人頭頂。每個人都面臨著隨時被處理掉的可能。
(整理:馮 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