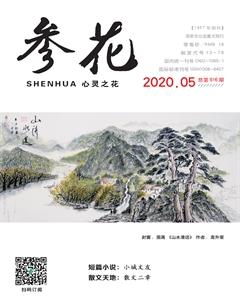艾青詩歌創作觀念探源
摘要:艾青作為中國現代詩歌的代表詩人之一,他將自我對民族的熱愛和對現實的關注凝結在作品中,他的創作對中國現代詩歌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本文主要從艾青詩歌的自我意識、苦難意識和民族意識等三個方面對艾青詩歌藝術創作觀念進行梳理,充分挖掘其詩歌的藝術魅力。
關鍵詞:艾青 詩歌 創作觀念
在中國現代詩歌的發展過程中,艾青的詩歌一方面繼承了中國詩歌會詩人的現實主義傳統,另一方面又借鑒了現代派詩人的創作藝術,成為新詩發展歷程中非常有影響力的詩人。他的詩歌緊密結合現實,充滿了積極的進取精神和飽滿的生活經歷。不論是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還是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生活里,艾青總是以“最偉大的歌手”要求自己,將自己對民族的熱愛和對現實的關注凝結在作品中,發揮著生命的光和熱。“美國評論家羅伯特·C·費蘭德曾把艾青和希克梅特、聶魯達并列為現代世界三位最偉大的人民詩人。”[5]
艾青從小被送到貧苦的農村生活,幼年的經歷使他體會到了勞動人民的善良和現實的苦難。20世紀30年代,出于對詩歌的熱愛,艾青來到了浪漫主義思潮風起云涌的法國巴黎。當時的艾青對詩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買了很多法文翻譯的俄羅斯詩人的詩集,從中汲取營養。游學的經歷和時代環境深深地刺激著他敏感的內心,在不斷地創作與探索中,艾青陸續發表了《大堰河——我的保姆》《向太陽》《火把》《我愛這土地》等一系列重要作品,并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文藝創作觀。
一、艾青詩歌中的自我意識
19世紀末,法國象征詩派風靡歐美,象征詩派的代表詩人除了早期的魏爾倫、蘭波之外,還有愛爾蘭的葉芝、奧地利的里爾克、比利時的凡爾哈倫、俄國的葉賽琳等。艾青最喜歡的是比利時詩人凡爾哈倫的詩歌,凡爾哈倫曾獲得“力的詩人”美譽,[2]他的詩歌中有很多城市勞動者的形象,這深深地影響了當時還在國外漂泊的艾青。艾青曾在他的《詩論》中說:“凡爾哈倫是我所熟悉的,他的詩,輝耀著對于近代的社會的豐富的知識,和一個近代人的明澈的理智與比一切時代更強烈更復雜的情感。”[1]“我歡喜蘭波和葉遂寧的天真——而后者的那種屬于一個農民的對于土地的愛,我是永遠感到親切的。”[6]的確,象征詩派的詩人大多都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和主體意識,他們重視人的主體性,并忠實于自我的體驗。
象征詩派的那種對自我意識的強調在艾青那里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他非常重視個人主觀意識。在艾青那首被贊譽為“歌頌土地的絕唱”《我愛這土地》中,詩人飽含情感地將自我化為一只鳥,盡管現實很殘酷,但是“我也應該用嘶啞的喉嚨歌唱”,“應該”一詞顯示了詩人超然的內心和一種自覺的意識。
“這被暴風雨所打擊著的土地,
這永遠洶涌著我們的悲憤的河流,
這無止息地吹刮著的激怒的風,
和那來自林間的無比溫柔的黎明……”[3]
艾青最終選擇了自覺地承擔一切,因為一種悲憤的情懷無時無刻不在詩人的內心深處流淌著,這是時代賦予他的使命,他向著溫柔的黎明處張望,向著太陽的方向,有著不屈與樂觀向上的精神,這是一位詩人的擔當,在他的詩歌中透露著一種強大的主體意識。
二、艾青詩歌中的苦難意識
艾青的詩歌飽含著復雜的情感因素,有人用“憂郁”一詞來形容他復雜又極具個性的氣質。作為一位詩人,艾青在創作詩歌的時候常常自覺地把個人的痛苦與人民、民族所遭遇的痛苦命運結合在一起。艾青一生經歷了許多磨難。盡管受到人生的苦難,艾青選擇再度回歸文壇,書寫出了他心中頑強的生命意志,例如在他的詩歌《魚化石》中,他把自己比作魚化石:
“凝視著一片化石,
傻瓜也得到教訓:
離開了運動,
就沒有生命。
活著就要斗爭,
在斗爭中前進”。[3]
詩人仍然沒有放棄生存的信念,他把現實的悲痛轉化成一種力量,這種不放棄的精神包含著他對現實苦難的深刻理解,因此,這首詩歌不僅是他個人的精神寫照,更是對整個民族的精神寫照。艾青詩歌中的苦難意識,使他成為一個絕對的自覺的行動者。艾青曾經說過:“我有大量的詩寫自己,但我寫自己都和時代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離開了這個時代,就找不到我的影子。”他在呼喊“中國的苦痛與災難/像這雪夜一樣廣闊而又漫長呀”,[4]那些破爛的烏篷船、蓬頭垢面的少婦、年老的母親,都陷入了生活的困頓與絕望中,詩人的情緒是非常沉重的,但詩人仍然祈求能夠給予他們一些溫暖。在這聲音背后是一種對生命的倔強與堅韌。艾青在詩中飽含深情唱著“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3]這些深厚的情感基礎都來自他對祖國、人民的極致熱愛,以及對自身所處時代的思考,從個人的苦難到民族苦難的敘述,是艾青詩歌的發展,他傾訴著民族苦難,深切地表現抗爭的精神,他那深厚而悲哀的嗓音注定使他成為時代的歌者。
三、艾青詩歌中的民族意識
偉大的詩人,總是能站在時代的制高點,為整個民族和時代而呼喊。艾青是一位民族詩人,也是一位世界詩人,他從人類共同的情感中找到了自身的位置,苦難的民族現實讓他懂得瞭望,把自己看作一個時代的歌者,積極地為之吶喊。歌德曾經在他的《箴言與省察》一文中說過:“藝術與科學,同一切有價值的一樣,是屬于世界的”“文學是人類的共同財富,現在是世界文學的時代,不放眼廣闊的世界,就會陷入自我的獨善的境地”。
艾青在西方留學期間,異域的環境使他充分感受到世界作家的眼界和胸懷。當艾青以世界的眼光回望整個中華民族,民族解放戰爭的號角吹響的時候,他迅速站在時代的前列,將憂國憂民的傳統觀念與現實緊密結合,舉起旗幟,思索著民族的未來,探尋著現代詩歌的方向。在中國現代詩歌的發展過程中,艾青主動承擔起一位詩人的職責,他時刻注視著世界的動向,努力把中國詩歌推向世界的舞臺,在海內外產生了重要影響。
1979年,艾青有機會出訪聯邦德國、奧地利和意大利。作為一位歷經苦難的詩人,當艾青面對德意志民族的分裂狀態時,他迅速寫下了《墻》《古羅馬的大斗技場》等詩歌。當時有一位外籍讀者在閱讀《墻》這首詩歌之后說:“詩人是中國人,如果不是真正的朋友,怎能如此深刻地理解我們民族的苦悶呢?”是的,艾青總能從世界人民的痛苦出發,兩相關照,從而找到世界民族的共鳴,充分地表達出詩人對德意志民族實現統一的祝福。
四、結語
縱觀艾青的詩歌創作,他一直努力地將自我的生命意識與民族的苦難、時代的召喚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與此同時,艾青能將自己的創作與世界文學聯系在一起,使得詩歌具有民族的特質和世界的特質,從而形成自己獨具特色的詩歌創作觀念。
參考文獻:
[1]艾青.詩論[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0.
[2]周紅興.艾青的跋涉[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8.
[3]彭燕郊.中國現當代抒情詩[M].長沙:湖南少兒出版社,2008.
[4]劉長華.彭燕郊評傳[M].長春: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2008.
[5]高永年.艾青:面向世界的詩人——論艾青國際題材詩[J].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09).
[6]彭建華.關于艾青對超現實主義接受的誤認問題[J].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0).
(作者簡介:陳洋,女,碩士研究生,黔南民族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講師,研究方向:現當代文學、語文教學)(責任編輯 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