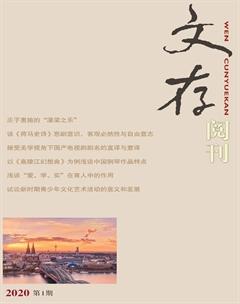淺說詩文中的“避復”
摘要:自古至今,人們在寫作中非常講究語言的錘煉,尤其在文字上講究“避復”。首先,“避復”避免了詞語的單調、重復,使語言更加活潑;其次,“避復”也可以使音調富于變化,平仄相對,呈現出錯綜變化、曲折多姿,給人以音樂美;再次,“避復”可以使語言更加精準。
關鍵詞:避復;語言;詞意
避復,是指在同一語句或上下文中,以及相距較近的語段里,在一般情況下,都應盡量避免連續或多次使用語音或書寫形式相同或相近的詞語。劉勰《文心雕龍·裁》:“同辭重句,文之疣贅也”,反對字詞重復使用。自古至今,人們在寫作中非常講究語言的錘煉,尤其在文字上講究“避復”,“避復”是語言追求的一種技巧。
首先,“避復”避免了詞語的單調、重復,使語言更加活潑。如:《詠懷古跡·其三》(杜甫):
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
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月夜魂。
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第一句中“群山萬壑”,詩人為什么不直接寫為“千山萬壑”?因為詩的尾聯“千載琵琶作胡語”有“千”字,這首七律總共才56個字,如果首句首字又用此字,明顯感覺重復。杜甫將“千”改為“群”,未必是此字有多么精妙絕倫,不過是他為了避免雷同,刻意找個近義詞代替而已。“群”與“千”都可以泛指很多,而且都是平聲。假如詩中保留的是第一個“千”字,而換掉第二個,那就不止改掉一個字,而是必須將“千載”換作“百代”之類的詞了。如此一來,韻律又不協調,所以還是改掉前一個好。
又如“滄海未全歸禹貢,薊門何處盡堯封?(《諸將五首·其三》)”詩中“禹貢”與“堯封”都是指版圖。“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諸將五首·其四》)”詩中“無消息”就是“久寂寥”之意。
其實不僅僅是詩,對于其他文體,許多作者也相當注意表達方式的繁復多樣,這在古代的詩詞歌賦中幾乎隨處可見,如:
“北通巫峽,南極瀟湘(范仲淹《岳陽樓記》)”;“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王勃《藤王閣序》)”,文中的“通”和“極”、“與”和“共”詞意相同。
《屈原列傳》:“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稱”、“道”、“述”如果分開解釋,或許有些區別,但在文中意思都是表示“提到”“稱道”等意思,之所以用不同的詞,也只是為了避復而已。
《諫太宗十思疏》:“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敬”就是“慎”。都是認真嚴肅、全神貫注地對待的意思。這里不說“慎始而慎終”,顯然是為了避復。又:“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盡”“竭”,意思相同。“恩所加,則思無因喜而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上下文分別用同義詞“因”“以”,是虛詞的避復。
其次,“避復”也可以使音調富于變化,平仄相對,呈現出錯綜變化、曲折多姿,使人感到活潑清新、起伏有致、音韻鏗鏘,給人以音樂美。
“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范仲淹《岳陽樓記》),文中的“銜”和“吞”、“居”和“處”詞意相同。
再看《病梅館記》:“梅以曲為美,直則無姿;以欹為美,正則無景;以疏為美,密則無態。”句中的“姿”、“景”、“態”這三個字的位置在原文中若加以重新安排,內容也不會受到什么影響。意義相近,避復而已。
“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諸葛亮《出師表》),文中的“臣”和“士”詞意相同。
“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其中“佳”“麗”“美”三復其文,造句相同,而選字各異。不僅是行文避復的問題,而且提出了避復的方式和修辭效果。古人在寫文章時遇到上下文有相同的字重復出現的情況,往往用同義詞互換,就是選擇不同的詞來表達相同的意義,如“佳”、“麗”、“美”三詞不同,卻同樣表達“美麗”的意義。同義詞互相配合,可以避免行文重復、呆滯,起到用詞豐富多采,行文跌宕起伏,生動活潑的表達效果。
“于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賈誼《過秦論》)文中的“之屬”、“之徒”和“之倫”詞意相同。
以上這些情況都是在對偶句、排比句的對應位置上,選用意義相同或相近的詞語避復,顯示用語的變化,增強語言的韻味,給人一種回環往復的音樂美。
再次,“避復”可使語言更加精準
有些同義詞,基本意義相同,但感情色彩有別,或抑或揚,或褒或貶,這是由于人們在用詞時的愛憎、褒貶和等級觀念、宗法思想的影響而產生的差異。利用同義詞感情色彩的差別,選擇適當的詞語來表現對人物、事件的態度,是人們常見的一種表現手法。讀者通過這些精心選用的詞語,可以準確地把握人物的愛憎好惡,從而深入理解作品的思想內容。
如:“我已經說過: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但這回卻很有幾點出于我的意外。一是當局者竟會這樣地兇殘,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國的女性臨難竟能如是之從容。”(魯迅《記念劉和珍君》)其中“竟會” 、“竟至” 、“竟能”三詞乍看相同,其實不然。“會”表示學得某種本領,“至”表示到了什么地步,“能”表示具備某種能力,三者分別用于不同場合,表示著不同的感受,各臻其妙,如果統一用其中的任何一個,就不免失之粗糙。
“避復”是寫作的基本功。如果一篇文章充斥著大量雷同的詞語,就會使語言單調而缺少變化。“避復”的運用,作者必須具有豐富的詞匯。“多財善賈,長袖善舞”,只有儲備足夠的詞匯供自己隨意選用,才能避免重復單調,從而顯示語言運用中應付自如、活潑瀟灑的風姿,增加了語言的表現力。
參考文獻:
[1]張昭政.文求變化須“避復”[J].學語文,2004(2).
[2]劉桂華.淺談古漢語同義詞的修辭作用[J].安徽教育學院學報,1993(2).
作者簡介:
李意蘭(1965年-),女,漢族,湖南長沙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學和應用文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