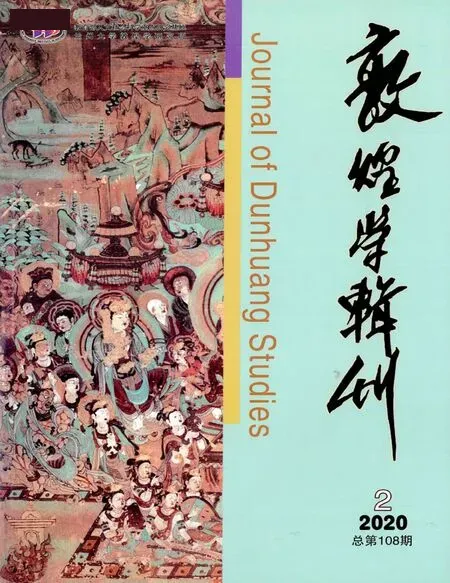瓜州榆林窟道教遺存谫論
李博雅 李 國
(1.藥明康德公司,上海 200120;2.敦煌研究院 敦煌學信息中心,甘肅 敦煌 736200)
榆林窟,又名榆林寺、萬佛峽,是我國著名的石窟群之一,是敦煌石窟藝術體系的一個支系。石窟距瓜州縣城南約70 公里,現存洞窟42 座,位于狹窄的山谷中。石窟分布兩岸,踏實河(又名榆林河)自南向北穿流峽中,水流湍急,聲震山谷,河岸雜樹叢生,紅柳掩映,特別到晚秋時節,黃葉滿谷,碧空如洗,峽谷美景一覽無遺。以往,前賢們關注焦點一直在豐富的佛教壁畫與精美的彩塑上,而對石窟中的道教壁畫、塑像以及道教游人題記等遺存雖有所記,但并未過多關注和深入探究,尤其是現存清光緒年間一方道俗書題敘載稀世珍寶象牙佛在榆林窟發現與失而復得、重新回歸曲折經歷的匾額,內容頗為豐富。鑒于此,筆者在對瓜州榆林窟道教游人題記調查整理時,對這些大多不為人知的材料進行了考察,現擬從榆林窟道教遺存這個視角對這些新資料試作一些梳理與探討,不妥之處,敬請方家教正。
一、瓜州與榆林窟歷史探源
自古以來,瓜州與敦煌為同一文化圈。漢代以前,敦煌、瓜州曾先后居住有羌人、烏孫人、月支人和匈奴人。西漢元狩二年,武帝開辟河西,派霍去病統兵出擊匈奴,給匈奴以重創。盤踞河西的匈奴渾邪王率民舉地降漢。①李正宇《漢朝和平接管河西,不由攻奪強占》,《敦煌研究》 2019 年第1 期,第80-84 頁。當河西歸附漢朝版圖后,就先后設立了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并“徙民以實之”。②[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第189 頁。敦煌郡所轄敦煌、效谷、龍勒、冥安、廣至、淵泉六縣。其中冥安、廣至、淵泉縣都在后來的瓜州境內。西晉元康五年分敦煌郡之冥安、宜禾、伊吾、深泉、廣至等五縣,與酒泉郡之沙頭縣,新設會稽、新鄉二縣,共合八縣置晉昌郡。③冥安,《晉書》 作“宜安”,據《元和郡縣志》,應作“冥安”。深泉:應為“淵泉”避唐諱更名。今瓜州之地大體就在晉昌轄境之內。東晉時,北方先后經歷十六國統治,其中在瓜州一帶主要經歷了前涼、前秦、后涼、西涼、北涼的統治。后涼段業分宜禾入涼興郡,余七縣未變。北魏改名為會稽郡,分廣至、冥安、淵泉入涼興郡,更名為常樂郡。北周并二郡為會稽郡,更名水興郡。隋初并入瓜州(今敦煌),至大業三年始改為敦煌郡。唐武德二年設瓜州(治所敦煌),五年更名為西沙州,貞觀七年省“西”字稱沙州,另于晉昌縣立瓜州,轄晉昌、常樂二縣,治晉昌(今瓜州東南)。隋唐時玉門關從敦煌東徙至瓜州,由此說明了瓜州地理位置之重要。唐初玄奘西行求法,偷渡玉門關,就是當時瓜州之玉門關。
瓜州榆林窟諸窟之創建年代及其在中國佛教藝術史上的地位和價值,國內外時賢論著頗豐,茲不贅述。但若據第25、39 等窟均有中心柱,與敦煌莫高窟魏、隋諸窟形制別無二致,且壁畫多有重層,下層壁畫多系唐代早期制作,第25 窟前室東壁還存有“光化三年十二月廿二日”題記;“因此不難推斷,榆林窟開窟時間當在唐代之前的魏、隋時代,與敦煌莫高窟開窟時間相去不遠。④敦煌文物研究所《安西榆林窟勘查報告》,《文物參考資料》 1956 年第10 期,第9-21 頁。”
榆林窟歷經唐、五代、宋、回鶻、西夏、元、清各代,超越一千多年的營建。瓜州與敦煌地域相接,山水相連,文化同脈。榆林窟的洞窟形制、壁畫和彩塑、題材內容和藝術風格與敦煌莫高窟極為相近。學術界習慣將瓜州榆林窟納入敦煌石窟體系。可以說,瓜州榆林窟與敦煌莫高窟共同創造了敦煌藝術的輝煌。與莫高窟相比,榆林窟又有其自身的藝術特點,如:吐蕃時期營建的第25 窟繪畫是中國同期壁畫藝術中的精華,五代、宋時期,榆林窟所新建和重修的近30 座石窟,是榆林窟的主體。西夏、元代洞窟及其以藏傳密教為主的不同民族的壁畫藝術,是中國晚期石窟寺壁畫藝術的精萃,補充了莫高窟之不足。榆林窟藝術保存了絲綢之路中西文化和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信息,其重要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及其精美的壁畫是敦煌石窟藝術寶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中晚期佛教石窟寺壁畫藝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①敦煌研究院編《榆林窟藝術》,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14 年。
二、榆林窟的道教遺存及佛道關系
瓜州榆林窟歷代壁畫保存完好,很多彩塑都經過清代重塑;由于榆林窟在清代后期主持多為道士,佛窟功能逐漸發生變化,許多洞窟成為了佛教與道教的融合體。同時也有像第1、7、8、11 等窟建成后亦成為單一道教活動場所。清代榆林窟的修繕歷時久、規模大、范圍廣。從作為古代佛教遺存的角度來看,清代對榆林窟的修繕實為一種帶有嚴重破壞性質的修復,很大程度上對石窟本體造成了難以挽回的損失。但若換一個視角,榆林窟中的道教繪塑,從一個側面客觀揭示了佛道相融的關系。當然,因受時代和文化修養等因素制約和影響,在經濟、技藝、創新等方面已很難趕超先代。
榆林佛窟在清代滲入道教題材遺存簡況如下:
第1 窟,清代。東壁開一龕,內塑山神、土地道教方神二身,龕外南側為夜叉攜虎,北側為侍者牽犬。東壁龕內屏風五扇,畫茶花、母子觀溪、蝴蝶荷花、山林、花鳥;西壁畫寒梅三鵲,南壁竹石七雀圖。
第7 窟,清代。老君洞。東壁開一龕,內塑道教老君及二童子。(圖1)

圖1 榆林第7 窟老君及二童子
第8 窟,清代。三清洞。東壁神壇上塑道教最高神靈元始天尊、靈寶天尊和道德天尊“三清”及侍從等神像五身。東壁畫山水人物花鳥屏風六扇;南、北壁東側各畫花卉屏風三扇。
第11 窟,清代。龍王洞。東、南、北壁五龕內塑以龍王為主尊一鋪五身。正壁上懸泥制匾額一方,上題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六月“澤流汪濊”四個大字,泥匾四邊亦繪有老君乘鶴、香爐、花瓶、梅花等,四角畫太極圖。窟頂模仿中國傳統建筑椽、檁的表現形式,在檁條上繪出花卉圖案及雙排組合式八仙圖六幅12 身。其中,東端倆倆相對兩組四幅繪出神話傳說中的八仙;西端對應一組把何仙姑和清代成為女神仙的藍采和同處重復各畫兩身。(圖2)

圖2 榆林第11 窟內景圖
第23 窟,清代重修。主室東、南、北壁馬蹄形佛床上塑道教全真七子等神像十五身。窟頂中央畫乘鶴手捧陰陽魚老君一身,四周貼紙畫八仙圖;北壁、東壁各畫道教故事,南壁畫八仙傳奇。(圖3)

圖3 榆林第23 窟主室佛床清塑道教神像和窟頂清畫老君及八仙圖
第35 窟,清代重修。文昌洞。主室中心佛壇上塑民間和道教尊奉掌管士人功名祿位之神文昌帝君及“天聾”“地啞”侍童像。前室南壁像臺上塑持矛道教神像一身;北壁像臺上塑道教神像一人一馬。
第37 窟,清代。正壁上懸泥制匾題“虛皇閣”。西、南、北壁馬蹄形佛床上塑虛皇元尊等道教神像十一身。主尊背屏畫蝠菊團花四龍椅座,兩側屏風各三扇畫花鳥。南、北兩壁屏風十二扇,畫人物山水花鳥。(圖4)
第40 窟,清代重修。玉皇洞。窟門上方彩繪匾額一方,上題“有感必應”,匾額四邊畫花卉等,四角畫太極圖。西、南、北壁馬蹄形佛床上塑玉皇等道教神像十九身。主尊背屏畫蝠菊團花四龍椅座,兩側屏風十二扇畫人物山水;南、北壁各十四條幅畫人物、山水、花鳥。(圖5)

圖5 榆林第40 窟內景圖
第6 窟,民國重修。中心佛壇壇前塑寶瓶蓮株成龍門形雙龍盤柱,柱上懸塑八仙分立兩側。
以上榆林窟現存的這些道教塑像和繪畫,大致囊括了“從中央到地方”、從天上到地下、從陸地到水(海)里中國上古神話傳說中的道教大小神仙和民間崇拜雜神及他們的傳說、經文故事,以及各類山水花鳥裝飾等等,這在敦煌石窟群中具有突出的特色。這種場景,實際上已經讓榆林窟成為一處完整的道教活動場所,使得清代以來榆林窟的道教活動尤其興盛。榆林窟道教活動的題記亦比比皆是,大多書寫工整、內容豐富,有真情實感,具有相對較高的水平。如榆林第6 窟二層門北西壁潚之題壁詩(圖6):

圖6 榆林第6 窟二層門北西壁潚之題壁詩
石硤疊疊水接天,綠樹陰濃罩河灣。一輪明月千峰掛,幾洞神仙半壁懸。
雨洗青崖添潤色,風繞雄峙起曾煙。鳥與斜陽平空盡,云岫石城曠野閑。
誰修茅庵誰養性,誰煉金丹誰坐禪。①煉金丹,指修仙求道。唐寅《言志》 詩:“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閑來寫幅青山賣,不使人間造孽錢。”[明]唐寅撰,[清]唐仲冕編《六如居士外集》 卷1,清嘉慶六年(1801)刊本。好景愧無佳句賞,囊空辜負一佛山。
尤其是“鳥與斜陽平空盡”句,作者化用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絕句描述映照榆林河峽谷兩岸陡峭崖壁,于塞下榆林河波光蕩漾,水中倒影一片紅色美景,勾勒出一幅婀娜多姿寧靜致遠的畫面。
清雍正年間,安西就有關帝廟、城隍廟、龍王廟等道教場所,瓜州狐仙廟、橋灣永寧寺、東千佛洞、榆林窟以及蘑菇臺子王母宮、老君廟等處均有道人居住,負責看管廟宇,保護寺內文物,焚香供祭,化緣修補寺廟等。每年的農歷六月初六,瓜州地方各鄉各鎮都會有道士活動,給民眾念經布道,敬奉神靈,為婚喪嫁娶選擇吉日或看陽宅、斷瑩地風水;榆林窟亦接待廟會香客。榆林第6 窟二層民國丁巳(1917)郡歲進士柳學孔筱魯氏天貺節四首懷古、寫景題詩,就反映出一定的道教信仰情結和信仰遺俗。
榆林窟作為社會化宗教和民間信仰的活動場所,兼備了傳承性、群眾性、復雜性和區域性的特征。窟內不僅佛道繪塑相映,釋道儒三教和諧共存壁題也屢見不鮮。一方面是佛道融合,最為典型的是第6 窟清道光十八年(1838)釋子劉理璋、玄門弟子朱慶壽聯合題寫“文□玉滿積無量功德/眾列成行吾□□□□/信不免無常言□□君/白學□銀燒丹煉藥苦弗/參吾下金木水火土□或/山林釋迦仸②仸(fó),古同“佛”。雪山修禪苦/行六年功成滿吾下生老/病死苦寂滅歸空”的題記。內容雖然殘損嚴重,但可以看出,其中既涉及到了對道教燒丹煉藥的學習和對五行之說的參究,也談到了佛祖釋迦牟尼雪山苦修和生老病死、苦集滅道等佛教義理,字里行間既有佛教內容,又有道教信息,落款釋子和道士聯袂題名,關系非常融洽,他們在對佛教和道教義理的認識方面也很一致。又如第6 窟淵泉道士書題,反映了佛道在信仰層面的融合,身為道門人士而期望通過對榆林窟“萬佛”的朝拜,保佑一家大小安寧康健和富貴長生。再如第8 窟清光緒十一年(1885)五月十八日羽士在“天師殿前叩誦《皇經》 一部”題記,黃紙帖后抄引《醒世詩》:“為人不必苦貪財,貪得財來天降災。即是有錢人不在,不如人在少貪財。無名之財不可貪,不能………”(圖7)。實際上,勸善懲惡幾乎是所有宗教信仰的核心教義之一,道教亦不例外。另一方面是三教融合。如榆林未編號窟(第30 窟西北原郭元亨住所)前室西壁“仁山道人”題詩,勸勉追求仙道者,不能僅僅依靠服食丹藥以求長生,更要通過自身的苦修參悟成道,并指出“三教用工同一理”,揭示了儒釋道三教在義理與踐行方面深刻的同一性。這與唐宋三教融合的發展方向和金元以降道教中三教融合修煉理論和實踐是完全一致的。①李國《榆林窟道教游人題記芻議》,《敦煌研究》 2020 年第3 期,第27-36 頁。
清代以來的榆林窟,道教人士不僅虔心守護著佛教石窟圣地的壁畫與彩塑,在繁多的游人題記中還真實地記錄了儒、釋、道徒及信眾在榆林窟修行、朝禮、巡游的活動軌跡,體現了其本身所具有的宗教文化價值;同時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清及民國時期瓜州歷史之一斑,部分題記內容為史書或方志所闕載,為輯補地方道教史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新資料,無疑具有獨特而珍貴的歷史價值。總括而言,榆林窟的道教遺存為我們研究清代以來榆林窟乃至瓜沙地區宗教信仰變遷,提供了豐富而可靠的實物資料,在整個宗教史的研究方面具有重要價值和意義。

圖7 榆林第8 窟清光緒11 年黃紙帖后抄引《醒世詩》
三、道士與榆林窟象牙佛的傳奇經歷
瓜州榆林窟第6 窟前平房小院門內,懸掛有一方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的墨書匾額,內容如下:


這份文獻詳細敘載了稀世珍寶象牙佛在榆林窟的發現經過與失而復得重新回歸的曲折經歷①李春元《安西象牙造像〈請回象牙佛匾文紀〉 》,《隴右文博》 2003 年第1 期,第60-63 頁。,同時它也是榆林窟100 多年歷經磨難的歷史見證。

圖8-1 象牙佛外立面圖像

圖8-2 象牙佛內立面圖像
清乾隆年間,喇嘛吳根棟(一說云游道士)云游至此,見洞窟殘存,佛像毀壞,決心修復洞窟,遂四處游說,募集資金。吳喇嘛在清除榆林窟東崖第5 窟(睡佛殿)前的積沙時,偶然間從積沙中獲得了一件非常珍貴的象牙佛。據載,剛從沙子中挖出時,其外用黃布包裹,內裹七層布帛和一層哈達。該佛像是用象牙從中一剖為二后雕鑿而成,兩瓣象牙用銅合頁相連,象鼻內側有鉆孔,可以完全扣合并用繩固定。扣合后高15.9cm,上端寬11.4cm,中部寬15.7cm,下端寬14.8cm,兩邊對合厚3.5cm。其外刻一尊騎象菩薩,雙手持覆缽式相輪寶塔,除象以外還刻有十個人物像,描繪的是佛傳故事中的“乘象入胎”的一節內容。從中間打開后,兩邊各有27 格,共有54 格,每一格都刻有一段佛本生故事,共有54 個故事。共刻有人物279 個,動物、塔、車馬12個。他們共同構成了一幅由佛祖誕生到涅槃的畫卷。如最上面四格描繪的是摩耶夫人入夢,到樹下誕生悉達多太子的場面。正中18 格和兩邊延伸出的四格是悉達多太子降生后,九龍灌頂、仙人占相、姨母撫養、太子學習、太子角射、灌頂立太子、閻浮樹下思惟、四門游觀、出家四愿、耶輸陀羅入夢、后宮嬉戲、夜半逾城、山中辭別、剃發染衣等情景。下面的22 格描繪的是矯陳汝五士追尋、山中苦行、降魔成道、二商奉食、鹿野苑說法、娑羅樹下涅槃等場景。(圖八1、2)從形制和形象來看,這件象牙造像具有印度藝術風格,應該是傳自印度的藝術品,制作年代可能在唐代之前,后來由印度傳法高僧或中國去印度學經僧人攜歸中國,是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罕見物證。北京大學陳萬里教授考證認為,象牙佛系印度作品,“為唐代西游僧侶所攜歸者。①陳萬里《西行日記》,北京:樸社出版,1926 年,第99 頁。”中央研究院西北科學考察團歷史考古組閻文儒②閻文儒《談象牙造像》,《文物參考資料》 1955 年第10 期,第81-84 頁。、向達、夏鼐及故宮博物院顧鐵符③顧鐵符《“象牙造像”說明》,《文物參考資料》 1955 年第10 期,第80 頁。和甘肅省博物館喬今同④喬今同《一件珍貴的象牙造像》,《甘肅日報》 1958 年1 月3 日第3 版。對象牙造像亦進行過研究考證,他們認為系印度恒河上游中世紀第三期巴拉胡提王朝(相當于中國初唐時期)犍陀羅佛教雕刻品。金申綜合研究認為,舊藏榆林窟象牙龕像來自犍陀羅,是典型的克什米爾雕刻風格。“如果此牙雕為克什米爾所作,那么它應是由克什米爾僧人攜帶著沿罽賓古道通過吉爾吉特,穿洪扎河谷,越過紅其拉甫山進入皮山,通過和田,后幾經輾轉,從西域南麓流傳入榆林窟的。⑤金申《榆林窟象牙龕佛像及相關攜帶式龕像》,《2000 年敦煌學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紀念敦煌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 石窟考古卷,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 年,第340-364 頁。金申《從舊藏榆林窟的象牙龕像談及相關的攜帶式龕像》,《佛教美術叢考》,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年,第73-89 頁。參閱國家文物局教育處編《佛教石窟考古概要》,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年。”
有關象牙佛造像的文獻記載與民間傳承,至遲在南北朝時業已出現。《廣弘明集》卷十五梁武帝象牙詔曰:“大同四年七月,詔曰……上虞縣民李胤之掘地得一牙像,方減二寸,兩邊雙合,俱成獸形。”《南史》 卷七十八載:“槃槃國,梁中大通元年、四年,其王使使奉表累送佛牙及畫塔……”“丹丹國,中大通二年,其王遣使奉表送牙像及畫塔二軀。”《法苑珠林》 卷五十二引《西域志》 說:“王玄策至大唐,呈使獻物龍珠等。具錄大真珠八箱,象牙佛塔一、舍利寶塔一、佛印四。”由此可見,自六朝至隋唐以來,以佛教為題材的牙雕造像藝術品在中國非常流行,且作為佛教圣物而備受尊崇。
無意間從流沙中得到這尊稀世珍寶,便成為榆林窟的鎮窟之寶和歷任住持的權力象征。清嘉慶十二年(1807),吳根棟在榆林石窟內坐化前,將象牙佛傳給掌門弟子;此后,歷代住持相傳收藏、供養著象牙佛。同治年間,青海青頭山回民馬文祿、陜西西安回民白彥虎聚眾叛亂,并相繼攻陷了肅州、玉門、瓜州等地,戰亂殃及榆林窟。叛匪綁架了住持道人楊元,逼其交出象牙佛。弟子李教寬得到楊元暗示,便偷偷攜帶象牙佛離開榆林窟。匪兵得不到佛像,竟將楊元殘害致死。隨著時間的推移,又過了30 多年,到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榆林窟住持道人嚴教榮從一個玉門商人口中打探到金塔縣塔院寺有一尊象牙佛,與此前密藏于榆林窟的象牙佛非常相似。經多方核實,最后確定金塔縣塔院寺的象牙佛就是當年李教寬從榆林窟帶走的象牙佛。次年冬,由榆林窟住持嚴教榮和瓜州鄉民王祖英、溫國明、張榮等人組織親自赴金塔迎請佛像。幾經周折,象牙佛終于重新回到了闊別數十年的瓜州榆林窟。光緒末年,榆林窟再遭匪劫,為保護象牙佛,嚴教榮與一小道士又被殺戮。1925 年,美國探險家、考古學者華爾納(Landon·Warner)到安西榆林窟考察,北京大學陳萬里教授作為中國專家隨行考察,期間曾受安西縣長陳芷皋之邀“赴縣署一觀”象牙佛,并“攝片十余,撫拓數紙”。陳氏在《西行日記》 中有這樣記述:“據稱清初時某僧于積沙中獲之,同治回亂,踏實一帶均被蹂躪。道人星散,牙佛亦遂失蹤。亂平,遍覓之,始悉已移置金塔,初奉于塔院寺,尋在梁貢士家,后為盛居士所供養,地方人民即醵金推代表,往金塔求之,往返半年,幾費唇舌,居然佛歸原處,此光緒三十年冬間事也。①陳萬里著《西行日記》,第98-103 頁。”民國十九年(1930),馬榮貴道長化緣遇匪跳崖自盡,他是為象牙佛喪命匪禍的第三任道長。之后,象牙佛便秘密藏身于瓜州境內。民國二十九年(1940),象牙佛傳到了住持道人郭元亨手中。民國三十年(1941),國畫大師張大千偕同范振緒赴榆林窟調查、臨摹壁畫,期間張大千曾許諾郭元亨道長白銀兩千兩并送他去五臺山修行,懇請一睹象牙佛容顏,未果。同年秋,國民黨中央委員、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巡視河西期間,亦向郭元亨詢問象牙造像事,郭道士以“不知道”婉拒。民國三十二年(1943),西北軍閥馬步芳部下流竄到榆林窟,強迫郭元亨交出象牙佛,郭道士答復佛像不知去向,遭到了這伙兵痞慘無仁道的摧殘。民國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1943-1944),閻文儒先生路經瓜州時,曾懇請瓜州地方賢達想一睹傳說中的象牙佛,都均未如其所愿。
象牙造像的珍貴之處除了其本身所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外,還體現在其鮮為人知的流傳經歷上。更為重要的是,歷代道士們作為看管石窟,清沙疏路,焚香供祭,化緣修寺,保護石窟文物的重要角色,維系了榆林窟古代文物遺存的延續,其重要作用和功績是絕不容忽視的。為保藏好象牙造像,榆林窟先后有八位主持和道士付出了生命代價。1950 年春,由最后一代主持道人郭元亨②李春元《郭元亨先生生平傳略》,《陽關》 1992 年第1 期,第38 頁下轉第25 頁。歷盡艱辛,將妥善保管的珍寶象牙佛捐獻給安西縣人民政府。1954 年4 月,象牙佛造像在蘭州五泉山公園首次展出,引起社會各界極大關注,同年8 月移交甘肅省文物管理委員會。1956 年,移交甘肅省博物館。1958年,這件出土于榆林窟的稀世珍品移交至中國歷史博物館(今國家博物館)永久珍藏。
四、結語
從上述內容亦可看出,榆林窟道教遺存相當豐富,他們既是調查研究清代道教歷史的重要資料,也是研究這一時期佛道關系的珍貴史料,值得我們關注并作深入研究。
關于榆林窟道教的豐富文化遺存與道士的事跡,1941 年于右任先生巡視河西赴榆林窟游覽時所作《萬佛峽紀行詩》①于右任《西北紀行詩》,《說文月刊》(渝)第3 卷第10 期,1943 年,第5-8 頁。作了精辟的描述:
隋人墨跡唐人畫,宋抹元涂覆幾層;不解高僧何事去?獨留道士守殘燈。
層層佛畫多完好,種種遺聞不忍聽;五步內亡老道士,②于右任詩句夾注:“鐘道士,商州人,八十余,民國十九年為匪所害,并將藏經毀去。”十年前毀一樓經。
由此,面對榆林窟珍貴的文化遺產,我們也不應該忘記榆林窟的歷代全真道士為了保護古代佛教文化遺存,不惜犧牲生命,他們亦可稱為一方文脈道統的守護者。可以說,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道士們雖然默默無聞,但他們不拘教規,明辨是非,心存大義,志系國寶,體現出了作為出家人寬廣的胸懷、優良的品行和高度的社會責任心。
附記:本文初稿承蒙敦煌研究院馬德研究員、蘭州大學劉永明教授閱審并提出寶貴的指導意見;稿件修改時筆者曾多次赴榆林窟調查,蒙宋子貞、李立新兩位所長及同事提供幫助;課題組余生吉、王海彬對調查亦付出辛勞。文中插圖由敦煌研究院提供,謹此一并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