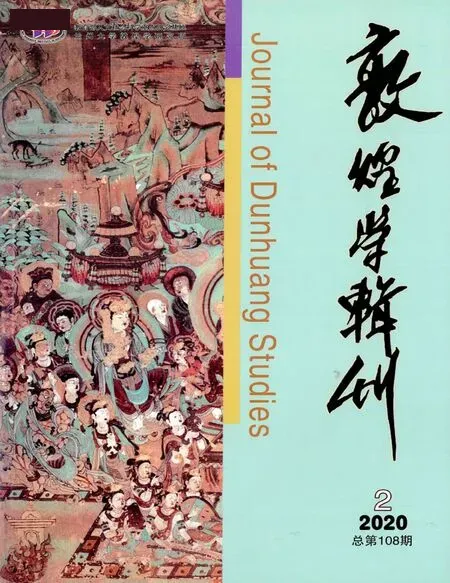20 世紀上半葉法國漢學之發展
——以《通報》 為中心的討論
丁斯甘
(1.蘭州大學 敦煌學研究所,甘肅 蘭州 730020;2.蘭州城市學院 外國語學院,甘肅 蘭州 730070)
法國漢學起始于18 世紀,來到中國的法國傳教士翻譯、闡釋和推廣中國的古典典籍,引起了法國人乃至歐洲人的廣泛興趣。1814 年12 月11 日法蘭西學院開設了漢語講座,標志著專業漢學的形成。雷慕沙(Abel-Rémusat,1788-1832)、儒蓮(Stanislas Julien,1797-1873)是19 世紀法國最有代表性的漢學家。法國漢學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推動法國漢學進入繁榮期。他的研究涉及多個漢學領域,沙畹的《史記》 譯著手稿中包含了導言、注釋和詳盡的目錄,在當時的歐洲“都缺乏與之匹敵者”①[法]戴密微著,耿昇譯《法國漢學研究史》,耿昇編《法國漢學史論》 上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15年,第116 頁。,他培養了包括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馬伯樂(Henri Maspéro,1883-1945)、葛蘭言(Marcel Granet,1884-1940)在內的一批才華橫溢的法國漢學家,他們使20 世紀上半葉的法國漢學尤為光彩奪目,可稱為“沙畹——伯希和時代”,①桑兵《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37 頁。巴黎也獲得了“西方漢學之都”的美譽。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則使法國漢學界失去了多位漢學巨擘,葛蘭言、馬伯樂和伯希和相繼去世給予了法國漢學界沉重的打擊,因此1945 年可以稱為整個法國漢學研究史上“重要的分水嶺”②[法]謝和耐著,耿昇譯《二戰之后法蘭西學院的漢學研究》,任繼愈主編《國際漢學》 第2 輯,鄭州:大象出版社,1998 年,第466 頁。。漢學史研究屬于學術史研究范疇,以文獻學為中心的漢學具有較高的客觀性與穩定的演變特征,通過整理研究成果可以總結其漢學發展軌跡。《通報》(T’oung Pao)是法國最具權威性的漢學期刊之一,多位著名漢學家都曾擔任其主編。以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擔任主編時期發行的《〈通報〉,1890-1944 年四十七卷總索引》(Index Général des Quarante Sept Premiers Volumes années 1890-1944,1953)為依據,梳理《通報》 所刊發的文章有助于把握20 世紀上半葉法國乃至歐洲漢學史的整體脈絡和階段性特征。
一、法國漢學期刊《通報》 概述
1889 年,考狄(Henri Cordier,1894-1925)、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1840-1903)和布里爾的兩位編輯思道普拉爾(M.F.de Stoppelaar,生卒不詳)和奧爾迪(A.P.M.van Oordt,生卒不詳)在前往奧斯陸準備參加東方學家會議的列車上提出創辦一份東亞研究的學術期刊,布里爾出版公司(Brill)負責印刷出版,考狄和施古德聯袂擔任主編,1890 年《通報》 創刊。施古德去世之后,沙畹于1904 年繼任施古德的主編一職,與考狄一起成為《通報》 的主編直至1918 年去世。考狄于1917 年至1919 年獨自擔任主編工作,自1920 年起伯希和成為《通報》 的新一任主編,與考狄一同負責主編工作。1924 年考狄去世,伯希和于1925 年至1935 年期間獨自擔任《通報》 主編一職。1936 年戴聞達(J.J.L.Duyvendak,1889-1954)與伯希和合作共同擔任主編工作,兩人合作近十年直至伯希和于1945 年去世。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法國漢學家戴密微繼任《通報》 主編一職。
《通報》 一般以一年一卷的規律發行,每卷有一至六期不等,截止1945 年共發行47 卷,其中1920 至1921 年、1925 年至1926 年、1934 年至1935 年分別合并為一卷,1927 年至1929 年、1938 至1940 年分別在三年中發行了兩卷,因二次大戰的原因1940年至1942 年上半年合并為一卷,1942 年下半年至1944 年共發行一卷。1890 年至1899年出版的《通報》 被編為第一集(Série I),1900 年至1909 年在《通報》 封面就注明了Série II(第二集),自1910 年起期刊封面用更為簡潔的卷號(vol.)替代了集號“Série”,此后刊物一直使用卷號編號順延下去。1935 年《通報》 將每期的期號(No.)更改為冊號(Livr.),并沿用至1992 年。期刊的定價也略有調整,1890 年至1912 年每卷為12 荷蘭盾,1913 年至1916 年漲至14 荷蘭盾,1917 年至1944 年每卷的價格固定為16 荷蘭盾。
《通報》 截止1944 年,期刊共出現了13 個欄目,欄目出現的次數依次為:“學術論文”(Articles de fond)共47 次、“書目”(Bibliographie)42 次、“雜識”(Mélanges)41 次、“訃告”(Nécrologie)40 次、“紀事”(Chronique)36 次、“評論簡報”(Bulletin Critique)33 次、“通信”(Correspondance)21 次、“按語與征詢”(Notes and Queries)19 次、“雜錄”(Variétés)15 次、“收到贈書”(Livres Re?us)6 次、“通告”(Annonces)3 次、“期刊文章”(Revue des périodiques)2 次、“官方資料”(Documents officiels)1 次。
《通報》 的欄目可以分為專題類欄目、互動類欄目和資訊類欄目。專題類欄目主要刊發專題文章,包括專業性質的漢學論文、經典釋讀、混合性質的探險家游記、田野調查等文章、零散性質的書目、書評、訃告等,包括“學術論文”欄目、“雜識”欄目、“評論簡報”和“書目”欄目和“訃告”欄目。每期發表一至五篇不等的論文,撰稿人多以專業漢學家為主,文章的學術研究價值大。《通報》 1890-1944 年“學術論文”欄目每期刊載三篇左右的學術論文,一般在30-50 頁,有時甚至有100 頁以上的長文。《通報》“雜識”欄目數量不定,內容精煉、類似于作者隨筆的研究札記,或者是對某一研究成果的補充。“評論簡報”和“書目”從創刊就占據了重要地位,“書目”欄目基本囊括了歐洲、美國、中國、日本等出版的漢學專著或期刊,介紹出版物的基本信息,不做任何評價。“評論簡報”是主編對文章或著作所闡述的觀點進行評論,發表個人看法,篇幅相對較長。“書目”和“評論簡報”欄目對西方語言、漢語和日語等漢學著作進行介紹和評論,語言犀利,石田干之助認為該欄目“最為豐富,而且最有權威”。①[日]石田干之助撰,唐敬杲譯《歐美關于中國學的諸雜志》,《學術界》 第1 卷第5 期,1943 年12 月,第39-49 頁。伯希和擔任主編后,從第25 卷(1927-1928 年)開始取消了“評論簡報”欄目,并將書評文章歸于“書目”欄目中,并于1925 年第24 卷開始創立新欄目“收到書籍”,代替之前的“新到書籍”欄目。伯希和逐漸將部分書評歸于此欄目中,第27-29卷“收到書籍”欄目長達上百頁。戴聞達接任后將書評重新歸至“書目”欄目中,該欄目恢復介紹新書基本信息的功能。“訃告”欄目自創刊就存在的欄目,主要刊發已故漢學家的生平,總結其漢學成就,列舉其研究著作,對學術史研究頗有幫助。期刊主編是主要撰稿人,可以看出期刊對前人研究的重視,石田干之助對“訃告”欄目評論:“又本雜志特色之一,在斯學底名家逝世之際,撰載附有詳細著述目錄的傳記,為編近代中國學史的所不容或缺的參考資料”。②[日]石田干之助撰,唐敬杲譯《歐美關于中國學的諸雜志》,第41 頁。
互動類欄目主要為讀者與編輯、作家與編輯、作家與作家之間提供一個溝通的平臺,凸顯期刊“交流”的特色,包括“按語與征詢”欄目和“通信”欄目。“按語與征詢”欄目共刊載了105 則信息,內容主要為讀者的來稿、回答讀者的問題、或轉載一些報刊文章的節選,篇幅較短,內容細碎化,并無標題和主旨,多數信息不到一頁。考狄與施古德時期,該欄目是固定欄目,施古德去世后,該欄目迅速減少,僅在1913年(14 卷)、1914 年(15 卷)和1920 年(20 卷)短暫出現過。“通信”欄目截止1944 年共刊載了56 封信件,作者多為漢學研究人員,作者通過該欄目與其他學者交流溝通,發表個人觀點,進行學術討論。
《通報》 的資訊類欄目包括“紀事”欄目和“雜錄”欄目,欄目信息碎片化,所涉及的范圍相當廣泛,包括國際學術會議的內容報道、報刊或官方文件的節選、政治談判、政治人物的相關報道、一些探險家的報道。“紀事”欄目在1890-1930 年期間基本為固定欄目,1931 年伯希和取消了該欄目。“雜錄”欄目屬于期刊草創時期,該欄目反映出法國和荷蘭在遠東的國際形勢。1904 年沙畹繼任主編后將國際學術會議報道、歐洲探險家報道歸于“紀事”欄目中,“雜錄”欄目取消。伯希和任主編時于1924 年短暫恢復了該欄目,此后該欄目再未出現。
綜上所述,《通報》 通過欄目將文章分為了專題文章、交流互動信息和新聞資訊。截止1944 年,期刊在54 年的發展過程中,因主編旨趣的不同對欄目有所調整,因《通報》 的學術特性故取消了“按語與咨詢”欄目,取消了欄目特征不明顯的“雜錄”欄目,突出“學術論文”、“雜識”欄目的不同文章特色,合并“評論簡報”與“書評”欄目,欄目不斷精簡,其形式內容不斷規范豐富。
二、20 世紀上半葉《通報》 的基本特征
在歷任主編的努力下,《通報》 成為20 世紀上半葉最重要的漢學期刊之一,就期刊的基本情況作簡單說明:
1.期刊作者分布
期刊的作者群體從國籍角度考察,可考者共計190 名,法國作者共89 人,約占47%;德國共32 人,約占17%;英國15 人,約占7%;荷蘭13 人,約占7%;美國共12 人,約占6%;其余俄國7 人、比利時4 人、匈牙利3 人、意大利3 人、瑞士2 人、中國4 人、日本2 人、芬蘭、瑞典、奧地利、西班牙各1 人。國籍占比基本與發表了3篇文章以上活躍撰稿人國籍的占比基本一致,法國作者占了絕對優勢,其次是德國作者,荷蘭籍作者無論在作者群體還是活躍撰稿人中都不占優勢,可以證實《通報》 是法國漢學的代表刊物。從職業身份角度考察,《通報》 作者群體中職業可考者共185人,學者共121 名,約占65%,是該刊的主要撰稿人群體;外交官23 人,約占12%;傳教士15 人,約占8%。此外教師、軍官、探險家、譯員、記者、醫生等多種職業也占據一定地位。作者群體與活躍撰稿人的統計數據保持一致,專業研究人員占據了絕對優勢,顯示出20 世紀前半期法國漢學研究趨向專業化的特征。
2.期刊文章分類
以1953 年《通報》 出版的《題材的補充索引》(Index Complémentaire par Matière)為主要依據,《通報》 刊載所有文章①文章包括《通報》 專題類、互動類、資訊類欄目的所刊文章。的研究領域按照數量排列,條目順序依次為:文獻與文學(653 篇)、歷史(431 篇)、宗教(372 篇)、藝術(290 篇)、科技(257篇)、地理(205 篇)、游記出使(204 篇)、風俗(118 篇)、書目(103 篇)、貿易(80 篇)、教育(77 篇)、人類學(69 篇)、交流(37 篇)、政府(37 篇)、人口(28篇)和法律(21 篇)②因法國漢學各領域多有交叉和重疊,經常一篇文章可以同屬于不同的類別,例如伯希和于1929 年在《通報》 第26 卷上發表的《關于中亞研究的九個注釋》(Neuf Notes sur des questions d’ Asie Centrale)就涉及歷史、文獻學、地理等多個研究領域,故統計數據時會出現一篇論文涉及兩個或更多的研究領域的情況,研究領域占比總數大于刊載文章的總數量。。進一步分析,《通報》 中專題類欄目的文章數目遠高于資訊類和互動類欄目的文章數目,專題類欄目是《通報》 的核心欄目。專題欄目所收文章主要分為論文和書評,專題類中與中國相關的文章數量依次為:文獻與文學(595 篇,專文225 篇,書評370 篇)、歷史(377 篇,專文182 篇,書評195 篇)、宗教(329 篇,專文132 篇,書評197 篇)、藝術(258 篇,專文66 篇,書評192 篇)、科技(181 篇,專文109 篇,書評72 篇)、地理(162 篇,專文95 篇,書評67 篇)、游記出使(125篇,專文50 篇,書評75 篇)、風俗(90 篇,專文35 篇,書評55 篇)、書目(86 篇,專文23 篇,書評63 篇)、貿易(63 篇,專文34 篇,書評29 篇)、人類學(57 篇,專文18 篇,書評39 篇)、教育(29 篇,專文19 篇,書評10 篇)、政府(25 篇,專文9篇,書評16 篇)、法律(18 篇,專文4 篇,書評14 篇)、人口(18 篇,專文8 篇,書評10 篇)、交流(13 篇,專文5 篇,書評8 篇)。《通報》 與考狄的《中國書目》(Bibliotheca Sinica,dictionnqire Bibliogrqphiaue des Ouvrages Relatif à l’ Empire Chinois)重合度高度重合,除了教育與交流條目外,《補充索引》 的其余條目皆可納入《中國書目》 的總類別中,這些條目下的文章基本涵蓋了《通報》 與漢學研究的全部內容,符合其漢學期刊的定位。
3.漢學學術期刊的確立
《通報》 創刊封面副標題為“關于東亞(中國、日本、朝鮮、印度支那、中亞和馬來西亞)的歷史、語言、地理、人種志的研究”,主編聲明中對期刊的定位有明確的說明:“填補遠東民族研究的空白”。③Henri Cordier,Gustave Schlegel,‘Avertissement des Directeurs’, T’oung Pao,Vol.1,No.1,1890,pp.I-IV.研究領域方面將中文文獻中的中亞問題研究列在首位,考狄特別針對中國與中亞、東南亞之間的關系研究指出漢學家需要學習波利尼西亞和閃語族語言,強調了漢學家和東方學家的跨學科合作,這也突出了《通報》 刊名中“交流”的概念。考狄與施古德時期的《通報》 并未將中國史研究放在首位,期刊關注遠東地區各領域的研究,研究范圍以中國為中心,輻射日本、韓國、印度、東南亞地區,內容繁雜,期刊的學術定位尚不明晰。1904 年沙畹接任《通報》 主編后,1904 年2 月22 日寫給考狄的信中寫道:“我相信,有了《法蘭西遠東學院學報》 和《通報》,法國漢學在科學界將占有一席之地。我會盡我所能讓你(考狄)不會后悔讓我參與主編工作。”①Henri Cordier,‘Edouard Chavannes’, T’oung Pao,Série II,Vol.18,No.1/2,1917,pp.114-147.由此可知,沙畹期望《通報》 專門服務于漢學研究。1906 年布里爾出版公司經理、《通報》 創始人之一思道普拉爾去世后,沙畹將期刊封面副標題改為“關于東亞的歷史、語言、地理和人種志的資料”,縮小了期刊的研究范圍。1920 年伯希和接任主編于1931 年再次修改《通報》 封面副標題,改為“通報或者東亞的歷史、語言、地理、人種志和藝術資料”,研究地區不變,研究領域擴展到藝術史研究。
1890 年至1945 年期刊“學術論文”欄目刊發論文共551 篇,與中國相關的論文共405 篇,其中第一卷(1890 年-1899 年)共收錄論文102 篇,與中國相關的論文67 篇,占總數的比例為65.7%;1900 年到1944 年共收錄文章449 篇,與中國相關的論文為338 篇,占總數的比例為75.3%。20 世紀開始《通報》 多個領域中漢學研究文章和書評數量明顯增加,條目增加比率依次為:文獻與文學8.7%、歷史5.1%、藝術16.1%、科技14.7%、地理25.3%、游記出使9%,證明了《通報》 對漢學各領域都有涉獵,每個領域的研究程度各不相同,研究領域逐步細化。
綜上所述,數據清晰地表明《通報》 對漢學研究的關注逐年增加,研究關注點逐漸集中的特點,由此可以證明沙畹繼任《通報》 主編后,調整了創刊初期定位于遠東地區的研究范圍,是期刊定位的轉變對文章刊布影響的直接反映,這個時間點的出現也證明了法國本土漢學的崛起,法國漢學研究進入了新的階段。
三、法國漢學在20 世紀上半葉的進步
通過上文可知,《通報》 作為漢學研究的平臺,與歐洲漢學發展緊密相關,期刊如實反映出法國漢學較之19 世紀更具有科學性,研究領域向縱深發展。20 世紀上半葉的法國漢學的進步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漢學機構與漢學期刊的創立
20 世紀上半葉,法國先后設立了多處漢學教學與研究機構,例如巴黎大學漢學研究所、波爾多大學和里昂大學的漢學講座、巴黎盧浮宮博物館的遠東藝術史講座、法國國家教育部下設“東方語言和文明”部門、法蘭西遠東學院的成立。漢學機構的建立有助于專業漢學研究人員的培養。期刊方面,19 世紀法國乃至歐洲的學術期刊多以遠東地區為研究對象,中國只是亞洲研究的一部分,19 世紀末至20 世紀初《通報》 等專業漢學期刊的創立證明了法國漢學家從遠東研究過渡到漢學研究,研究范圍逐漸專精,《新中國評論》 的主編庫壽齡(Samuel Couling,1859-1922)在《新中國評論》 的編輯聲明中就指出了《通報》 等法國專業刊物對法國漢學發展的重要,稱法國的漢學刊物“共同維持了法國在這門科學中的領導地位”,①王國強《視野與評價:19 世紀至20 世紀初的英國漢學——以〈中國評論〉 為討論中心》,章開沅、嚴昌洪主編《近代史學刊》,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141-154 頁。《通報》 等一系列專門漢學期刊的出現正是法國漢學飛速發展的重要條件。
2.不斷完善的研究方法
19 世紀時期,法國漢學家都從未來過中國,缺乏田野考察,法國漢學研究仍局限于翻譯注釋,缺乏原創性,研究深度不及德俄兩國水平。20 世紀初,法蘭西遠東學院為法國漢學家提供了近距離接觸中國文化的機會,漢學家有機會在中國地區進行實地考察,20 世紀的法國新一代漢學家在繼承了19 世紀法國漢學家開創的文獻研究法的同時,利用中國考古發現、碑銘、題記等大量史料綜合分析研究中國。沙畹、伯希和就是20 世紀前期法國漢學家的代表,沙畹“從法國學者那里,他繼承了一種精確地文獻學研究的頭腦和方法,及法國圖書館科學的可貴遺產;從英美漢學家那里,他了解到第一手田野考察經驗和當代漢語知識的重要性”。②韓大偉《傳統與尋真——西方古典漢學史回顧》,《世界漢學》 2005 年第3 期,第6-14 頁。沙畹重視使用考古材料,開創了法國碑銘學研究,他在《通報》 上發表的《蒙古時期(元代)的漢字碑銘和令旨》③沙畹共撰寫了三篇蒙古時期碑銘論文,分別是:‘Inscriptions et pièces de chancellerie chinoises de l'époque mongole’, T’oung Pao,Série II,Vol.5,No.4,1904,pp.357-447;‘Inscriptions et pièces de chancellerie chinoises de l’époque mongole:Deuxième partie’, T’oung Pao,Série II,Vol.6,No.1(1905),pp.1-42;‘Inscriptions et pièces de Chancellerie chinoises de l’époque mongole’,T’oung Pao,Série II,Vol.9,No.3,1908,pp.297-428.系列論文使用文獻考據學的研究方法翻譯考釋了云南大理的崇圣寺(即三塔寺)中的漢字碑文,指出了各個版本的不同之處,分析元朝時期漢語作為官方語言的語用特征,并將元代的漢文碑文進行分類。沙畹的碑銘學研究為法國之后的敦煌學研究、西域史學研究、蒙古學研究奠定了基礎。伯希和亦贊同碑銘學等考古資料的使用,他為羅振玉先生的《魏書宗室傳注》 撰寫的書評中強調佛教遺跡的題記的重要性:“佛教石窟題記是一個尚未被使用且不應被忽視的信息來源”。④Paul Pelliot,‘Reviewed work:Wei chou tsong che tchonan tchou(“Commentaire sur les biographies des agnats impériaux dans l’Histoire des Wei”)by Lo Tchen-yu’, T’oung Pao,Série II,Vol.24,No.1,1927,pp.79-86.
《通報》 的研究還引進了西方近代發展起來的語言學、語音學、人類學、社會學等跨學科研究方法。主編沙畹積極接受西方現代科學的研究方法,他認為:“社會學無疑是漢學學者目前最感興趣進行研究的學科之一,因為在面對中國文化時,漢學家可以借助社會學的科學手段解決所面臨的問題,運用社會學理論發現無數研究主題”。⑤Edouard Chavannes,‘Reviewed Work:Les rites de passage by Arnold van Gennep’, T’oung Pao,Série II,Vol.10,No.2,1909,pp.232-235.伯希和在《通報》 發表了多篇西域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的論文,他討論蒙語與漢語、突厥語等多語言之間的對音現象,梳理各語言間的銜接情況,進而考證各民族間的交往歷史。伯希和吸收了中國乾嘉考證的學術傳統,論文附有大量注釋,對比各版本間的不同之處,尋找各版本的出處,伯希和的注釋為之后的研究學者提供了便利,更為之后的歷史語言研究、蒙古學研究提供了合理的研究方法。
20 世紀上半葉法國乃至歐洲學界注重與中國學界的交流,以沙畹、伯希和為代表的法國漢學家與中國學者建立了個人聯系,通過《通報》 為法國漢學界提供中國最新的研究成果。《通報》“書目”和“評論簡報”欄目多次刊載中國學者的專著或中國歷史期刊的論文,如沙畹于1911 年在“評論簡報”欄目中為羅振玉先生、王國維先生主編的《國學叢刊》 撰寫書評,簡要介紹了期刊所刊載相關敦煌遺書的研究。沙畹向西方讀者詳細介紹了羅振玉先生和王國維先生的專著。①Ed.Chavannes,‘Reviewed work:Kouo hio ts’ong k’an Recueil de travaux imprimés se rapportant à l’érudition nationale by Lo Tchen-yu,Wang Kouo-wei’, T’oung Pao,Série II,Vol.12,No.5,1911,pp.743-746.伯希和擔任主編后,持續關注中國學界,他的書評可以分為兩類:首先,伯希和撰寫長評評述中國傳統史學家的研究成果。伯氏分別為羅振玉先生的《古鏡圖錄》 和《魏書宗室傳注》 撰寫書評,詳細介紹羅振玉先生的研究成果,并稱贊“羅振玉先生的新作是朝代史考證的重要貢獻,文章信息的準確性和文章的研究廣度值得毫無保留地贊賞”。②Paul Pelliot.,‘Reviewed work:Wei chou tsong che tchonan tchou(“Commentaire sur les biographies des agnats impériaux dans l’Histoire des Wei”)by Lo Tchen-yu’,pp.79-86.1928 年,伯希和在《通報》上發表《王國維作品集》,文章長達71 頁,幾乎涵蓋了王國維先生的所有作品,并評價王國維的作品“是如此重要和豐富,我認為很有必要將他的作品詳細列舉出來,我可以借此機會討論其中的一些問題。”③Paul Pelliot,‘L’édition collective des ?uvres de Wang Kouo-wei’, T’oung Pao,Série II,Vol.26,No.2/3,1928,pp.113-182.其次,伯希和對中國新派學者的關注。這類學者留學歐美等國,學習了西方的史學研究方法并應用到中國歷史研究中,伯希和評論胡適先生的《先秦名學史》 時指出“這是迄今為止中國學者用歐洲語言做出的最好的科學成果。”④Paul Pelliot,‘Reviewed work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 by Hu Shih’,T’oung Pao,Série II,Vol.22,No.4,1923,pp.309-315.
3.研究領域的細化
《通報》 作為法國漢學界的媒介,期刊表現出一種明顯的學術自覺性——期刊在書評中開始評論漢學研究的現狀并思考漢學的發展方向。沙畹在多篇書評中表示漢學研究應向多學科領域發展,進行跨學科研究。高本漢(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在書評中強調語言學對于漢學研究的重要性:“在之前的漢學研究中,語言學一直被被忽視,直到現今從更廣泛的漢學角度進行考慮,正如考古研究、歷史研究、宗教研究一樣,語言學研究逐步受到重視”。⑤Bernard Karlgren,‘Reviewed work:La langue chinoise parlée,Grammaire du Kwan-hwa septentrional by Maurice Courant’, T’oung Pao,Série II,Vol.15,No.2,1914,pp.283-285.文學研究方面,伯希和支持中國詩歌的譯介與研究:“中國詩歌已成為潮流,但是人們對于無法翻譯出玉石的神韻時會感到遺憾,無論如何中國詩歌已經激發了公眾的好奇,那么遠東學者就應該滿足其需求”。①Paul Pelliot,‘Reviewed work:Fir-Flower Tablets,Poems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Florence Ayscough,Amy Lowell’, T’oung Pao,Série II,Vol.21,No.2/3,1922,pp.232-242.宗教研究方面,沙畹希望深入開展道教研究,他為戴遂良《道教》(第一卷)撰寫的書評中提出不應該將研究重點放在《道德經》 的翻譯問題上,應從宏觀角度研究道教思想,“道教研究已經成為漢學家需要解決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②Edouard Chavannes,‘Reviewed work:Tao?sme,tome I,Bibliographie générale by L.Wieger’,T’oung Pao,Série II,Vol.12,No.5,1911,pp.749-753.1953 年《通報》 出版的《補充索引》 按照漢學研究領域通報目錄分為13 類別,“文獻”“宗教”“科技”“藝術”等條目下設子條目,法國漢學在20 世紀上半葉呈現出各學科細化且相互隔絕的特點。
結論
如前文所述,20 世紀上半葉的法國漢學研究范圍正如《通報》 所顯示的一樣,研究涉及了漢學領域各個方面,研究方法有了全新發展。沙畹、伯希和為代表的法國漢學家打破了19 世紀以雷慕沙、儒蓮為代表的“法國漢學學派時期”③韓大偉《傳統與尋真——西方古典漢學史回顧》,第7 頁。的書齋式研究方法,20 世紀上半葉的法國成立了多個漢學機構,并培養了多位法國專業漢學家,他們善于利用漢文典籍,重視實地考察工作,加強與中國學界的聯系,開創了法國碑銘學研究、敦煌學研究、西域史學研究、蒙古學研究、藏學研究、宗教研究等諸多研究領域,由此法國漢學研究進入了鼎盛時期并對20 世紀后期的國際漢學研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