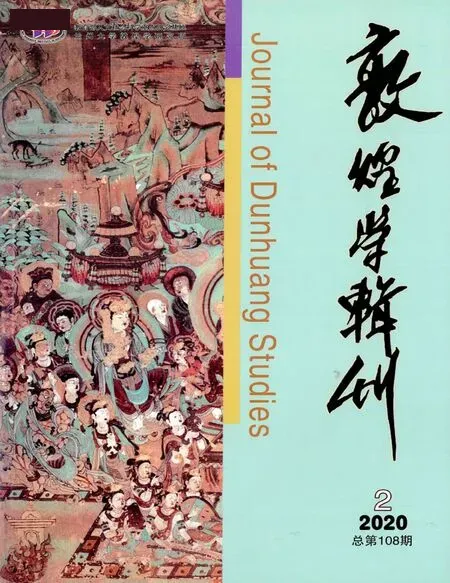宿白先生與須彌山石窟調(diào)查
羅 豐 李志榮
(1.西北大學 文化遺產(chǎn)學院,陜西 西安 71000;2.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寧夏 銀川 750000;3.浙江大學 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00)
一
第一本須彌山石窟的報告書要出版了,在我們終于松了一口氣的時候,自然而然的又想起了宿白先生。
須彌山報告的整理出版,與其說是宿白先生長久的心愿,還不如說是宿白先生一個長長的心病,現(xiàn)在可以算得上是還了一個許下先生很久的愿,雖然先生已無法目睹。宿白先生從1984 年起至2000 年曾四次前往須彌山石窟考察,其中時間最長的1986、1987兩個年度,每年在須彌山的時間都長達一月之久,須彌山也是先生石窟考古生涯中浸注心血最多的一個石窟之一。
2001 年的春天,記得是在一個灰蒙蒙的上午,筆者之一羅豐去北京大學朗潤園宿府拜訪宿白先生。那時我剛擔任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不久,宿先生雖對我能否勝任人事關(guān)系復雜的單位工作仍表示擔憂,但還是對寧夏在考古方面的幾項工作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導,其中也說到了須彌山石窟報告的整理編寫。我順口向宿先生表達了想法,北京大學考古系既然曾經(jīng)調(diào)查過須彌山圓光寺,能否重新啟動編寫工作。宿先生見我隨口說來,并非成熟考慮,就談到他所擔心的事:北大原來的須彌山圓光寺調(diào)查,是受寧夏文管會的委托而開展的,現(xiàn)在由考古所接手,有無障礙?他知道,過去兩個單位之間并不和諧。我馬上表態(tài),寧夏文管會已經(jīng)撤銷,由我們接手并無不妥,請先生放心,寧夏方面我會協(xié)調(diào)一致。“如果這樣,你可去找馬世長商量,先把圖找來,再核對原來的調(diào)查記錄,然后再說報告編寫的事情。”并叮嚀說馬世長身體不好,事又多,你多催著點。隨后我找到拄著拐杖、拖著病身但情緒高漲的馬世長先生。聽我轉(zhuǎn)達宿先生的想法后,馬老師十分高興,說由你們接手當然好呀,這件事終于又可以啟動了!接著他委托陳悅新來具體操辦。陳悅新曾經(jīng)參加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須彌山調(diào)查(本報告說的第二次考古調(diào)查),在寧夏工作多年之后,當時剛?cè)氡贝箅S馬世長讀博士學位。
不久,消息傳來,結(jié)果令人失望,圖丟了。原來北大考古系幾次搬家,須彌山調(diào)查時繪制的大部分圖紙不知所蹤,同時遺失的還有一些文字記錄。馬世長聽說后,幾次對我說,遺失是不可能的,再找找。當然沒有下文。每當宿先生問我和馬世長商議的結(jié)果,我只能王顧左右而言他。有一次在北大勺園開會我向馬老師建議,要不要一起去向宿先生說明情況,馬老師滿臉為難地說:“還是由你說比較方便,宿先生也不好說你。”看來這個惡人只好由我來做了。聽說圖沒了,宿先生非常吃驚,又詳細詢問了尋找過程,說那以后須彌山的報告就成問題了。接著又說了很長的一段話,簡要大意是,石窟調(diào)查主要是調(diào)查者要仔細地看,一切觀察的結(jié)果都要落在圖上,圖紙是石窟報告整理的基礎,也是成果,調(diào)查記錄只是圖紙的補充和輔助。為了不使宿先生失望,我信心滿滿地向宿先生保證,會補繪缺圖,重新組織力量調(diào)查。宿先生搖搖頭,滿臉狐疑,失望和不信任掛在臉上:“那就試試看吧。”
從此以后的數(shù)年間,我們在國家文物局的支持下重啟調(diào)查,卻又累起累仆,困難迭起,進展緩慢。宿先生對重新調(diào)查每每用警惕的目光注視,幾番反復之后不被宿先生看好的調(diào)查活動幾成僵局,我也有些喪氣了。
調(diào)查工作陷入僵局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缺少石窟專業(yè)人員主持,二是石窟測量繪圖的結(jié)果大家都不滿意。時間拖了很久,所謂的石窟測量調(diào)查也時斷時續(xù)地進行著,仍沒有拿出一張大家滿意的測圖,人員卻換了好幾撥。2010 年情況終于出現(xiàn)了轉(zhuǎn)機,這一年原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曹錦炎先生受命組建浙江大學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一次會上偶遇談及有無機會合作,我借機向他講述須彌山調(diào)查的情況,曹所長稱他們正在嘗試利用數(shù)字化技術(shù)進行一些測量活動,倆人一拍即合,決定聯(lián)合調(diào)查須彌山石窟。曹所長并稱北京大學李志榮很快加盟浙江大學,可以請她來負責這一項目。
接著我在北京向宿先生匯報我們與浙江大學的合作意向,宿先生說由浙大方面李志榮負責須彌山調(diào)查是可以的,她雖然沒有做過石窟,但完全可以勝任,只要協(xié)調(diào)好與原有寧夏方面人員關(guān)系。得到宿先生的支持,我心里稍有些底,我們的須彌山調(diào)查測繪一向不被宿先生看好認可。2011 年年中剛調(diào)入浙大的李志榮和浙江大學數(shù)字化團隊很快來到須彌山石窟,在初步數(shù)字信息化采集工作之后,大家都覺得這樣的辦法雖然還在摸索之中,但無疑是可行的。在調(diào)查工作團隊的組建中,我們充分考慮了既往工作的沿續(xù)性,也邀請相關(guān)專家一起工作。來年五月,我再次向宿先生報告了準備情況及調(diào)查人員的構(gòu)成,宿先生表示,這樣看來工作可以開展了,并明確告訴我,須彌山石窟的調(diào)查工作就由李志榮主持吧,其他人有時間就去,調(diào)查就是要有人一直盯在現(xiàn)場,隨時解決出現(xiàn)的問題,并批評道你們以前那樣不行。
隨即我們兩家簽署須彌山石窟聯(lián)合調(diào)查協(xié)議,并請宿白先生擔任總顧問,宿先生欣然接受了我們的邀請,調(diào)查工作終于可以開始了。宿先生聽了彌山石窟初步考察的收獲,非常高興,隨即我們一起商定考古組織的基本架構(gòu)和設想。他看過在須彌山試驗數(shù)字化技術(shù)的成果,覺得能夠利用這一技術(shù)解決須彌山石窟測量問題,只簡單地說,“那就抓緊干吧!”
二
宿白先生關(guān)注須彌山石窟實際是他推動中國石窟寺考古調(diào)查的一個組成部分,他用相當多的時間來思考中國佛教考古的問題,尤其是石窟寺調(diào)查的具體方法,許多重要石窟的考古調(diào)查工作都是在先生的親自指導下進行的,也是他學術(shù)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環(huán)。
如果我們希望正確地評價宿白先生對中國石窟寺考古的貢獻,那么將其放在二十世紀中國石窟寺調(diào)查的長河中去認識的話,大約應該是一個不錯的角度。在宿白先生的學術(shù)生涯中,佛教考古是他研究的重點之一,除藏傳佛教考古外,他花費了很大的功夫來研究、推動中國石窟寺考古的調(diào)查、研究工作。在宿白先生進行的一系列開創(chuàng)性工作中,他的每一部著作幾乎都標志著佛教考古學科一個新的起點,我們都可以從中學習到許多東西,如提出問題的角度、解決難題的方法和可靠而不被注意的材料信息等等。他會輕而易舉地抓住問題的本質(zhì)進行討論,與長廣敏雄的論戰(zhàn)完全突顯了他的這種才能。幾十年后的今天,這些著作仍然是學術(shù)領(lǐng)域中的經(jīng)典著述,《中國石窟寺研究》 《藏傳佛教寺院考古》,甚至未正式刊行的著名的《敦煌七講》 都是這樣的著作。
云岡石窟是宿白先生研究石窟寺考古的開始,關(guān)注云岡石窟可以推及到解放以前的1947 年。那時,他在整理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的善本書籍過程中,意外地發(fā)現(xiàn)清代金石學家繆荃孫傳抄的《永樂大典》 天字韻《順天府》 條中引了元人《析津志》。《析津志》 中有一篇《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記》。繆荃孫所抄《金碑》 雖系近錄但卻是孤本,因為他所抄錄的這冊《永樂大典》 在庚子事變中已不知所蹤。后來宿先生依據(jù)這篇碑文所記的云岡十寺,來研究云岡石窟中寺院的歷史。他采用注釋的體例,謹慎地推測了其中五個寺院的位置。后來在與日本著名考古學家長廣敏雄的辯論中,詳盡地論述了這篇《金碑》 史料上的可靠性,以及一些刻銘、文獻在研究石窟寺考古時的重要性和使用原則,特別強調(diào)石窟附近的一些寺院建筑遺跡的延續(xù)和繼承性。
實際上宿白先生從1950 年參加雁北文物考察團到過云岡石窟后,多次前往云岡石窟進行調(diào)查,他的多篇有關(guān)云岡石窟的論文就是實地考古調(diào)查的心得。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著名的“云岡模式”這一石窟考古上的重要概念。宿白先生從魏道武帝占據(jù)平城以來的百年歷史事實出發(fā),指出云岡石窟實際上是北魏王朝集中各地優(yōu)秀人才、財富、技術(shù)的產(chǎn)物。云岡石窟的三個階段都與當時崇佛思想、南北交流、宗佛思潮密不可分。遷洛以后,云岡的大型石窟營造中輟,大批中小型洞窟盛行,是皇家勢力撤出后由留平、復來貴族充分利用平城舊有技藝的結(jié)果。它的式樣與洛陽地區(qū)石窟聯(lián)系甚密,雜染華風是必然。云岡石窟影響范圍之廣、延續(xù)時間之長,是其他任何石窟所不能比擬的。北魏領(lǐng)域內(nèi)的任何石窟建造都是參考了云岡石窟新興的營造模式或以此為典范。
敦煌莫高窟是宿白先生關(guān)注的另外一個重點。大約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開始,宿先生在敦煌文物研究所講述著名的敦煌學七講,學生們根據(jù)他的講課記錄,整理了《敦煌七講》。在這次系列講座中宿白先生主要從中國石窟寺研究的歷史出發(fā),系統(tǒng)地梳理了石窟寺考古研究中的若干問題。他的這些思考雖然大都見于后來發(fā)表的若干文章當中,但其中若干關(guān)于石窟寺考古具體調(diào)查方法和需要解決的問題,現(xiàn)在仍然值得我們領(lǐng)會思考。
中國境內(nèi)最早進行石窟寺考古調(diào)查的是外國探險家,斯坦因、勒柯克、伯希和等人在新疆、河西的調(diào)查報告書是學術(shù)界了解克孜爾、敦煌石窟的基礎。內(nèi)地佛教遺址考古調(diào)查最早在二十世紀初年,日本學者在這方面用功最多,尤其是抗日戰(zhàn)爭期間,日本軍隊占據(jù)華北地區(qū)后,他們對云岡、龍門、響堂山石窟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調(diào)查和詳盡的勘測,并且很快出版了考古報告。1936 年,長廣敏雄、水野清一等調(diào)查龍門石窟,1941年出版《河南洛陽龍門石窟之研究》;1936 年調(diào)查響堂山石窟,次年《河北磁縣河南武安響堂山石窟》 就出版。當然,長廣、水野用力最多的是云岡石窟,調(diào)查時間幾乎伴隨著整個抗日戰(zhàn)爭,報告的整理時間更長,從1952 年開始到1956 年出版《云岡石窟:西歷五世紀中國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調(diào)查報告》,共十六卷三十二冊。至于一些云岡石窟零星發(fā)掘品的整理,更是要晚至2006 年,才由岡村秀典整理出版(岡村秀典編《云岡石窟·遺物篇》,京都:朋友書店,2006 年)。這部考古報告是中國石窟寺報告中最重要的一部,也是宿白先生最重視的一部,多次向我們推薦這部報告。他曾指出這部書是石窟寺考古報告編寫的一個藍本;但同時也指出,長廣敏雄和水野清一在編寫過程中的一些分歧,他們的意見分別表現(xiàn)在各自主持的報告部分。報告的日文部分主要由長廣敏雄主持編寫,英文部分的主持人水野清一。水野邀請國立博物館的原田治郎進行翻譯。翻譯并未按日文一一對應,并請一位美國人Peter.C.Swann 擔任校對工作。所以水野花了大量時間向譯者逐一敘述云岡石窟,水野對云岡石窟的看法主要體現(xiàn)在英文部分。宿白先生提醒在閱讀英文部分時要注意這種差異。
宿先生對這些日本石窟報告的總體評價是:南北響堂山石窟報告因為時間太短,較為粗糙一些,龍門石窟相對從容要稍好一些,但問題很多。云岡石窟報告則更好,它可以看成是二十世紀上半葉日本學術(shù)界對我國石窟研究的一個總結(jié)。不過在宿先生眼中,日本人關(guān)于佛教考古著述中最高水平的著作,是京都大學的《居庸關(guān)》。居庸關(guān)的過街三塔除去許多雕刻造像外,過街塔洞還銘刻許多其他文字,所以當時京都大學集中許多各方面的專家共同研究。歷史方面有藤枝晃、日比野大夫,圖像方面有高田修,梵文、藏文方面有長尾雅人,八思巴文、西夏文方面有西田龍雄,回鶻文方面有江實,陀羅尼文方面有利惇氏、梶山雄一等。這些人都是當時不二之人選,因此報告的總體水平要超過《云岡石窟》。當然這是由于居庸關(guān)材料的特殊性決定的,一般的石窟調(diào)查,《云岡石窟》 仍具有重要的參考性,包括報告書的形式。
宿先生雖然覺得日本人石窟考古研究在推進中國石窟考古研究時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但他早在六十年代就指出其中的一些缺陷。例如他們的研究偏重于題材考證,無法了解題材的發(fā)展;一些現(xiàn)象只有一些不大肯定的推測,而無正確闡釋。即使對內(nèi)容的考察,也只能注意其表面現(xiàn)象,而無法重視其內(nèi)部關(guān)系。另外,一個致命的缺陷是掌握的材料不夠全面,像天梯山、麥積山、敦煌莫高窟這些重要的材料,他們都不了解,無法進行比較研究。雖然日本學者以網(wǎng)羅文獻著稱,宿先生卻覺得他們在參考文獻方面受到一些限制,像金代《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記》 這樣重要的文獻,在長廣敏雄看來有點兒來歷不明,從而不被重視。還有他們對于禪宗、密宗的理解有點兒片面。因為這些問題的研究都與道德傳統(tǒng)、生活習慣、習俗等有密切關(guān)聯(lián),而不能僅用自身的理解去研究,他們在這方面也有困難,無法深入。
石窟寺考古是宿白先生長期思考的歷史考古學問題之一,尤其是石窟寺的考古調(diào)查,這是石窟寺研究的基礎。早在六十年代,他在著名的《敦煌七講》 中專門用兩講的篇幅講解了他的思考和方法。
宿白先生認為:石窟寺考古首先要探討排年、分期和性質(zhì),然后才能進一步討論它的社會性質(zhì)。因此,注重窟室形制、布局、分組和形象各種題材,組合與造像特征的調(diào)查記錄是最重要的環(huán)節(jié)。考古學的基礎是層位學和類型學,石窟寺的考古學記錄,相當于考古學的層位學。石窟寺考古學的記錄,不是一般性的調(diào)查記錄,它所要達到的最高標準是在考古對象被破壞以后,可以根據(jù)調(diào)查記錄,進行復原工作。這一點,對于石窟遺跡來講,尤其重要,因為石窟的壽命不可能永久存在下去,它會一點一點的消失,最后全部損毀。阿富汗巴米揚石窟的被毀,完全突顯了詳盡考古調(diào)查工作的重要性。
正式的石窟考古學記錄,是石窟寺的科學檔案,共有六項工序,所有進行調(diào)查石窟工作的人員都應當掌握:
(一)測繪
完整的測繪圖應當有:連續(xù)平、立面圖,這便于我們了解被測窟在窟群中間的位置,也要注意窟外檐、棧道等遺跡平面圖,要求與連續(xù)平、立面圖相匹配,用不同高的線條表示高低。還應當注意已經(jīng)消失的跡象,如幢幡架、燃燈架、欄桿等,當然造像等復雜遺跡更要重視,應該用方格基線剖面圖,縱、橫剖面都要有,最好能延至窟外,可以看出其與上下窟的關(guān)系,還要能表示出改建痕跡。各壁的立面和各壁畫面的實測圖,復雜的壁畫要有細部原大白描圖、窟頂圖。窟前木構(gòu)圖,要分清原裝和后裝,注重材、栔、分口、榫卯等古建筑的規(guī)格和方法。塑像石測圖應包括,正視、左右側(cè)視、后視、俯視圖等。衣紋、佛面、花紋及后塑部分都要有細部圖。窟前遺址圖。石窟解剖、軸線投影圖,雖然原理簡單,但實際操作起來麻煩,最好能有。
(二)尺寸登記表
這項工作應與測繪同時進行,與圖相輔而行,彼此不可偏廢。尤其要注意實測圖中不亦表現(xiàn)出的尺寸。
(三)照像草圖和登記
照像的部位要畫出草圖,照片、草圖都要記錄。
(四)墨拓
墨拓最好由記錄者制作。它的對象是石窟中的各種石刻、木刻、磚等。因墨拓的延伸關(guān)系,注重其神。
(五)文字、卡片記錄
以上述各種圖為單位制作單位大卡片。卡片描述必須客觀準確,不作任何考證,必要時可以作附注。
(六)簡單小結(jié)卡片
各種圖表、卡片記錄完之后,要由負責人作簡單小結(jié)卡片,檢查各種記錄、圖表之間相互交換關(guān)系,內(nèi)容必須統(tǒng)一,不能有矛盾。小結(jié)時要有圖表總目錄,圖表要進行統(tǒng)一編號。
宿白先生指出在整個石窟考古中最為重要的是造像的測量,而造像的測量不僅要注意造像的現(xiàn)狀,還要從造像制度方面考慮問題。造像的經(jīng)典都來自一定的佛教規(guī)制圖樣,幾次大的佛教傳入,主要是根據(jù)圖樣。雖然,我們現(xiàn)在在《大藏經(jīng)》 中找不到一本造像經(jīng)典,但歷代工匠肯定是依照經(jīng)典尺寸來造像的。一些佛經(jīng)如《阿婆縛抄》 《覺禪抄》 《別尊雜記》 和《畫像要集》 等密宗經(jīng)典都提到過造像的尺寸、顏色、布局。他特別到注意一部名為《造像度量經(jīng)》 的藏文經(jīng)。這部關(guān)于造像的經(jīng)典最早由元人幢吉祥從梵文譯成藏文,大約在明代中期出現(xiàn)漢譯本,現(xiàn)在的漢譯本是由精通藏文的蒙古族人工布查布在清乾隆年間譯出。《造像度量經(jīng)》 中有一些圖樣,并且根據(jù)經(jīng)文對佛的坐立、佛面、菩薩、佛母、天王進行比例分析。例如頭與身的比例,面部各部位的比例,坐與立的比例,佛與菩薩的比例等。雖然這些比例關(guān)系并不一定完全符合諸多石窟造像尺寸,但對于我們理解造像比例關(guān)系規(guī)律、為我們研究藏傳佛教的形象、儀式提供幫助,也是通過唐密圖樣的橋梁。
宿白先生關(guān)于石窟考古調(diào)查的思想是全面的,方法具體而詳盡,即使過去五十多年,由于技術(shù)的進步,一些過于艱困的測量已經(jīng)變得相對簡單。但是宿白先生所要求的具體操作方法、關(guān)注問題仍具有現(xiàn)實指導意義,或者說我們?nèi)匀粵]有達到宿先生所要求的水準。
在宿白先生的晚年,他在不同的場合,依然強調(diào)這些原則,并加以發(fā)揮。當一些技術(shù)嘗試性地運用到石窟調(diào)查之中,宿白先生總是給予熱情的鼓勵和支持。他提醒調(diào)查時要注重人員的結(jié)構(gòu),強調(diào)考古學者如何主導調(diào)查方向,而不至于成為技術(shù)的附庸。
三
大約是在2011 年10 月份,初查須彌山回到杭州不久,李志榮接到宿先生電話,希望到一趟北京,一是要聽9 月在須彌山初查數(shù)字化三維建模技術(shù)在須彌山石窟第45 窟前壁西龕進行數(shù)字化測量實驗的結(jié)果,二是要求到北大考古系資料室借出日本人云岡報告,好好念一遍。
2012 年4 月須彌山石窟第三次考古調(diào)查正式開始。這次工作與此前石窟寺考古的最大區(qū)別,就是計算機數(shù)字化測量記錄技術(shù)的引進和應用。因此,這次工作可以定義為是一次在數(shù)字化技術(shù)介入條件之下的石窟寺考古實踐,甚至可以說是全新的嘗試。須彌山石窟考古工作從團隊組織到具體環(huán)節(jié),都是在宿白先生學術(shù)思想之下對石窟寺考古方法論在新條件下的學術(shù)實踐和方法論探索。
團隊的組織。地面遺跡的田野調(diào)查,除不發(fā)掘之外,工作與田野考古無異,同樣需要對遺跡的全面細致的觀察,從整體到局部的測量,對觀察和測量遺跡的全面的文字記錄,以及對觀察和測量并文字記錄的遺跡的全面的攝影記錄,做到盡可能全面地把遺跡信息多方位地記錄下來、呈現(xiàn)出來。石窟寺遺址除歷史地理諸環(huán)境因素外,還有窟外遺跡、窟前遺跡和窟內(nèi)遺跡,極為復雜,依照宿先生的要求和徐先生的標準,需有考古工作者率專業(yè)的考古測量工作者、考古攝影師,數(shù)字化工程師,無分別地全面觀察和記錄。須彌山石窟考古調(diào)查團隊,就是由寧夏考古所和浙江大學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聯(lián)合組成的一個由考古工作者、攝影師、測量工作者和數(shù)字化工作者組成的團隊。后者是數(shù)字化技術(shù)介入在團隊組織中的反映。
整理石窟寺研究史。宿先生說,梳理研究史,對考古工作而言,最重要的是為了更好地了解遺跡得以成為今天現(xiàn)狀的來龍去脈。從某種程度上說,梳理歷史文獻的也是這個道理。因此,一切與遺跡面貌有關(guān)的行為,不論是學術(shù)調(diào)查、研究還是加諸考古遺址上的其他行為——對石窟寺而言,當然還包括石窟寺的保護整修等等——都應當納入研究史。本次工作,除梳理方志文獻外,梳理了自須彌山石窟被發(fā)現(xiàn)以來歷次的著錄和調(diào)查,特別專門梳理了1983 年代以來大規(guī)模的須彌山整修工程。這次整修工程不僅改變了須彌山的整體面貌,順著修整工程的“功業(yè)”逆流而上逐項“剔除”,正好可以復原整修工程前須彌山石窟的面貌。而兩次大規(guī)模的調(diào)查,對須彌山石窟群進行了科學編號和分區(qū),公布的包括題記和圖版在內(nèi)的資料,記錄保存了上世紀80 年代中期洞窟內(nèi)外遺跡的實況,對認識今天的遺跡面貌、兩次調(diào)查的學術(shù)貢獻和整修工程中搶救保護遺跡的時代貢獻,意義非凡。研究史的梳理使本次工作建立在扎實的基礎之上,并保持了與前人工作的延續(xù)性。中國現(xiàn)存的石窟寺大都不僅經(jīng)過幾代學者若干次的調(diào)查研究,而且也幾乎都經(jīng)過1949 年以來若干次修繕和加固保護工程,宿先生強調(diào)立足遺跡梳理研究史,當不僅僅適用于須彌山石窟。(圖1)

圖1 宿白先生1984 年考察須彌山石窟北周51 窟①圖1、圖2 照片由雷潤澤先生提供,謹表謝意。
整體布網(wǎng)測繪。現(xiàn)存的中國石窟寺,和須彌山石窟一樣,均為自然歷史環(huán)境獨特、區(qū)劃復雜、洞窟眾多的石窟群,如何進行可持續(xù)的考古工作,到目前為止尚是一個令從事石窟寺考古的機構(gòu)感到困難的問題。幸而目前測量技術(shù)進步使這個問題的解決成為可能。用在大遺址考古中普遍使用的帶RTK 的全站儀首先對石窟群連同其選址環(huán)境進行布網(wǎng)測繪,不論后續(xù)具體實施的詳細考古調(diào)查從石窟群的哪個區(qū)哪個窟開始,都會歸宗于窟群整體。這是現(xiàn)代測量技術(shù)給當前石窟寺考古工作帶來的便利。須彌山石窟工作中,我們首先安排了整體布網(wǎng)測量,之后選擇從須彌山石窟群的核心區(qū)段圓光寺區(qū)開始。目前須彌山子孫宮區(qū)全部和相國寺區(qū)第51 窟及其附窟的田野工作都已經(jīng)全部結(jié)束,局部的測量和整體布網(wǎng)測量之間實現(xiàn)了宏觀和微觀記錄的統(tǒng)一。(圖2)

圖2 宿白先生在相國寺區(qū)洞窟石階
石窟寺的數(shù)字化測量及測圖。如前所述,石窟寺記錄中首要而繁難的就是具體石窟寺洞窟內(nèi)外的測量。數(shù)字化技術(shù)引入之前的傳統(tǒng)測量,是借助工程測量三視圖的方法,設立測量基點、基線,建立坐標系,然后借助各種傳統(tǒng)的測量工具,測量遺跡在坐標中的位置,形成石窟寺的平面、立面、剖面圖,理論上通過三視圖,來復原石窟寺洞窟內(nèi)外遺跡的三維空間和遺跡全貌。但由于石窟寺遺跡的復雜性,要做到精準測量極不容易,做到完全復原只是理想而已。數(shù)字化技術(shù)引進石窟寺考古中解決洞窟內(nèi)外的測量問題,其過程與傳統(tǒng)測量正好相反。2012 年須彌山一期具體的做法是,用多圖像三維建模的方法,首先獲得洞窟內(nèi)外遺跡的三維空間模型,然后再從這個已經(jīng)獲得的三維模型中,根據(jù)考古記錄呈現(xiàn)遺跡的需要,獲得各種數(shù)字化的測量圖——正射影像圖。這樣形成的正射影像圖的每個點都是數(shù)字測量的結(jié)果,可以用作傳統(tǒng)意義上測圖的底圖,清繪之后就成為可反映洞窟遺跡及遺跡關(guān)系的線圖。令人感動的是,宿先生幾乎是立刻就理解這種新技術(shù)能給石窟寺考古帶來怎樣的促進,只是不斷督促說,線圖繪制,那一定得做考古的人盯著,數(shù)字化工程師也好,清繪的人也好,不了解遺跡和遺跡關(guān)系,或理解不深,是畫不出來的。我們謹遵教誨不敢放松,堅持與數(shù)字化測量同時工作,在現(xiàn)場完成石窟寺考古觀察和記錄,并不斷地給數(shù)字化作業(yè)工程師講解遺跡,讓他們了解他們工作的對象以及目標。
然而以數(shù)字化測圖為底清繪而成傳統(tǒng)線圖,并沒有預想的容易。數(shù)字化記錄的是遺跡包括質(zhì)感、色彩、風化、殘損等的全面信息,正射影像圖因此就成了把遺跡和遺跡關(guān)系呈現(xiàn)得十分豐富繁復的底圖,遠超傳統(tǒng)測量所得,給清繪帶來了取舍難題。通過從數(shù)字測圖到清繪成線圖的全過程,事實上可見兩種測圖表達內(nèi)容的差異,前者可以看作對遺跡全貌的客觀記錄,而線圖——其功能已經(jīng)不再是用以復原洞窟的空間信息——表達的一定意義上是考古工作者對遺跡的觀察認識。數(shù)字化的底圖使表現(xiàn)更多遺跡信息的更加細膩的線圖成為可能。也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進一步認識了數(shù)字化記錄的優(yōu)越性。最后我們堅持兩種測圖同時發(fā)表。
石窟寺遺跡的文字記錄。無需多言,和任何考古工作一樣,考古記錄需在現(xiàn)場面對遺址遺跡不斷地深入觀察的基礎上進行。關(guān)于這一點,宿先生總是在說,使勁看,看明白,看不明白也就不可能記錄明白。而石窟寺遺跡包括選址營鑿的工程遺跡,如果有窟前寺院營建的話,還有地面寺院的營建遺跡,進入洞窟,則有洞窟形制、布局遺跡,還有造像遺跡,還包括在開鑿洞窟過程中形成的工藝遺跡,還有石窟寺存續(xù)的漫長時間里不斷的重裝遺跡,如同傳統(tǒng)考古地層學所示的不同文化層疊壓一樣,都需要不予人為輕重分別地全面記錄。對于晚期遺跡,宿先生說,那當然要記錄了!須彌山石窟的記錄,雖不敢說確實看明白了,但卻謹遵教誨,使勁看了,認真地記錄了窟外窟內(nèi)的遺跡、開鑿的遺跡和晚期重裝的遺跡,看見了洞窟營鑿的匠心,看到了手工時代的雕鑿技藝對遺跡形成的影響,看見了遺跡細部中充滿的生動的變化,最重要的是,常被一筆而過的“晚期重裝”,對于像須彌山石窟這樣在晚期有過系統(tǒng)性重裝的石窟寺,被詳盡記錄。正是透過晚期重裝遺跡,開鑿時期洞窟遺跡才被“暴露”,特別是造像遺跡。事實上,不論開鑿還是重裝,都是人們?yōu)閷崿F(xiàn)自己的信仰理想付出努力勞作傾盡心力的結(jié)果,不論早晚都不能稍有忽視。而正是須彌山案例,我們獲得了歷史時期保護修繕石窟寺文物的具體知識。也是在現(xiàn)場的觀察記錄中,我們同時草繪了全部圖表,和洞窟形制、布局的手繪記錄,重點的開鑿和重裝遺跡的草圖記錄,特別是標注出哪些遺跡需要專門圖版,哪些地方需要用線圖呈現(xiàn),哪些地方必須用正射影響圖呈現(xiàn)等等,客觀上使考古記錄成為統(tǒng)領(lǐng)其他各專業(yè)配合的核心。
數(shù)字化技術(shù)和考古工作的融合。須彌山石窟考古引入數(shù)字化技術(shù)在石窟寺考古界當然不是第一次,但把數(shù)字化技術(shù)作為石窟寺考古記錄的新方法的技術(shù)環(huán)節(jié),而不僅僅是為實現(xiàn)傳統(tǒng)石窟測量目標的輔助工具,確是第一次。如何使數(shù)字化技術(shù)真正成為考古記錄的新幫手,提升石窟寺遺跡記錄的成果質(zhì)量,因此成為一個問題。在須彌山石窟的田野工作中,我們堅持“考古的立場”,也就是數(shù)字化技術(shù)的工作目標是為記錄石窟寺的遺跡服務的,這項技術(shù)應當跟著石窟寺,或者說考古記錄的要求改進和升級;我們堅持“考古的在場”,就是強調(diào)數(shù)字化田野作業(yè)過程中,考古工作者必須和他們一起工作,向數(shù)字化工程師解析不同方位、類型遺跡的內(nèi)容,提出需要數(shù)字化技術(shù)進行工作的明確需求;同時堅持“考古的標準”,就是數(shù)字化技術(shù)的使用過程,甚至計算過程必須符合考古學“科學客觀”的要求,保證其過程的科學性,杜絕人工干預和違背科學路徑的任何虛假結(jié)果,其成果要達到“一旦石窟寺毀廢,可以據(jù)記錄重建的程度”的標準。在須彌山石窟田野工作中總結(jié)和堅持的數(shù)字化工作原則,已經(jīng)成為浙江大學文物數(shù)字化的根本理念。
圖版拍攝。洞窟測量記錄的遺跡,表達的是遺跡客觀的存在,反映的是石窟營鑿者、重裝者的思想和用一定工藝手法實施完成所呈現(xiàn)的客觀結(jié)果的遺留,即使有了數(shù)字化技術(shù)可以記錄遺跡的形色信息了,但我們觀察、記錄時與遺跡的交流和遺跡給予的啟發(fā)和我們從中的認知獲得,卻是不可測量的,比如石窟群所在的壯美山河和雕鑿遺存的微妙轉(zhuǎn)折!因此圖版拍攝,反映的就主要是測量無法完全反映的、觀察者認為需要特別強調(diào)并希望能夠同時呈現(xiàn)和表達的遺跡整體或細部,是考古工作者認識的角度和板眼所在,不可稍微輕易。不同類型的記錄用不同的方法,從事者都應當是專業(yè)的。在須彌山石窟考古工作中,我們強調(diào)根據(jù)考古要求攝影的圖版由專業(yè)攝影師完成,每一幀都應當是真正的攝影作品,構(gòu)圖、布光和畫面符合專業(yè)攝影標準。我們先后拍攝兩次,其中還得到文物出版社資深編輯蔡敏的專門指點。
報告的編寫。須彌山考古報告編寫過程中,我們把“原真呈現(xiàn)”遺跡本身確定為報告的目標,并以此為準安排章節(jié),盡量做到文字、測圖、圖版均成系統(tǒng),彼此相輔相成。這是我們對先生教誨的理解。報告結(jié)語,以遺跡為核心總結(jié),也是宿先生在報告寫作過程中反復強調(diào)的,“不要牽涉別的石窟的事,年代問題的討論可放在最后一卷。”
其實,沒有比記錄客觀事實更難的事了。從兩次田野工作完成到報告最終付印,前后用了差不多八年時間,固然我們學力不強怠惰懶散,而編寫石窟寺考古報告之難也確實非從事者難以體會。
行文至此,不禁懷念起并不久遠的須彌山石窟考古調(diào)查事前事中到報告編寫的那些永不復返的不短的歲月。那時候,宿先生精神尚好,關(guān)懷心切,我們在田野工作的每一天,都要向宿先生匯報,和先生保持著熱線聯(lián)系,聽著先生興奮的回應和針對新情況的指導教誨。在室內(nèi)工作的每一階段,差不多一個月就帶著整理的文字,不斷出來的圖,奉在先生面前。先生只要一聽到須彌山石窟考古的新發(fā)現(xiàn)和新進展,總是說“好!好!”發(fā)自內(nèi)心的欣喜難以名狀。先生家的墻上,一直貼著一幅須彌山壯美的全景,那是這次工作拍攝的先生心系的須彌山。直到先生辭世,照片都未從先生家的墻上摘下來過,成為先生最后歲月的背景。
從宿白先生第一次上須彌山的1984 年算起,至今已經(jīng)整整過去三十五年,須彌山報告的出版能稍慰我們對宿白先生深深的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