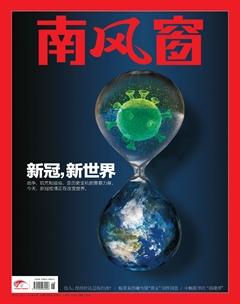新冠病毒如何推動制造業轉型

隨著新冠病毒疫情的逐步升級,全球供應鏈的內在風險,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暴露無遺。對此,先進經濟體的企業并未像以往那樣停下來,等待何時再將生產活動集中在那些勞動力廉價又充足的國家中,而是將注意力放在了工資最低的工人—機器人—身上。
在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鐵幕的倒塌、中國被整合進全球,以及集裝箱運輸的興起,企業開始將生產轉移到低工資國家。1990—2008年被稱為高度全球化時代,其中全球價值鏈大概占據了全球貿易的60%。
2008年的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標志著這個高度全球化時代的終結。全球價值鏈在2011年時停止了擴張,從那以后再也沒有增長過。
這種逆轉是由不確定性驅動的。從2008年到2011年,世界不確定性指數上升了200%。相比之下,在SARS期間該指數僅僅上升了70%,而在英國2016年投票決定脫離歐盟后則飆升了250%。
當不確定性上升時,全球價值鏈就會受損。根據過去的數據,可以預測不確定性增加300%(正如新冠病毒大流行所可能導致的那樣)將使全球供應鏈活動減少35.4%。企業也不再認為,外包所節省下來的成本能高于風險。
而在部署機器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廉價的時候,實現生產回流的動機也就更加強烈。這筆賬很容易算,比如一家美國公司向越南或孟加拉國工人支付的工資雖然比給美國工人的少得多,但是安裝在美國的機器人根本不會要求工資,更別提醫療保險或病假等福利待遇了。
對機器人的投資也不是什么新鮮事。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先進經濟體企業一直在追求這一目標,其中以汽車產業為最—該產業的機器人裝機量,可以占到全國總量的50%~60%。全球部署機器人最多的德國,2017年制造業每萬名工人相對的機器人裝機量為322臺,只有韓國(每萬名工人710臺)和新加坡(每萬名工人658臺)的比例更高,而美國的每萬名工人裝機量為200臺。
事實上當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一些國家(例如德國)已經擁有足量機器人以最大程度降低生產中人工成本的權重。其他許多國家,在2008年后利率相對工資比率急劇下降的推動下,也開始推廣機器人,并將更大份額的生產遷回了本國。
如今也可能會發生同樣的情況。根據迄今為止的貨幣政策,隨著央行試圖抵消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破壞性影響,預計利率會下降達30%。過去的數據表明,這可以使機器人的部署速度加快75.7%。
這種趨勢將集中在最受全球價值鏈影響的產業。在德國,這指的是汽車和運輸設備、電子產品以及紡織品—這些產業有大約12%的生產部件,進口自低薪酬國家。
在全球范圍內回遷最為積極的產業,是化學品、金屬產品以及電氣產品和電子產品。而化學產業則是法國、德國、意大利和美國回遷規模最大的產業。
這一趨勢對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增長模式構成了重大威脅,因為它們依賴于低成本制造業和中間生產部件的出口。在中歐和東歐地區,一些國家通過自身投資機器人來應對這一挑戰。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亞(擁有大量外資汽車行業)如今每萬名工人對應的機器人數量,都超過了美國或法國。
但那些亞洲低成本制造中心的日子就比較難過了,特別是經歷本次疫情大流行之后。盡管中國計劃轉向高附加值生產并增加國內消費,但這個以往通過確立自身在多個全球價值鏈中的核心地位來確保經濟增長的國家,將面臨特別嚴峻的挑戰。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權《南風窗》獨家刊發中文版。達利亞·馬林,慕尼黑大學國際經濟學教授,英國智庫“經濟政策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