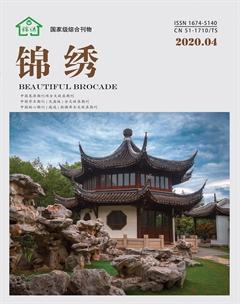淺析1844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創作邏輯
李子君
摘 要:《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是馬克思在世界范圍內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然而,盡管手稿經常被討論,對其作者的思想的總體解釋是如此重要,但很少有人關注它們存在的文獻學問題。本文簡要介紹了馬克思在法國首都的逗留時間和他從那里開始的經濟研究,考察了《1844年經濟與哲學手稿》與馬克思從政治經濟學家著作中編纂的節選的平行筆記本之間的密切聯系,以及他在他發展的這一主要時期所取得的更大的哲學和政治上的成熟。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手稿;馬克思主義
一、背景分析
巴黎是一個“可怕的奇跡,一個令人震驚的運動,機器和思想的集合,千千萬萬不同浪漫的城市,世界的思維盒”(Balzac,1972,33)。這就是巴爾扎克如何在他的故事中描述大都市對那些不徹底了解的人的影響。在1848年革命之前的幾年里,這個城市由工匠和工人在不斷的政治攪拌下居住。它從其流亡者、革命者、作家和藝術家的殖民地以及一般的社會發酵中獲得了在少數其他時代所發現的強度。具有最多樣化的智力天賦的男人和女人正在出版書籍、雜志和報紙,寫作詩歌,在會議上講話,在咖啡館、街上和公共長椅上無休止地討論。它們的緊密接近意味著它們對彼此產生了持續的影響。總之,這是歷史上最重要的時刻。巴爾扎克說“巴黎的街道具有人類的品質和如此的自然地理,讓我們留下沒有阻力的印象(Balzac,1972,310)這些印象也打動了卡爾·馬克思,他在1843年10月25歲時曾在那里運動;他們深刻地標志著他的智力進化,在他在巴黎的時間里決定性地成熟了。在新聞工作經歷之后,馬克思放棄了黑格爾理性國家的概念視野和相關的民主激進主義,但是,這是由無產階級的具體遠見所動搖的。
二、理論分析
馬克思著名早期文本的批判解釋,《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在他在巴黎停留的過程中,主要集中在文獻學問題上。在政治經濟上,當他RheinischeZeitung一起工作時,馬克思已經準備好應對特殊的經濟問題,但總是從法律或政治觀點出發。隨后,他在1843年在Kreuznach的思想中,對黑格爾的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貢獻的來源,在這個思想中,公民社會被認為是政治國家的真正基礎,他首次提出了經濟因素在社會關系中的重要性。但是,只有在巴黎,馬克思開始了一個“基于良心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研究”(馬克思,1975D,231),它從法律和波利的矛盾中得到了一個重要的動力,這些矛盾不能在自己的范圍內解決,也不能解決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馬克思在“摩西赫斯”、“錢的本質”的影響和他從思辨向社會-經濟層面的異化概念的反式地位的影響下,首先集中在對金錢經濟調解的批判上,作為實現人的本質的一個障礙。在對布魯諾·鮑威爾的“在猶太人的問題上,”中,他認為猶太人的問題是一個社會問題,它代表了資本主義文明的哲學和社會歷史預設。他的工作的指導思想是需要揭開和反對波提·卡爾經濟的最大的神秘化:它的類別在所有時間都是有效的,在所有地方都是有效的。馬克思深受這種盲目性的影響,對經濟學家來說缺乏歷史意義,因此,馬克思試圖通過把他們看作是自然的事實來掩蓋和證明其時代經濟狀況的不人性。他在一篇關于案文的評論中指出,“私人道具是一個事實,其憲法不涉及政治經濟,而這是它的基礎。因此,整個政治經濟是以缺乏必要的事實為基礎的。1”因此,政治經濟學將私有財產制度、相關生產方式和相應的經濟范疇視為永恒不變的。資產階級社會的人看上去好像是一個自然的人。這種不同的理解社會關系的方式產生了重要的后果,其中最主要的無疑是那些關于異化勞動的概念。與經濟學家或黑格爾本人不同,對他們來說,這是一種自然的、不變的社會狀況,馬克思走上了一條道路,這條道路將導致他拒絕異化的人類學維度,而傾向于一種觀念,這種觀念在歷史上根植于某種生產和社會關系的結構:人類在工業勞動條件下的隔閡。馬克思摘錄的“詹姆士·米爾”中的注釋突出了“政治經濟學如何將疏遠的社會交往形式定義為與人的本性相對應的本質和原始形式。”論,得出了這些結論,對自己的構成要素進行了批評,并對他們的結果進行了反轉。這涉及到了他在最激烈和不懈的努力中的參與。
在塞納河左岸,他計劃了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開始研究法國革命,以寫出《公約》的歷史,然后,他提出了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的批判,然后他就像一個瘋狂的人進入了政治經濟,這突然對最終清除德國的地形成為了對鮑威爾等人的先驗批評的首要任務。但他打斷了這一任務,寫了他的第一份工作:神圣的家庭。然后又有一百個項目:如果有批評要做,它穿過了他的頭,穿過了他的鋼筆。然而,馬克思認為他的信息是不夠的,他的判斷不成熟,使他無法出版他所從事的大部分工作;因此,它仍然是輪廓和碎片的形式。他的筆記因此極為珍貴。他們允許我們衡量他的研究范圍,包含自己的一些思考,應該被認為是他作品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也是巴黎時期的真實,他的手稿和閱讀筆記證明了他寫的東西和他對他人作品發表的評論之間的密切關系。盡管《1844年經濟學和哲學手稿》的特征不完整,但幾乎所有的讀數都被忽略或被視為不重要的文獻學問題(參見。Rojahn,1983,20)。此外,他們只在1932年出版了兩份單獨的版本。在由社會民主學者Landshut和Mayer組成的集合中,它們出現在標題“民族玻利維亞人(KunieundPhillios)”下(Marx,1932A,283-375),而在馬克思-恩格斯的GesamtausGabe中,它們是“《1844年第1844號公約》,《1844年公約》,《1844年公約》,《1844年公約》,《1844年公約》,第”(Marx,1932B,29-172)。這兩個部分之間不僅有名稱,而且內容也有差異,而且各部分的順序存在重大差異。蘭塞-梅耶爾版本由于原始手稿的解密而出現了錯誤,未能包括第一組文件,所謂的第一本手稿,以及直接歸因于馬克思的第四腳本,實際上是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的恢復。
三、總結
盡管有這些明顯的形式問題,盡管在不同版本出版后出現了混亂,而且最重要的是,人們知道第二稿(最重要但也是最分散的)大部分都從劇集中消失了,但新版本的關鍵翻譯或編者沒有對原件進行重新審查。然而,對于在對馬克思的各種解釋的辯論中如此重要的文本來說,這一點尤為必要。
參考文獻
[1]韓劍鋒,曹亞麗.淺析《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人的本質思想[J].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38(02):7-14.
[2]張德昭,鄧莉.馬克思哲學革命的內在邏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存在論和科學觀思想[J].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版),2019,46(01):36-43.
[3]肖寧.作為原則的“對象性活動”:《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隱含前提[J].江西社會科學,2019,39(01):27-33.
注釋:
[1]高新民.現代西方哲學[M].武漢 :武漢出版社 ,1996.第1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