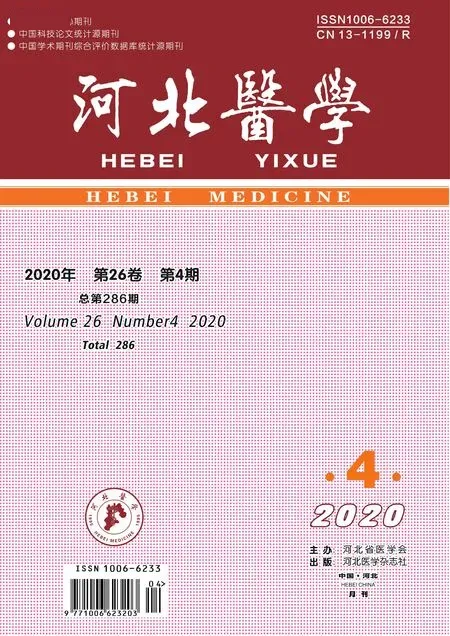遠隔缺血處理對心臟瓣膜置換術患者血清心肌肌鈣蛋白及全身炎性反應影響
莊煥偉, 白樹堂, 符洪犢, 梁麗明, 歐陽華, 張 亮
(1.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附屬海口醫院心胸外科, 海南 海口 570208 2.中山大學附屬第七醫院(深圳)胸外科, 廣東 深圳 518107)
心臟瓣膜置換術在臨床的應用已越來越廣泛,其在體外循環(cardiopulmonary bypass,CPB)下使用人工機械瓣膜完成替換手術[1]。但有相關資料指出,在CPB中因主動脈的阻斷、心臟停跳、復跳,易引起心肌缺血再灌注損傷(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IRI)從而引起心肌損傷,造成炎癥反應[2]。故有效減輕CPB時的IRI至關重要。就以上問題Murry等研究人員于1986年首次提出缺血預處理理論,后經Przyklenk發展為遠隔缺血預處理(remote ischemic preconditionin,RIPC)。現國內外已有大量文獻表明,RIPC可有效實現對心肌的保護作用,降低IRI,但對于心臟瓣膜置換術全身炎性反應的降低仍具有較大爭議[3]。基于此,本研究探討遠隔缺血處理對心臟瓣膜置換術患者cTnI及全身炎性反應影響,并分析其臨床價值,以期為臨床治療提供參考。現將研究成果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選取2017年8月至2019年8月于本院進行心臟瓣膜置換術的患者66例為研究對象,按隨機數字表法分為研究組、對照組,各33例。病例納入標準:①符合美國心臟協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HA)和美國心臟病學院(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ACC)發布的《2014心臟瓣膜病患者管理指南》[4]標準,且(New York Heart Association,NYHA)為Ⅱ~Ⅳ級者;②臨床資料完整,能夠配合完成本次研究者;③患者及家屬知情同意并簽訂同意書者。排除標準:①嚴重心、肝、腎等功能障礙者;②過敏體質或治療藥物過敏者;③感染性、炎癥性疾病者;④免疫系統疾病者。兩組患者手術類型、NYHA級別、手術時間及年齡等資料比較差異不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本研究征得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受試者均知情同意。

表1 兩組一般資料比較
1.2方法:術前兩組均進行常規檢查及術前準備,其中包括體征、心電圖、呼吸機檢查等。研究組患者在經麻醉誘導后,使用12cm寬的氣壓止血帶系于左側上肢處(距肘關節2~3cm),止血帶進行加壓充氣至35kPa,并持續5min,以阻斷上肢血流。然后減壓至0kPa,維持5min,促進上肢再灌注,重復以上過程4次。對照組患者在經麻醉誘導后,取氣壓止血帶系于患者相同部位保持40min,氣壓止血帶不進行充氣。
1.3觀察指標及評判標準:①心肌肌鈣蛋白I(cardiac troponin,cTnI):比較兩組患者麻醉誘導前、主動脈開放30min、主動脈開放6h及主動脈開放24h的cTnT濃度。方法:抽取患者肘靜脈血5mL進行離心,速度3000 r/min,10min,完成后,取上層血清-80℃保存備測,使用放射免疫測定儀(德國),采用雙抗體夾心法測定cTnT的濃度。②B型利尿鈉肽(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BNP):比較兩組患者麻醉誘導前、主動脈開放30min、主動脈開放6h及主動脈開放24h的BNP水平。③炎癥因子檢測:比較兩組患者麻醉誘導前、術中、術后6h及術后24h的腫瘤壞死因子(Tumou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介素-6(Interleukin-6,IL-6)、白介素-8(Interleukin-8,IL-8)水平。炎癥因子采用全自動生化分析儀(貝克曼庫爾特AU5800型),使用酶聯免疫吸附法進行檢測(試劑供自武漢博士德生物工程公司)。上述操作均遵循試劑說明嚴格進行。

2 結 果
2.1組手術前后cTnI水平比較:結果顯示,兩組患者麻醉誘導前cTnI濃度較低,主動脈開放后cTnI濃度隨時間的變化逐漸遞增(P<0.05),研究組cTnI濃度低于對照組(P<0.05),見表2。

表2 兩組手術前后cTnI水平比較(ng/mL)
注:與對照組比較*P<0.05;與麻醉誘導前比較aP<0.05;與主動脈開放30min比較bP<0.05;與主動脈開放6h比較cP<0.05;下同
2.2兩組手術前后BNP水平比較:結果顯示,兩組患者在麻醉誘導前至主動脈開放6h的BNP水平逐漸降低(P<0.05),主動脈開放24h后迅速升高(P<0.05),但研究組在主動脈開放30min、6h、24h的BNP水平低于對照組(P<0.05),見表3。

表3 兩組手術前后BNP水平比較(pg/mL)
2.3兩組治療前后的炎癥因子比較:結果顯示,兩組患者術后1d的TNF-α、IL-6、IL-8水平均升高(P<0.05),但在術后3d、術后7d的TNF-α、IL-6、IL-8水平均呈下降趨勢(P<0.05),且研究組患者的TNF-α、IL-6、IL-8水平在術后3d、7d均低于對照組(P<0.05),見表4。

表4 兩組治療前后的炎癥因子比較
注:與對照組比較*P<0.05;與術前比較①P<0.05;與術后1d比較②P<0.05;與術后3d比較③P<0.05
3 討 論
心臟瓣膜置換術可分為二尖瓣置換、主動脈瓣膜或雙瓣置換等,其主要針對心臟病變的瓣膜,在CPB下將病變瓣膜置換為良好的瓣膜,以促進患者心臟功能的改善,提高患者預后。但有相關資料顯指出,手術創傷、CPB管道于血液之間的接觸、毒性釋放、血液稀釋及IRI等均可促進炎癥因子的激活,從而導致全身炎性反應,造成患者心臟嚴重損傷,影響預后[5]。因此術中有效保護患者心肌功能,減少IRI至關重要。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者經不斷的臨床實踐探究指出,RIPC對心臟瓣膜置換術患者的心肌具有積極的保護作用[6]。RIPC是通過氣壓止血帶對患者進行短暫的非致死性的輕度缺血處理,以此來降低遠隔器官因缺血而產生致死性損傷,從而使被保護的臟器能夠耐受較長時間的IRI。李彩鳳[7]等研究人員指出,臨床上關于RIPC對腦缺血造成損傷的保護機制雖尚不明確,但有學者指出其可減少IRI,從而減少缺血造成的血腦屏障的破壞,且RIPC后可能會產生神經保護物質,并通過內源性物質釋放后介導細胞內新的蛋白合成及基因調控來實現缺血損傷的降低。
cTnI為心肌肌肉收縮的調節蛋白,其水平會隨心肌損傷而發生變化。郭圣東[8]研究指出,cTnI具有較高的敏感性和特異度,當心肌細胞損傷時,存在于胞漿中游離的cTnI會在外循環中大量釋放,從而導致cTnI水平升高明顯。本研究中兩組患者麻醉誘導前cTnI水平均較低,主動脈開放后cTnI水平逐漸升高,但行RIPC處理組的患者在主動脈開放30min、6h、24h的cTnI均低于常規止血組。結果提示,心臟瓣膜置換術中兩者均發生了IRI,使得cTnI水平逐漸升高,但在麻醉誘導后行RIPC處理可降低心肌損傷,減少手術雖心肌功能的損害。而BNP為心室分泌的神經激素,其與心臟功能密切相關。據資料指出,BNP可作為無癥狀心力衰竭及心力衰竭早期的篩查指標,且其水平隨心功能衰竭程度而升高。且當心室功能不全或瓣膜功能障礙時,BNP經合成大量釋放,水平即升高。本研究中兩組患者的BNP水平在麻醉誘導前至主動脈開放6h逐漸降低,后迅速升高,其水平變化與瓣膜置換術中動脈阻斷、灌注停博、重新開放及IRI過程一致。但行RIPC處理組的患者在主動脈開放30min、6h、24h的BNP均低于常規止血組。說明RIPC對書中患者心肌具有一定程度的保護作用。
如上所述,手術創傷、CPB管道于血液之間的接觸、毒性釋放、血液稀釋及IRI等均可促進炎癥因子的激活,從而導致全身性炎性反應。TNF-α為巨噬細胞產生,它能有效促進中性粒細胞的吞噬作用,從而引起機體發熱,并對肝細胞急性期蛋白的合成具有誘導作用,促進細胞進行分化,進而參與機體病理損傷。而IL-6、IL-8均是促炎細胞因子,IL-6由多種細胞共同合成,它能與肝細胞的合成進行刺激,從而生成急性期蛋白,參與炎癥反應。另有相關文獻表明,IL-6也可刺激肝細胞,因此當機體受到感染后,會對急性期反應蛋白進行合成誘導,從而提高機體內hs-CRP水平[9]。而IL-8具有生物活性作用,它能夠與中性粒細胞進行作用,發生形態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可導致機體局部的炎癥反應,促使細胞發生損傷。本研究中,術后1d的TNF-α、IL-6、IL-8水平均升高,但在術后3d、術后7d的TNF-α、IL-6、IL-8水平之間下降,且行RIPC處理組的患者的TNF-α、IL-6、IL-8水平在術后3d、7d均低于對照組。結果說明,瓣膜置換術中行RIPC處理可降低患者全身炎性反應,改善預后。
綜上所述,RIPC可有效減輕心肌的IRI,在瓣膜置換手術中對心肌起到了保護作用,且對于患者炎癥反應的降低具有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