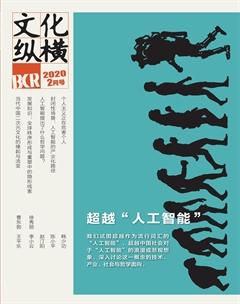當代中國二次元文化的緣起與流變
曹東勃 王平樂
[青年與青年價值觀·欄目導語]
2020年,中國大學生將基本由出生于21世紀的“00后”構成,而“90后”“80后”也將成長為社會的中堅力量。至此,改革開放后成長起來的這一代青年,正式成為社會主流。這場代際更迭將對中國乃至全球發展帶來怎樣的深遠影響?
作為成長于國家上升期的“豐裕一代”,他們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發展出空前的個體化意識;同時,他們的成長伴隨著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虛擬世界創造的豐富文化空間構建出新的身份認同,為他們建立起不同于父輩的認識世界、社會交往、集體行動的模式。曹東勃、王平樂的文章,詳細梳理了青年群體中流行的“二次元”文化的來源及基本特點,深入討論了這樣一種 “亞文化”如何塑造青年人的思想偏好與價值傾向,以及這樣一種青年文化與主流文化之間存在著什么樣的張力。
只有理解青年的精神文化需求,才能走近青年,引導青年。2019年12月刊,我們以“新青年與新個人主義”為封面專題,開啟了這一話題的深度討論,并正式將“全球變局下的當代青年問題”列入我們未來的研究重點。我們將延續12月刊的討論,開設“青年與青年價值觀”欄目,持續關注這一領域的深度研究。
一、問題的提出
二次元文化是當下青年思想文化現象之一,具有鮮明的世代特征,并與現時代中國發展的歷史進程、面臨的時代狀況、遭逢的社會思潮變遷密切相關。
近年來,學術界圍繞青年思想文化變遷展開了諸多有益探討。筆者在2016年曾圍繞“‘95后全面占領大學”(即當年的應屆大學畢業生主要出生于1994年)這一節點,從1995年發生的“Windows95版推出”“《仙劍奇俠傳》游戲發行”“《大話西游》上映”三件小事,總結了“95后”的三個特征:
一是開放性。其父輩大體為“65”“70初”一代,因此其成長階段可被視為中國家庭對子女投入從“人多錢少”轉入“人少錢多”的關鍵時期。由此,相當一部分在校大學生成長于家境殷實的家庭,享受改革開放豐碩結果,他們與“80后”一代顯著不同,正如其父輩與“80后”的父輩“50后”顯著不同。
二是互動性。他們既親身見證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快速崛起,又通過互聯網接觸到過往歷史與現實中的其他維度,兩者的糾纏交織構成了他們在思想方面的基本底色。對他們來說,生活實踐大于專業教育,專業教育大于網絡影響,網絡影響大于空洞說教。

二次元指稱由動畫、漫畫、游戲所創造的虛擬人物構成的虛擬世界
三是解構性。傳統教育結構中,本應處于消極被動接受主流價值觀念熏陶和教育的一方,如今卻可輕而易舉地反戈一擊,對施教者及其宣教的知識、理念、信念展開間接的揶揄、反諷,或直接的惡搞乃至顛覆。這是后現代思潮潛移默化的時代影響。[1]
對上述判斷,陳立明、劉炳輝在2019年以“復興一代”為核心概念和分析框架提出了商榷,認為“后現代主義”的概括有失偏頗,“95后”整體上是可愛、可信、可為的一代。[2]應當承認,從2016年到2019年,國內外的確發生了諸多變化,特別是全球范圍內的逆全球化、內卷化趨勢和中美貿易沖突向思想文化等領域的滲透,都對陳立明和劉炳輝文章的判斷提供了一定的事實支撐。不過,正如陶慶梅以“新個人主義”對當下青年個體與民族國家之間新的張力及其背后文化模式和情感結構的解讀,[3]以及“中國大學生社會心態研究”課題組指出這一代青年身上“體現的對國家和現有秩序的支持,是其社會心態與主流價值觀最為關鍵的耦合點”[4],“開放性、互動性、解構性”的特征與對這一代青年“可愛、可信、可為”的總體樂觀判斷之間并不矛盾。青年思想文化研究中的這種爭鳴,恰恰更加說明當代青年思想文化結構的深層復雜性,也啟示主流價值系統面對青年文化需要采取更為有效的因事而化、因時而進、因勢而新的姿態。
二、何以生成:二次元文化的中國落地
“二次元”一詞源于日本,最初是對“two dimensional”(二維的)一詞的日語翻譯。本意指“可以用 X 軸和 Y軸來定義的二維空間,漫畫和動畫描繪的是平面的二維空間,因此是二次元的”[5]。狹義的“二次元”也就是這樣一種象征和符號,指稱由Animation(動畫)、Comic(漫畫)、Game(游戲)所創造的虛擬人物構成的虛擬世界(簡稱“ACG”)。廣義上的“二次元”,也泛指ACG愛好者所構成的亞文化社群及相關產業所形成的文化產業鏈條,特別是將這種虛擬世界中虛擬人物的“人設”“三觀”與行為模式放大、映射到現實世界中,甚至形成某種“入戲”過深的代入感或幻象。
“二次元”概念雖然是我國近些年才出現的專業術語,但其事實的發生要早得多。“80后”可能是國內最早的二次元文化受眾,且其孩童時代的“角色扮演”(role play)經歷了一個本土化到逐漸去本土化的過程。這一過程,大致是從《大鬧天宮》《神筆馬良》《黑貓警長》《葫蘆兄弟》《邋遢大王》《舒克和貝塔》等中國國產動畫片,先過渡到美式的《貓和老鼠》《星球大戰》《變形金剛》,再過渡到日本的動漫文化。20世紀80年代,在尚屬寬松的監管體系和比較和諧的中日關系背景下,國內電視臺引進《圣斗士星矢》《七龍珠》《灌籃高手》等動漫作品,這些更具人間煙火氣的虛擬人物,既不同于完全針對低齡化幼稚階段小孩子、毫不掩飾教育意圖的國產水墨動畫片,也不同于“傻大黑粗”、把生活場域完全投射到久遠未來外太空某個角落的美式動漫,成為課余飯后在校園內外嬉笑打鬧時樂于模仿和扮演的二次元角色。
20世紀90年代可以說是二次元文化在中國的全面擴散階段。從中央級的電視臺到地方臺的黃金時段,基本都有日本動畫片的轉播;而彼時中小學生熱衷光顧的專營租書的書店或書社,日式漫畫書也幾乎和真真假假的金庸作品平分秋色。1998年后,國家出臺針對引進海外動畫片的一系列限制政策,使二次元文化在主流媒體遭到全面封殺達十年之久。但與此同時,國內各大高校BBS開始出現ACG的專門板塊,供用戶進行相關作品的資訊分享與交流,以互聯網媒介為基礎的二次元文化在這一時期逐漸成形。隨著互聯網的進一步發展和個人電腦的普及,PC端主機游戲、網絡游戲也逐漸走入大眾視野,普通二次元用戶利用網絡媒介進行二次元作品的創作和傳播也更加便捷。
分別創建于2007年和2009年的視頻網站AcFun(A站)和Bilibili(B站),效仿日本的Niconico網站,推出彈幕功能。這種線上即時品評臧否、互動吐槽的視頻傳播方式深受用戶喜愛,成為今日二次元文化傳播的重要形式。當下的二次元文化正在從虛擬世界向現實世界拓展延伸。二次元愛好者模仿自己喜愛的虛擬角色,裝扮成他們的樣子,即所謂“cosplay”(角色扮演);將喜歡的劇情或創作的同人臺本搬上舞臺,搞真人舞臺秀;動漫同好聚集一堂,在一年一度的中國國際數碼互動娛樂展覽會(ChinaJoy)上互動交流。
三、身份召喚:二次元文化的青年基礎
當代青年群體所處的社會背景與二次元文化早期傳入時相比,已有較大不同,主要表現在生活方式和表達方式兩方面。
從生活方式上看,間接經驗高度發達,直接經驗相對欠缺。他們熟悉并擅長運用現代科技工具,高效快速獲取信息、傳播信息,行為方式也更趨便捷化、智能化。基于親緣、地緣、業緣等傳統的交際網絡雖然仍在發揮影響,但借助于互聯網移動終端的新媒體社交,才是他們典型的交往方式。互聯網讓他們可以突破現實人際圈,也巧妙地隱藏了交往對象之間在社會地位、職業、年齡等方面的差異。
他們一方面是個體化程度空前的一代人,另一方面也是虛擬世界社會交往程度空前的一代人,各種問答社區、興趣群組、地方性網絡組織都備受他們的青睞。他們本著“怎么都行”的心態與外界互動,追求生活的多樣性和新鮮感,有明顯的叛逆心理和行動表現。也正因如此,二次元文化幾乎是十分開放包容地看待諸如宅男、腐女等各類亞文化群體及小眾議題。同時,由于他們實際處于社會話語權相對弱勢的地位,因而也在借助這種特立獨行的方式確立身份認同,為自身“壯膽”,為承認而斗爭。
從表達方式上說,傾向于另起爐灶,建構自成一派的話語系統。首先是情緒表達的碎片化。快節奏的生活使他們難有大把的精神消遣和情感宣泄的時間。因而一些熱門的短視頻APP,如抖音、快手等,正適應了他們的這種“快閃”式的特點。這種小塊的情緒碎片也為二次元文化群體的二次創作和表達,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其次是文化表達的符號化。他們擅于以后現代主義的解構方式,對現有的文化質料加工、組合、改寫、重建,最終呈現為新的符號體系。以“表情包”創作為例,在一些大眾熟知的圖像基礎上,對圖片進行改造或配上簡潔的文字,或是調侃,或是嘲諷,或是批判,以這種拼貼重塑的方式賦予其新的內涵。 “姚明笑”“葛優躺”等,莫不如此。
最后是社交表達的圈層化。網絡社交在青年群體的社會交往中舉足輕重,由網絡交友逐漸形成網絡文化圈,繼而形成小規模的社交群體。以不同的愛好或風格為標準劃分“圈子”:“御宅”有“御宅”的文化,“飯圈”(粉絲群體)有“飯圈”的規矩。一個青年人可能同時身處多個“圈子”之中,但圈外人往往對圈內的語言一頭霧水。如“CP”(Coupling,人物配對或同人配對)、“YY”(意淫,指腦補、自行想象CP或idol的不實際內容)、“KY”(指做出煞風景、不解氛圍、不合時宜的言論或行為)、“發糖”(喜歡的配對人物出現了新的甜蜜劇情的動態)、“寄刀片”(編劇設定的劇情不合理或讓觀眾無法接受時,觀眾就可揚言給編劇寄刀片)等“圈內行話”或“黑話”,都是青年群體在社會交往活動中的圈層化表達的產物。
四、并非奇葩:二次元文化的特征解讀
作為一種不容忽視的青年文化現象,二次元文化自身的一些特征,也與當代青年的前述特點相契合。
(一)創造性反抗
一方面,在方式上,青年人借助于新媒體、新平臺和新技術來傳播和表現二次元文化。這種傳播和表現的方式是創造性的,他們可以隨時隨地通過手機、電腦終端進入二次元世界。在線上的小說、漫畫、動畫、短視頻、電影、電視劇和線下的衍生周邊、cosplay、社團、展演等豐富而集中的呈現中,營造一種集體狂歡的盛大圖景。
另一方面,在內容上,青年人在獨特空間中創造屬于自己的文化觀念和精神世界。我們在詢問二次元文化對青年群體的吸引力時,受訪者比較集中地提到如下一些方面:豐富多彩的表現形式、刺激爽快的感官沖擊、青春熱血的理想信念、天馬行空的想象空間——“藝術想象就是為一個舊的內容發現一種新的形式”[6]。這種“舊瓶裝新酒”的二次創作,也使二次元文化天然地具有一定的反抗性。
更準確地說,這種反抗更應該被理解為一種溫和的吐槽與調侃、善意的戲謔與反諷。中國的二次元文化,還不是對主導地位文化公然抵抗,它更多表現為對成人文化或主導文化的顛覆性重構和再闡釋。

二次元文化愛好者常因某種相同的興趣愛好而聚集成為趣緣群體并獲得歸屬感
2015年底,互聯網上突然出現一陣對五六十年代的宣傳畫進行“再創作”的風潮,諸如“我就是喜歡你看不慣我,卻又不得不同我一起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樣子”“如果說我們還有絲毫的聯系,那大概就是我們都是社會主義接班人吧”“你追我,如果你追到我,我就和你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等語言邏輯跳躍又充滿戲謔意味的語句,配上經典社會主義風格的圖片,呈現一種微妙的亞文化特點。我們并不傾向于認為這種顛覆和惡搞有什么更深的內涵或幕后的黑手。恰恰相反,他們并不想與主流文化或父輩的教諭公開沖突,而只是用另辟蹊徑的文化解讀方式,進行一種稍顯叛逆的自我表達、自我宣泄與自我滿足。他們面對成長的煩惱,把在二次元的世界里“借殼上市”“指桑罵槐”“顧左右而言他”,作為情緒的出口與“弱者的武器”,這何嘗不是另一種“求關注”“搏出位”,以及爭取身份認同的方式?
(二)趣緣性排他
趣緣是指人與人之間因相同的興趣、志趣而結成的一種社會交往關系。二次元文化愛好者之間非常容易因相同的興趣愛好、相似的審美觀念和價值取向而聚集成為一個趣緣群體,并獲得歸屬感。喜歡同一本小說的人、喜歡同一部動漫的人、喜歡同一對CP的人之間,都可以組成這種以趣緣性關系為基礎的二次元內的小群體。二次元文化在這個意義上說,其實就是一種青年群體出于對相關文化作品的喜愛,通過互聯網媒介尋找同好進行的趣緣性實踐活動。
這種趣緣性的文化實踐活動也可以從網絡平臺延伸至現實世界。二次元用戶可以在不同的趣緣群體之間“滑動”,一個人可以同時喜歡cosplay、Lolita(洛麗塔裝扮)、Vocaloid(人聲歌曲合成軟件),并同時加入他們的同好社群。但這些同好社群之間又是相互獨立、無法相互替代的。以各自的趣緣關系為基礎建立的不同趣緣群體之間,會表現出相互排斥的傾向。最為典型的表現就是不同CP粉(某組配對人物的粉絲)之間的“掐架”。按照布迪厄的觀點,場域是社會個體參與社會活動的主要場所,是集中的符號競爭和個人策略的場所,每個場域都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二次元”群體就是以趣緣關系為基礎聚集形成的相對獨立的“場域”。二次元文化就是青年群體自我創建的區別于現實世界和成人文化的精神空間。
(三)虛擬性實現

二次元文化是青年群體出于對相關文化作品的喜愛進行的趣緣性實踐活動
根據盧揚的調查,我國二次元用戶以獨生子女為主,有兄弟姐妹的二次元核心用戶是極其罕見的。[7]獨生子女的成長過程比較孤單,二次元作品可以給他們帶來精神上的撫慰,彌補情感上的缺失,實現感情上的滿足。比如,將二次元作品中喜愛的角色當作自己的朋友或兄弟姐妹,得到情感上的共鳴與陪伴,“在二次元的世界中才能找到共鳴/治愈/愛”[8] 。
核心二次元用戶在二次元文化體系中無疑是最大的貢獻者,其中有一部分人還會進行二次元作品的創作或者再創作。這些核心二次元用戶自我價值的實現,大部分來自其原創作品得到其他二次元用戶的喜愛以及群體的認可。優秀的“UGC用戶”(原創作者)還會被網絡平臺邀請簽約,進一步實現商業價值的創造。二次元文化的虛擬性,是與其以互聯網為主要媒介的傳播形式密切相關的。在這個與現實相區隔的二次元世界中,青年們得到了情緒的釋放、情感的寄托甚至自我價值的實現。
五、正反兩說:二次元文化的思想影響
從主流文化視角來看,二次元文化無疑對青年人的思想偏好和價值傾向有很強的影響。結合對青年的調研訪談,我們似可大致梳理出二次元文化的若干影響。
一是以志趣為核心構建的自主社交空間;而這樣的自主社交空間,也容易產生群體排他性,導致社交疏離。
二次元平臺創造了一個自由選擇的廣闊社交空間。這里不再以地緣、業緣、親緣論親疏,完全以青年自身的興趣愛好為主軸,撐起一面網,建構自己獨特的語言體系。這里形成了一套“默會知識”系統—諸如“大清藥丸”“火鉗劉明”等從二次元作品中生成的“行話”,只有共同接觸過這些作品的人,才能“get”其中準確含義。而從老“梗”中又會不斷衍生新“梗”,話語體系隨之逐漸擴張。
在完全自發的二次元社交空間中,部分群體還會出于共同的興趣愛好而產生有組織性、有紀律性的團隊合作活動,以此互利互惠。對于大多數參與者來說,這個自發的社交空間最基本而單純的作用,是自由結交同好帶來的快樂,以及從中找到一種新的身份認同和歸屬感。
但對主流文化而言,趣緣性排他固然能帶來一種“去政治化”的效果,但它的另外一個面向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封閉內卷甚至社交恐懼。
二次元文化與一次元文化(以文字為基本媒介的文化形式)、三次元文化(由拍攝真實的人、事、物構成的三維的電影、電視劇等文化形式)相區別,而二次元文化與作為現實世界的三次元之間橫亙著的壁壘被他們稱為“次元之壁”。這種在他們看來難以跨越的代際鴻溝和文化觀念差異造成的壁壘,使二次元愛好者在面對三次元時,容易先入為主地產生接受障礙、表現出排斥心理,更希望退避于自己的二次元世界之中,以不被三次元文化所同化。
面對強勢的成人社會群體的不解和誤解,二次元用戶群往往無力辯駁。而當父輩以“叛逆者”“崇洋媚外”甚至“漢奸”等標簽加諸二次元文化群體之時,這些外部壓力進一步壓縮了雙方的交流空間。最終多是采取“二次元不需要被三次元理解”的態度,放棄溝通的意愿。
這道難以逾越的“次元之壁”,使得二次元文化愛好者更傾向于劃分界限,以結隊來維護內部圈層的“純粹與美好”。這種內卷傾向在特定情況下會表現出某種一致對外的網絡集體行動,如各類“守護”“出征”。“青年群體以獨有的風格和個性凸顯群際差異,區分內群和外群,在排斥外群的積極表現中獲得群內認同,這種認同往往是一種‘拒斥性認同,力圖通過與外部的對抗來支撐內部的共同‘戰壕。”[9]可以謹慎樂觀的是,絕大多數二次元用戶認識到他們與現實社交相疏離的問題,并且有積極打破“次元之壁”的嘗試。在我們的訪談中,一位“00后”本科生表示:“我們可以在二次元的天地獲得快樂,同時也會在三次元過好自己的生活。”
二是二次元文化追求異質表達,青年群體借此發揮想象,也是在創造新的文化與精神表達方式。
青年人在日常生活、學習和工作的壓力之下,很難或不愿在人前表露真情實感。但在二次元空間里,他們卻可以擺脫現實束縛、放飛自我。現實世界是等級森嚴、律令嚴苛的現代性的國度,二次元的理想世界中人們卻大可無拘無束、隨心所欲,呈現為一種精神的狂歡,[10]這表現在二次元文化利用解構、拼貼、重塑、轉譯等手法創造新的文化符號,并擁有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其塑造的文化空間不僅在二次元世界中,也成了當代青年日常生活的存在,甚至也會成為社會關心的熱點。
這種精神狂歡的典型表現形式即“鬼畜”。
在彈幕視頻網Bilibili流行這樣一個說法:B站只有兩個分區,一個是鬼畜區,另一個是鬼畜素材區。所謂鬼畜,即使用素材在音頻、畫面上做一定處理,達到與BGM一定的同步感。2018年2月,一個名為《趙本山:我就是念詩之王【改革春風吹滿地】》的鬼畜視頻爆紅網絡。截至2020年1月,僅B站平臺就獲得5007.9萬播放量和36.6萬彈幕。事實上,“改革春風吹滿地,中國人民真爭氣”這句“宏大敘事”,承載著太多的歷史記憶,幾乎是20世紀90年代后期人盡皆知的一個“梗”。這一句“大詞”,先是在1999年的央視春晚中經由趙本山之口進行了解構式創作,時隔近二十年后又被二次元文化重新“發掘出土”、二次創作。視頻作者表示,其創作初衷只是想表達自己對兒時春晚記憶的一種懷念。[11]
這種極具后現代風格的精神狂歡,既提醒人們關注青年群體的精神文化訴求,同時它本身也正是精神壓力的一種紓解方式。
三是二次元文化在虛擬與現實之間的模糊存在,容易導致青年人的角色錯位,也容易帶來行為失范。
二次元虛擬世界景觀之豐富、情節之跌宕,會誘發一種近乎真實的代入感。三觀仍在定型過程中的青年群體,也容易將其在現實生活中遭遇的無助、追求的理想投射其中,將希望寄托在這個虛擬世界中。所謂“二次元嫁”就是這樣一種狀態,即把二次元世界中的角色作為自己理想的婚戀對象——這些“男神女神”們不會老,不會死,永遠“凍齡”,沒有丑聞,絕對完美。這使得他們以一種極為嚴苛的姿態去審視現實世界中交往的對象,而越接觸,卻越發現距離自己的理想類型相去甚遠,從而拒絕進一步的交往。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如果罔顧社會規則和道德標準,走向極端的自我中心主義,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的自我認同矛盾與混亂也就很難調和。
此外,對中國來說,二次元文化本質上是外來文化,時至今日,國內二次元文化仍然是以日本動漫占據主導地位,其次為歐美作品,因此存在如何與本土的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相適應、相融合的問題。有些二次元文化作品中夾帶美化戰爭、歌頌軍國主義、消解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私貨”,值得警惕。二次元文化在青年群體中具有傳播優勢,但如不加辨析地全盤接受其中夾帶的價值觀念,難免會對尚處在成長階段的青年群體產生誤導,甚至導致行為的重大差錯。2018年,兩名青年男子在南京紫金山邵家山抗戰碉堡遺址前身穿仿制“二戰”日本軍服的照片被網友曝光。2018年5月1日正式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英雄烈士保護法》,是對那一時期類似行為的明確回應。這類現象值得引起人們對二次元文化的深刻反思。“精日”“兩面人”等言行的背后,未嘗不是價值觀念的紊亂,而偏離主流價值觀的二次元作品能夠在青年群體中產生影響,也間接說明了本土二次元文化的脆弱和創作發展的緩慢。
六、破壁之道:二次元文化的代際和解
我們該如何面對二次元文化?

利用解構、拼貼、重塑、轉譯等手法,二次元用戶創造出“鬼畜”等精神狂歡作品
一些年長者視二次元文化為洪水猛獸,堅持采取絕對拒斥的態度,每每對一些無傷大雅的“調侃”“反諷”上綱上線,動輒深挖“幕后黑手”,收效卻總不理想。事實上,對二次元文化“認真你就輸了”。當主流文化舉輕若重地調用各方面知識,對某個二次元文化現象進行一本正經地理論批判時,總會豁然發現,“敵軍”已宵遁不知所蹤。有一些人則采取“無所謂”的觀望放任心態或掩耳盜鈴的鴕鳥姿態,甚至用“以段子對抗段子”的自欺欺人的方式,自以為主動迎合與降尊紆貴就一定能夠在“打入敵人內部”后成功實施“策反”,其實這更可能是對時間和資源的浪費。
不論承認與否、偏好如何,二次元文化的存在至少分割了主流文化的部分空間。如何回應這種挑戰,既是對主流文化的一種考驗,但也可能是對主流文化的一次豐富。主流文化必須吸收它,豐富主流文化本身的內涵,才能與時俱進,在新的時代保持自身的領導力。近年來,黨政部門越來越多地“征用”二次元文化語匯,“任性”“萌萌噠”“主要看氣質”等網絡話語開始登堂入室,“燃”“給力”“點贊”“硬核”等甚至被用于官方場合領導人講話。主流文化主動對二次元文化符號吸納和轉碼,“高大上”的官方機構到二次元文化平臺上“開張營業”,具象化為互聯網上的一個個IP并建構其“人設”,這種“真香”姿態本身就說明了二次元文化絕不可能簡單地一拒了之。
對于主流文化而言,在大運動、大迂回、大包抄的過程中,賦予本土二次元文化更深內涵,是一條可行之路。近年來的《大圣歸來》《大魚海棠》《大法師》《白蛇·緣起》《哪吒之魔童降世》等國產動漫,以馬克思為傳主塑造的國產動漫《領風者》,均收獲不錯的口碑和票房。
主流文化需要直面和正視二次元文化對青年文化價值觀正反兩面的復雜影響。正視、尊重和理解,而非簡單否定和排斥,才能走進青年,消除“次元”之間的壁壘。了解青年的生存境遇和精神文化需求,在存異求同的基礎上開展對話,才能潛移默化、潤物無聲地實現有效引導。
作者單位: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責任編輯:張文倩)
--------------------------------------------------------
* 本文為上海市學校德育理論研究課題“新時代上海大學生的思想特點與行為規律研究”(項目批準號:2019-B-004)階段性研究成果。
[1] 曹東勃:《大學全面進入“95后世代”這意味著什么》,載《文匯報》2016年9月9日。
[2] 陳立明、劉炳輝:《復興一代:“95后”大學生的時代特性剖析》,載《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
[3] 陶慶梅:《當代青年的新個人主義—從<哪吒之魔童降世>談起》,載《文化縱橫》2019年第6期。
[4]? “中國大學生社會心態研究”課題組:《當代大學生社會心態調查報告》,載《文化縱橫》2019年第6期。
[5] 沃爾夫岡·韋爾施:《重構美學》,陸揚、張巖冰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 ~ 187頁。
[6] 魯道夫·阿恩海姆:《藝術與視知覺》,滕守堯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97頁。
[7] 盧揚:《“御宅族”—“二次元”的建構者與體驗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 第50頁。
[8] 艾瑞咨詢:《2015中國二次元行業報告》,
http://report.iresearch.cn/report/201507/2412.shtml ,第192~248頁。
[9] 平章起、魏曉冉:《網絡青年亞文化的社會沖突、傳播及治理》,載《中國青年研究》2018年第11期。
[10] 原宙:《青年網絡“吐槽”現象的亞文化透析》,載《思想理論教育》2016年第6期。
[11] 《趙本山:我就是念詩之王【改革春風吹滿地】》,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1939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