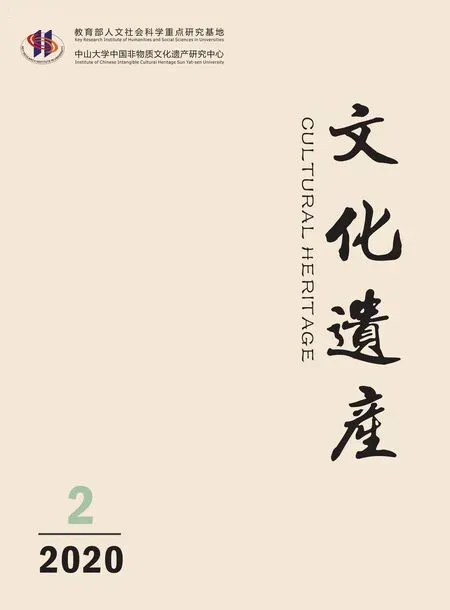非物質文化遺產商標保護的實踐、問題和對策*
羅宗奎
一、引言
非物質文化遺產(下稱“非遺”)的商標保護作為非遺知識產權保護的一種模式,一直受到學者的重視。羅伯特·K.帕特森指出:“相比于專利和版權,商標區分商品來源的本質屬性使其適合于非遺保護。”(1)Robert K.Paterson, Dennis S.Karjala."Looking beyo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resolving protec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indigenous peoples." Cardozo J.Int'l & Comp.L.11 (2003): p.633.楊建斌認為:“在現行知識產權制度中,保護非遺最直接有效和沒有爭議的應為商標制度。”(2)楊建斌:《商標權制度與非物質傳統資源的保護》,《北方法學》2010年第2期。雖然商標保護模式在非遺保護中存在一些局限,但它能夠充分體現非遺的經濟價值,且可兼容群體性主體、有利于活態傳承、無期限限制等優勢卻非常突出。(3)可參見徐輝鴻、郭富青《非物質文化遺產商標法保護模式的構建》,《法學》2007年第9期。Susy Frankel."Trademarks and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cultur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Legal Research Papers.Volume 1 Issue No 6, 2011.等。在目前非遺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不完善的現實條件下,商標保護模式具有重要價值。那么,我國非遺的商標保護運行實踐如何?存在哪些問題?這些均須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確定。由于非遺的商標保護必然通過“非遺商標”來實現,因此從“非遺商標”申請與注冊情況的視角來透視非遺的商標保護狀況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本文便擬從這一視角展開實證研究。但在研究之前,筆者擬先對非遺商標、非遺的商標保護之內涵以及二者之間何以聯結的內在機理作一闡釋,這也正是本文實證研究的理論基礎所在。
首先,所謂非遺商標,可定義為主要以非遺符號為構成要素的商標。眾所周知,非遺不僅是文化多樣性的重要體現,也是一個天然的符號寶庫。非遺項目名稱、曲目劇目名稱、傳承人姓名、圖騰標志、民族服飾佩飾形象等,這些非遺符號極具文化底蘊,是典型的傳統文化符號。與非遺實體的整體性文化價值不同,這些文化符號是非遺表達形式的碎片化存在,但其上卻附載著傳統文化衍生的知識產權利益,非遺商標正是這種衍生知識產權利益的表現。而申請和注冊非遺商標其本質乃是文化系統的文化符號向法律系統的商業標志轉換的結果,同時也是將非遺保護與商標法聯系起來的紐帶。
其次,相比作為事實或現象的非遺商標,非遺的商標保護則屬于一個論題或命題。它內涵“非遺保護”的文化價值目標,又是非遺法律保護的一種具體模式,處于“非遺的法律保護—私法保護—知識產權法保護—商標法保護”這一制度體系之中。從保護機理上來說,所謂非遺的商標保護具有兩種含義:其一是針對非遺的商標侵害進行排除的含義,為行文之便,我們將這種含義的保護簡稱為“被動保護”。因為非遺所有者(下稱“內部人”)之外的市場主體(下稱“外部人”)將非遺符號搶注為商標,這種搶注可能對非遺的文化內涵產生歪曲、侮辱、淡化,需要通過商標法對侵害予以排除,如美國曾經出現的“華盛頓紅皮”案(the Washington Redskins)和“齊亞太陽符號”案(Zia’s sun sympol),印第安人就認為將他們的部落標志注冊為商標是對他們文化的貶損;再如將“二人轉”注冊在避孕套之上可能會對“二人轉”非遺項目產生歪曲甚至侮辱,便可通過商標法的相關規定阻止其注冊。有的商標注冊雖未歪曲非遺內涵,如將“阿詩瑪”注冊在香煙上,但根據商標法中的“聯想理論”(4)聯想理論,即認為商標之所以能夠區分商品來源,是因為商標經過長期使用會與特定的商品或服務建立固定聯結,消費者一看到某一商標,就會聯想到特定的商品或服務。,該商標注冊后經過長期使用可能會使消費者將“阿詩瑪”與香煙形成固定聯系,而淡化其文化內涵,(5)有些上年紀的抽煙者提起“阿詩瑪”可能首先想到的會是香煙,而非那個不屈不撓同強權勢力作斗爭的姑娘阿詩瑪,因為“阿詩瑪”早在1982年就被玉溪卷煙廠在34類香煙上注冊了商標且長期使用。這種聯想一旦建立將很可能沖淡人們對撒尼民間故事“阿詩瑪”的印象。也會對非遺造成侵害。因此外部人注冊非遺商標的數據就能夠從反面反映非遺商標保護的狀況。其二是從內部人主動注冊非遺商標,并在非遺商標的保護之下進行非遺項目開發以促進非遺傳承角度而言的,這種含義的保護可稱之為“主動保護”。由于商標權的市場屬性,內部人注冊非遺商標必然意味著非遺的市場開發,因此這一含義與非遺的生產性保護緊密相關。我們知道,所謂非遺的生產性保護即通過非遺的市場開發獲取經濟收益,將“文化資源”轉化為“文化效益”,進而獲得“文化傳承”的動力和能力,也就實現了非遺保護,加入了非遺商標的生產性保護還具有額外的兩種價值:一是排除外部人搶注,保護非遺內涵;二是創造非遺項目文化品牌,在充分保護其文化價值基礎上實現品牌效益,更好地傳承非遺。“銅梁火龍”商標的注冊以及“南京云錦”證明商標的成功運營就是典型事例。美國俄克拉荷馬州喬克托人注冊的“Choctaw Defense Trademark”很好的保證了其產品的高質量和良好的聲譽。(6)See Brian Zark.Use of Native American Tribal Names as Marks. American Indian Law Journal.Vol.3 : Iss.2 2015.故內部人申請和注冊非遺商標的數據就能夠從正面反映非遺商標保護的狀況。
綜上,正是非遺商標這種特殊類型的商標將非遺與商標保護緊密聯系起來。對非遺的商標保護而言,不論是被動保護還是主動保護,都能夠通過申請和注冊非遺商標的數據予以體現。基于此,筆者擬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從非遺商標申請與注冊的情況,對非遺的商標保護作一系統化的數據統計與分析,以彌補目前各種點式報道、分析、研究不足以展示全貌的缺陷,更期待發現一些規律性問題并提出對策建議。
二、研究方案和實施步驟
該研究的總體方案是,以國家級非遺項目為對象,在中國商標網(7)中國商標局對外公布商標申請與注冊情況的官網,網址:http://sbj.cnipa.gov.cn/。進行商標檢索,從檢索結果中提取非遺商標申請與注冊的有效信息并進行數據統計。在統計結果基礎上,尋找規律性問題并提出相應的意見和建議,進行對策研究。
具體實施步驟如下:
第一步,確定非遺商標檢索對象。基于工作量、可行性等方面考慮,本次研究確定以國家級非遺項目為檢索對象,即以國務院在2006年、2008年、2011年和2014年公布的四批國家級非遺項目為準。(8)參見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博物館,網址:http://www.ihchina.cn/。
第二步,確定非遺商標檢索關鍵詞。關鍵詞選取以非遺項目名稱為藍本,以簡潔、有效、靈活為基本原則,簡潔是指關鍵詞盡可能以非遺名稱中最簡單的詞匯或詞匯組合為準;有效是指關鍵詞要保證非遺項目的基本內涵,在簡潔的基礎上能突出其獨特性,否則檢索出的條目將可能包含眾多無效選項;靈活是指有時可能需經過試錯來確定關鍵詞,經過使用不同關鍵詞進行比較,以確定最合適關鍵詞。
第三步,非遺商標檢索和數據提取。在中國商標網檢索窗口選擇“商標綜合查詢”,以上一步確定的關鍵詞進行檢索,對檢索結果進行數據采集。采集其中有注冊申請的數據,包括申請人名稱和地址、申請年份、尼斯分類、商品/服務、商標狀態、商標類型、商標標識等信息,同時結合非遺項目類別、文化內涵和特點、申報地區和保護單位,確定9項統計指標,并對各項統計指標賦值和記錄(統計指標及設計指標的意義或目標見表1)。
第四步,非遺商標數據統計、挖掘和問題分析。對各項統計指標單獨或結合進行數據統計和挖掘,形成統計圖表,發現問題和規律。
第五步,非遺商標保護對策建議。在上述統計結果和問題發現基礎上,結合商標法相關規定針對性地提出對策建議。

表1 統計指標
三、非遺商標保護運行實踐與問題
(一)數據總體情況說明
首先,涉及國家級非遺項目的數量。國務院發布的四批非遺項目共1372項,3145個子項。但子項之間多有重復,如“梁祝傳說”就有6個子項,商標檢索時這些子項共用一個關鍵詞。而一個大項往往又包含若干不同關鍵詞,如“格薩(斯)爾”就可提取兩個關鍵詞,均需檢索。故最終確定檢索項目數2477項。其次,在2477項檢索項目中,有1749條檢索結果為0,即這些檢索項無商標申請。剩余728項檢索項均至少有1件商標申請存在,共檢索出10374條商標申請數據。故本次研究最終得到的有效檢索數據為12123條,其中 10374條數據為有申請數據,另外1749條為無申請數據。本文接下來的數據統計與分析即從以上數據中產生,具體指標數據體現在下文的各統計圖表中。
(二)非遺項目商標化總體情況——當前態勢和未來趨勢

就非遺項目商標化的當前態勢和未來趨勢而言,首先可通過非遺項目是否有商標申請指標觀察。從圖1非遺項目商標轉化的數量和占比看,目前非遺項目商標化率還比較低。但從728項有申請的項目中就已產生10374項注冊申請,說明非遺商標產出量很高。筆者在檢索中也發現,許多申請人在申請非遺商標時往往是多類申請甚至全類申請。另外,從非遺商標申請年度變化趨勢圖(圖2)可見,非遺商標申請量在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一直為個位數,到90年代中后期也不過平均幾十件,而進入21世紀后每年都至少有幾百件,2017、2018年更是陡增至1244件和1401件(9)2019年數據非全年數據。。可見非遺商標申請量在有記錄的40年中呈現出一種在波動中逐步走高的趨勢。從上述數據可合理預測,未來非遺項目商標化空間十分巨大,非遺商標保護問題和壓力可能驟增,非遺商標保護之路還很漫長。


其次,從注冊狀態指標看(見圖3),在10374件非遺商標申請中,注冊成功6096件,注冊成功率58.8%,這一數據與我國商標注冊成功率的平均數值相比基本一致。(10)由于商標申請與審查的跨年度性,并沒有官方的商標注冊年度成功率數據。在此可以2017年的一個官方數據為對照,即2013年到2017年5年間的平均注冊成功率55%為對照。該數據參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商標評審委員會編著《中國商標品牌戰略年度發展報告(2017)》,http://sbj.cnipa.gov.cn/ sbtj/201805/t20180510_274101.html,訪問日期:2020年2月21日。考慮到非遺項目名稱的歷史傳承因素,社會知曉度較高,在商標化過程中往往會遭遇商標法上“顯著性”條款的限制,因此58.8%的注冊成功率還是遠超筆者的預期。

最后,從非遺商標申請主體構成(見圖4)看,個人、企業、協會、政府或事業單位這4類主體中,企業以7103件(占比68.5%)占據首位,其次為個人2192件(占比21.1%),協會295件(占比2.8%),政府或事業單位784件(占比7.6%)。考慮到非遺群體性特征,對非遺商標保護來說,協會、政府或事業單位作為主體申請非遺商標是我們所期望的,因為他們申請集體或證明商標的可能性更大,更契合和兼容非遺的群體性,且集體和證明商標屬于內部人申請的可能性也更大。表2數據顯示,本次研究檢索到的所有129件集體和證明商標均屬該兩類主體申請,個人、企業申請數為0,且無一例外均為內部人申請,的確證實了我們的推測。但從圖4數據來看,后兩類主體申請量占比明顯過低,前兩類主體占比極高,說明非遺商標目前的申請更具私人性、分散性,由協會、政府、事業單位統一組織非遺商標保護亟待加強。

表2 集體商標、證明商標的申請類別和申請主體構成
(三)非遺商標的主動和被動保護情況
前文述及,非遺商標的主動和被動保護可以從正、反兩面反映非遺商標保護的整體情況。而能夠反映這一情況的關鍵統計指標就是非遺商標申請人類別。下面將立基于這一關鍵指標,并結合其它指標對非遺商標保護整體情況做一統計與分析。

首先,從圖5內、外部人申請情況看,在10374件商標申請中,內部人申請為5185件,外部人為5189件,兩者幾乎相等。而兩者各自成功量和成功率數據也幾乎相同。以上數據首先可以說明,非遺的商標侵害問題確實相當嚴重,有50%以上的非遺商標均為外部人搶注,這與我們平時從公開媒體報道中得到的直接感受是相符的。(11)關于非遺商標搶注的報道或論文很多,多屬具體事例的點式報道。可參見管育鷹《“刀郎”現象折射出的民間文藝保護問題》,《中華商標》2005年第11期。劉亞、邊惠淀《梅村二胡商標保護戰》,《方圓》2016年第8期。李士林《論南音的商標法保護》,《民族藝術研究》2013年第6期。李明思《水書商標爭論凸顯民族文化保護之重》,《法制日報》2007年5月24日第4版等。但同時也必須注意到,非遺商標的主動保護情況也并不很糟糕,因為接近50%的非遺商標申請與注冊是內部人所為,說明內部人通過商標保護非遺項目的意識和行動能力還是較強的,值得肯定。

其次,從非遺商標尼斯分類(見圖6)來看。非遺商標申請在第33類(酒類)數量最多,高達1088件,在申請數排名前10位的尼斯分類中,除第41類(教育、培訓、娛樂、文體活動697件)與非遺內涵關聯較強外,其它大多都與吃(29類動物類食品479件、30類植物類食品691件)、喝(32類飲料328件、33類)、穿(25類服裝383件)、玩兒(39類中的旅游安排292件、43類食物和飲料服務444件)、商業推廣(35類686件)強相關,許多注冊與非遺內涵毫不相關。這種情況不僅出現在外部人申請,許多內部人申請也盡力向不相關但商業熱點領域的商品上靠,如將“阿詩瑪故鄉之禮”指定在29類的肉、火腿等商品上。甚至有許多前文所述的貶損類申請,如將“阿詩瑪”“董永”“女書” “穆桂英”“牛郎織女”注冊在避孕套或吸奶器上,將“穆桂英”“十八般武藝”注冊在避孕套、性玩具、性愛娃娃或潤滑劑上,且有注冊成功例。再如將“少林功夫”注冊在酒類或直接注冊“少林功夫酒”。(12)有可能對宗教信仰或宗教感情產生不良影響。檢索過程中還發現有欺騙之嫌的申請,如“梁祝之鄉” “吳歌之鄉”“楊家將嫡傳”“魯班傳人”等。還有許多注冊明顯為代理機構注冊,如“陶朱公”“阿里郎”等項目中的某些申請,這是目前商標法所禁止的。還有某一主體聚焦某一類非遺項目的申請,如某公司申請了多個傳統療法的商標,有囤積嫌疑,可能構成商標法上的惡意注冊。總之目前非遺商標申請與注冊可謂亂象頗多。為更好地考察這一情況,可以再引入相關性指標(圖7),可見在10374件非遺商標申請中,只有2283件屬于強相關,占比22.0%,1610件為一定程度相關,占比15.5%,而不相關的則高達6481件,占比62.5%。以上數據足以說明,非遺商標申請中存在太多與非遺內涵不相關的申請,它們可能淡化非遺內涵。

最后,將申請人類別與相關性指標聯系,可發現內部人、外部人申請的非遺商標在強相關、一定程度相關和不相關的情況下各自的數量和占比(見圖8)。數據顯示,在所有強相關的2283件非遺商標中,內部人申請為1453件,占比達63.6%,外部人申請830件,僅占36.4%。而隨著相關性的逐漸減弱,內部人申請占比也逐漸降低,由強相關狀態下的63.6%逐漸降為49.9%和45.2%。反過來外部人申請占比則隨相關性的減弱而逐漸增強,從強相關狀態下的36.4%逐漸增加到50.1%和54.8%。該變化規律直觀地反映了內、外部人在申請非遺商標時的不同側重。內部人申請顯然更注重商標與非遺內涵的契合性,更多出于保護非遺并對非遺開發的需求。而外部人申請則不太注重這點。

(四)非遺商標主動保護中的障礙因素考察
設定該項考察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理論研究和司法實務中兩個典型問題的思考。一是非遺商標“顯著性”問題。由于非遺商標容易被認定為通用名稱,尤其是其被指定在與非遺內涵相近的商品或服務上時。2016年“湯瓶八診”案(13)參見(2016)京行終1479號行政判決書,涉案商標被認定為不具有顯著性,最終被無效。和2009年“魯錦”案(14)參見(2009)魯民三終字第34號民事判決書,認定“魯錦”為通用名稱,該案后來被最高人民法院認定為指導案例。又加深了這種認識。因為內部人申請非遺商標更傾向于指定在與非遺內涵相近的商品或服務上,但這樣就加大了其被認定為“缺乏顯著性”的可能,從而更難獲得注冊。反過來外部人搶注的非遺商標更傾向于指定在不相關的商品或服務上,反而更可能獲得注冊。(15)正如學者胡世恩基于“湯瓶八診”案的評價:“這似乎得出了一個悖論: 被認定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就證明“湯瓶八診”是個通用名稱,既然是通用名稱,就無法獲得商標專有權保護。”參見胡世恩《回族傳統醫藥“湯瓶八診”商標系列訴訟案的法文化反思》,《回族研究》2016年第2期。典型案例畢竟是個別性的,那么針對該問題實踐中究竟是什么情況?本文的定量分析將有助于該事實的發現。二是關于集體商標和證明商標在非遺保護中的適用問題。由于大多數非遺項目的群體性特征,導致其所有者難以確定,一直以來這都是制約非遺知識產權保護的一個重大阻礙因素。而商標法中集體和證明商標可兼容群體性主體的特點使其成為學界寄予厚望的一種非遺知識產權保護解決方案。那么在非遺商標保護實踐中這兩種商標的適用情況如何?是否真正體現了其制度優勢,發揮了其應有的制度價值?這些也依賴于定量分析的展開。
首先,關于顯著性問題,我們將相關性指標與注冊狀態指標結合形成圖9,觀察三種相關性狀態下非遺商標注冊成功率。發現從強相關到一定程度相關時,其注冊成功率從46.5%小幅上升到47.4%,而到不相關狀態時則大幅上升到65.9%。說明當非遺商標指定商品與服務與非遺內涵強相關時注冊成功率明顯較低,而不相關時注冊成功率顯著提高。由于內部人申請更側重強相關商標,因此顯著性對內部人推行非遺商標保護帶來的障礙確實存在。不過同時也發現,即使強相關時也還是有46.5%的注冊成功率,說明顯著性問題對非遺商標申請的阻礙只是部分程度上的。

關于顯著性,筆者在檢索過程中發現的另一個問題倒頗值得關注,即非遺商標顯著性判斷標準問題。這個問題不能在圖表數據中體現出來,不過檢索過程中有眾多檢索例可以說明。比如同樣為民俗類項目,且指定商品或服務也相同或類似,“九華立春祭”“都江堰放水節”“馬街書會”“那達慕”“刀郎麥西熱甫”等諸多項目未獲注冊,而“秦淮燈會”“桃林坪花臉社火”“胡集書會”等卻注冊成功。傳統美術類項目“朱仙鎮木板年畫”獲得注冊,而“楊柳青年畫”“武強年畫”卻未獲注冊。民間文學類項目“汗青格勒”注冊成功,而“康巴拉伊”“彝族克智”則未成功。傳統音樂類項目“崖州民歌”“南音”“川江號子”注冊成功,但“侗族大歌”“薅草鑼鼓”則未成功。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這說明,關于非遺商標顯著性的判斷標準目前并不統一。

其次,關于集體商標和證明商標在非遺商標保護中的適用問題。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在所有檢索到的集體和證明商標中,全都屬于內部人申請和協會、政府或事業單位申請(見表2),說明該兩種商標確實顯示了其在非遺商標保護中應有的角色、地位和優勢。但從申請量和占比來看情況并不樂觀。圖10顯示了非遺商標申請中商標類型的情況。從圖中可見,一般商標共10245件,占比98.8%。而集體商標僅15件,(16)檢索發現,注冊成功的集體商標僅有5件:萬榮笑話(41類)、沐川草龍(20類)、黃梅挑花(24和26類)、萬載花炮(13類)。證明商標也只有114件,兩者加起來也僅占申請總量的1.2%,與一般商標相比根本不在一個數量級。看來該兩種被寄予厚望的商標在非遺商標保護中的價值并未充分體現。最后,從該兩種商標注冊成功率看,集體商標只有33.3%的成功率,證明商標情況稍好,成功率達到67.5%。總體來看,內部人還不太擅長利用這兩種商標實施非遺保護,尤其集體商標問題可能更多。
四、非遺商標保護問題分析與對策建議
(一)問題分析
從定量分析結果看,我國非遺商標保護中存在諸多問題。這些問題雖看似分散和混亂,但總體而言均可歸結到“權利人缺位”和“制度缺位”兩個方面。
首先關于權利人缺位。檢索過程中發現,非遺商標注冊中異議率并不高,許多申請均順利注冊,甚至一些明顯的貶損性、欺騙性、惡意申請也能成功,說明作為權利人的內部人在實踐中維權行動不足。與此相比,美國印第安人在“華盛頓紅皮案”和“齊亞太陽符號案”中窮盡一切途徑保護部落標志的行為彰顯了權利人積極的態度和行動。(17)印第安部落為了保護傳統符號,不僅訴諸商標法,還涉及美國憲法,甚至尋求政治途徑解決問題。他們的努力也直接促成了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NATI數據庫(18)即“美國土著部落標記數據庫”(The Native American Tribal Insignia Database)。由各土著印第安部落將他們各自的部落標記上報于專利商標局組成數據庫,其他主體在注冊商標時如果使用該數據庫中的符號將不被授權。See:Bernholz, Charles D., Linda G.Novotny, and Ana L.Gomez."American Indians and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The Native American Tribal Insignia Databas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6.1 (2009): pp.180-185.的建立。不唯美國,2019年新西蘭毛利人委員會(Maori Council)還針對新西蘭航空公司注冊“Kia Ora”商標的行為提起異議,認為該商標的注冊涉及竊取毛利人的文化資產。(19)《新西蘭航空注冊“Kia Ora”為商標,引發毛利人強烈抵制!》https://www.logonews.cn/air-new-zealand-threatened-with-maori-boycott-over-bid-to-trademark-kia-ora-logo.html,訪問時間:2020年4月15日。權利人不斷的聲索在非遺的商標保護中具有重要作用,這些聲音可能構成制度變革的動力。
其次關于制度缺位。目前非遺符號商標化利用的無序根本原因在于非遺符號利用權限不明。誰擁有非遺符號?誰可以利用以及怎樣利用?均缺乏專門制度規定。《商標法》僅有一些可解釋性適用的條款。因此任何主體的任何涉及非遺商標的申請,商標局往往只是像對待其他商標申請一樣予以審查,很少專門從非遺保護的視角看待,同時商標局也缺乏判斷某一標志是否屬于非遺符號或是否包含非遺符號的信息,造成非遺符號商標利用的無序。而在許多國家,針對傳統文化符號的商標利用早已有制度關注。美國商標法(即蘭哈姆法The Lanham Act)中的“誹謗性或貶損性商標”(Scandalous or Disparaging Marks)(20)Lanham Act,15 U.S.C.§1052(a),以及USPTO的NATI數據庫制度,構建起較為完整的排除機制。《新西蘭商標法》第17條(1)(c)規定的“冒犯性商標”(Offensive Trademarks)制度專門排除了商標注冊對毛利人族群符號的利用。2000年巴拿馬第20號法律賦予了原住民對其文化遺產集體性質的絕對控制權。國外立法雖不能說完善,但提供了非遺符號商標利用的基本制度安排,對規制非遺符號的濫用非常關鍵。
(二)對策建議
1. 積極利用現行商標法制度資源排除外部人搶注
事實上,僅就排除機制而言,我國現行商標法就提供了豐富的實體和程序條款可供利用。實體如第四條“惡意注冊禁止”條款,第十條第一款中的“民族歧視性”“欺騙性”“不道德性和不良影響性”條款,第十一條“缺乏顯著性”條款,第十九條的“禁止代理機構注冊”條款,第三十二條的“在先權利”條款等。程序條款如第三十三條的“商標異議”條款、第四十四條的“無效宣告”條款。依據上述規定均可就非遺商標的搶注進行阻止。目前實踐中的問題在于,在非遺保護這一文化系統和商標局商標審查這一法律系統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如果內部人不啟動異議或無效宣告程序,商標審查員以及進入司法程序后的法官不可能對非遺事項知之甚詳,這樣商標法現行的排除機制就可能無法發揮應有的效用。針對目前內部人雖數量眾多但往往意識不到,或者雖有意識但行動能力、財力不足的情況,應該由非遺保護與管理部門引導、鼓勵和支持相關主體啟動異議或無效宣告程序,必要時亦可由保護與管理部門自己啟動這些程序,排除外部人搶注。
2.注重非遺商標標識設計的顯著性問題
商標審查中標識本身的要素構成對判斷顯著性以及是否與他人商標相同或相似至關重要。數據表明,當非遺商標標識為精心設計的圖文商標時,其注冊成功率高于純文字商標(圖11)。說明非遺商標標識設計是克服顯著性問題的有效路徑。如何合理設計非遺商標標識?筆者以為,比起簡單、拙劣甚至粗鄙的“拿來主義”式的非遺符號利用模式,在對非遺符號所代表的文化內涵深刻理解基礎上再融入現代元素而精心創作的商標標識,才不僅符合商標法要求的顯著性,而且有更強大的生命力。不僅有利于阻止低成本、低質量、不誠信的商標濫注行為,而且有利于產出民族精品文化品牌,這才真正契合我國商標品牌戰略所要求的高質量發展內涵。

3.充分發揮證明商標、集體商標優勢
證明商標、集體商標由于本身兼容群體性主體的特殊性,對非遺的商標保護而言的確具有難得的優勢。美國早在1935年就通過了《印第安藝術與手工藝品法案》(IACA),通過“印第安制作”(Indian-made)標記對手工藝品進行保護,并對虛假標注行為予以禁止。澳大利亞通過“真實性證明”(Authenticity Certification)標記對土著居民以及托雷斯海峽島民的文化及經濟權益進行保護。在新西蘭奧特亞羅瓦(Aotearoa),毛利人注冊的“ToiIho”證明商標不僅是其產品真實性的表征,更是高質量的保證。在印度尼西亞,集體商標對傳統蠟染產業發展的積極效用也受到了高度肯定。(21)Agus Sardjono.Indonesian Experience In Dealing With Trademark Law: Case Study Of Batik SMEs.INDONESIA Law Review.Year 3 Vol.3 2013另外,由于該兩種商標注冊與管理的特殊性,是外部人幾乎不愿也不敢染指的領域,上述表2的數據也證實了這點。因此對內部人而言是一條難得的路徑,不僅可以解決非遺群體性難題,而且能夠擺脫外部人競爭。但目前極低的申請量顯然不能充分發揮其優勢和功能。因為該兩種商標在申請和注冊中特殊的法律要件,除了要滿足一般商標要求的顯著性等要件外,還需滿足有組織管理能力的主體、詳細具體的管理規則等要件,從而增加了商標申請的難度。鑒于原住民數量眾多、地域分散,缺乏組織和管理,非遺保護與管理部門的組織和引導工作顯得十分必要和關鍵。
4.建立“非遺符號數據庫”,變“事后排除機制”為“事前排除機制”
長期來看,未來非遺項目商標化空間巨大,極有可能引發更多的問題和糾紛,因此有必要研究和構建一套統一處理機制,以統一解決問題。筆者以為,可借鑒USPTO的NATI數據庫制度,構建一套非遺符號數據庫,作為商標審查時的禁用符號庫,除符合條件的非遺歸屬地的協會、政府文化部門、相關事業單位申請證明商標、集體商標使用這些符號外,一律不予授權。這一制度可將目前的“事后排除機制”變更為“事前排除機制”,這樣非遺商標的搶注、侵害、顯著性判斷等問題都將迎刃而解。唯一留下的出口將促使非遺商標均統一指向證明和集體商標,以充分發揮這兩種商標的優勢和功能,為非遺項目的生產性保護與開發提供制度保障。
就建立數據庫的法律依據而言,最好是在《商標法》第十條第一款中增設一項“與傳統文化符號相同或相近似的標志”作為“不得作為商標使用”的情形。當然修法難度可能較大,目前來說可將現行《商標法》第十條第一款第(八)項的“不良影響條款”作為設立該數據庫的法律依據,并在《商標審查與審理標準》上篇第一部分第九項中增加一條,即“可能對傳統文化內涵產生不良影響的”,作為商標審查時的直接依據。而集體商標、證明商標對該條款的免疫適用則可解釋為不屬于不良影響的情形,并將這種情形在《商標審查與審理標準》第七部分中特別規定出來。這樣,在《商標法》修訂和數據庫建立的基礎上,非遺商標排除機制就有了基本的制度框架。
結 語
本文的實證研究無疑為我們展示了非遺商標保護一個相對完整的圖畫,有助于發現該問題的種種實踐面相,并有的放矢去解決。囿于篇幅,研究還存在一些不足,如用于檢索的非遺項目范圍只限于國家級,非遺符號僅及于非遺名稱,因此更全面的實證研究有待進一步開展。在研究中筆者發現,其實非遺商標保護諸多問題的根本在于文化與法律系統的系統際沖突,因此該問題的解決需要兩個系統間的溝通和改變。商標法應該關照到非遺保護的特殊性而創新制度供給,非遺界也應加深對商標法的了解以尋求合宜之策。同樣地,兩個系統的學術研究也應加強交流,互通有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