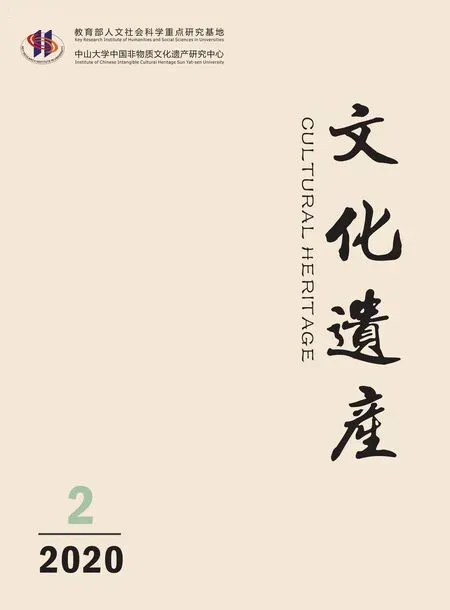清代宮廷儀典承應戲結構研究*
熊 靜
一
近年來,隨著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館等主要清代宮廷戲曲文獻收藏機構先后將館藏文獻刊布,昇平署檔案與戲本的面貌日益為世人所知。據學者統計,僅戲本一項,故宮博物院就藏有11491冊,臺北故宮博物院、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國家圖書館、首都圖書館等其他藏本較多的單位加起來的收藏也有2000余種(1)李士娟:《靜日生煙舞升平》,《人民日報》2016年12月6日第24版。,是存留至今的,我國古代戲曲文獻中規模最大的一批。
對于這批文獻的史料價值,率先披露昇平署戲曲檔案的民國著名學者朱希祖早有定論:“略謂近百年戲曲之流變,名伶之遞代,以及宮廷起居之大略,朝賀封冊婚喪之大典,皆可于此征之。”(2)朱希祖:《整理昇平署檔案記》,《燕京學報》1931年第10期。面對這樣一座幾乎取之不竭的戲曲文獻寶庫,學者興奮之情不言而喻,近十年來,宮廷戲曲文獻和演劇研究幾成顯學,涌現了大量優秀的成果,斯賴文獻披露之功。
然而,不論是文本研究,還是演出研究,論者多重視對清宮戲曲檔案與曲本史料價值的挖掘,以戲證史,以文獻見制度變遷,而對宮廷戲本的藝術價值則向來評價不高,至多有所保留地從舞美、戲臺等技術的角度給予肯定。其濫觴者如張庚、郭漢城先生主編的《中國戲曲通史》,在介紹了宮廷演劇的概況、戲臺、舞臺設備與彩燈砌末、服裝與化妝后,對其藝術價值如是評論:“(宮廷節令戲)媚神頌圣、征瑞稱祥而已,極少戲劇性。”(3)張庚、郭漢城主編:《中國戲曲通史》,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7年,第982頁。由于《通史》在戲曲研究界權威經典的地位,上述觀點幾乎成為人們對清宮戲曲的定論。
筆者自2007年開始接觸清宮戲本,十余年的閱讀、研究之余,也頗能理解《通史》中的觀點。如果僅從文本的角度來看,大部分宮廷承應短劇(折子戲除外),確實十分乏味,讀來“千人一面”,內容也可稱“媚上不堪”。然而,這類戲本在清宮戲本中占據了相當的比例,幾乎與明清傳奇折子戲、宮廷連臺大戲“鼎足而三”,考慮到這類劇本多為一至八出的短劇,其種類之多就令人嘆為觀止了。對此,筆者不禁產生了一個疑問,清朝是一個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演戲編劇想來非其所長,但從目前已經披露的史料來看,幾乎是入關不久,內廷便開始了戲曲演出,至康熙時期已有南府的建制,可以組織如萬壽盛典那樣大規模的戲曲承應了(4)清朝自關外時期,便有戲曲演出的記載。入關后,順治帝曾命教坊演出著名劇作家尤侗的《讀離騷》等。至康熙二十五年左右,檔案中即已出現南府的建制。具體情況可參看朱家溍、丁汝芹《清代內廷演劇始末考》,北京:中國書店2007年。,那么,支撐演出的劇本從何而來?清宮又是如何在短時間內積累起數量如此龐大的承應戲本的?如果說,少量的相似還可以說是巧合,如此大規模的劇本從內容到形式都體現了驚人的雷同,達到“千人一面”的程度,這是否說明了它們在劇作結構上具有一定的內在關聯性呢?我們常說清延明制,那么,清代宮廷儀典戲體現的這些特征,是否從前代宮廷演劇中汲取了養分?這是本文希望解決的問題。
二
在正式展開討論之前,有必要首先對本文的研究對象做出界定,也就是題目中的——儀典承應戲。宮中演劇,慣被稱為“戲曲承應”。從詞源上考察,“承應”一詞,典出《晉書》卷十七“律歷中”:“夏殷承運,周氏應期”(5)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497頁。,本意為承接而起。至南宋時,已引申為“妓女、藝人應宮廷或官府之召表演侍奉”的特稱(6)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年,第777頁。。也就是說,所有清宮戲本都可被稱為“承應戲”。就目前已披露的資料來看,清宮承應戲大致可分為四類:儀典戲;清宮連臺大戲;明清傳奇本戲、折子戲;亂彈本戲、折子戲。后兩類大多來源于民間劇壇,雖然會做一些適應宮廷演出的改編,但從總體內容與結構來看,仍與民間演出本保持一致。前兩類大部分為宮中創編,又有學者將連臺大戲稱為“承應史劇”(7)吳曉鈴:《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善本劇曲目錄》,《圖書季刊》1940年第3期。,頗能說明其性質,即以歷史事件為藍本的長篇傳奇(8)清末又有根據昆弋本戲改編的亂彈本戲。。剩下的那些廣泛上演于節令、慶壽、宴饗等場合的短劇,被學者命名為“儀典戲”(9)丁汝芹:《清代內廷演劇史話》,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第34-35頁。,取其主要用于朝堂宴會演出之義。我們在這篇文章中討論承應戲的結構,主要指的就是這類儀典承應戲。
儀典戲的概念,最早由丁汝芹在《清代內廷演戲史話》一書中提出(10)丁汝芹:《清代內廷演戲史話》,第34-65頁。,主要指那些內容上歌功頌德,形式上以舞蹈、或者大場面戲為主,專為宮廷演出所用的戲本。具體類別包括:節令戲、壽戲、慶典戲、宴戲等,人們熟悉的“月令承應”“九九大慶”“法宮雅奏”均屬此列。由于這類戲最能代表宮廷演出的特征,很早便受到了學者的關注。民國時期,傅惜華的系列文章:《清代內廷之開場、團場劇》《內廷除夕之承應戲——如愿迎新》《清宮之月令承應戲》《談〈天香慶節〉》《記乾隆抄本〈太平祥瑞〉雜劇》等;張笑俠的《清宮壽劇〈吉星葉慶〉》等,基本涉及到了儀典戲的各種類型,其研究視角主要在于文獻披露。
其后數十年,這一研究傳統被較好地繼承下來,儀典戲各個類型均有較為成熟的個案研究出現。進呈劇方面,周妙中考證了蔣士銓所作承應劇《西江祝嘏》的創作年代(11)周妙中:《蔣士銓和他的十六種戲曲》,《上饒師專學報》(社科版)1985年第3期。。壽戲方面,學者對于清代皇帝和太后壽誕演出專用戲本——《九九大慶》最感興趣。李鼎霞撰文披露了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九九大慶》的內容和版本信息(12)李鼎霞:《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九九大慶〉全本簡介》,白化文等編:《周紹良先生欣開九秩慶壽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475-491頁。,在此基礎上學者對北大本《九九大慶》的創作年代、劇本形制進行了探討(13)熊靜:《清代內府“九九大慶”戲研究——以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九九大慶〉為例》,日本東北大學《東北亞細亞研究》第16號,2012年3月。。節令戲方面,中秋承應戲《天香慶節》受到的關注最多,除了前述傅惜華的文章,1941年張聊公發表《觀天香慶節》,詳細地記載了著名京劇演員王瑤卿主演的《天香慶節》的演員表、演出特色等(14)張聊公:《觀天香慶節記》,《聽歌想影錄》,天津:天津書局1941年,第97-98頁;俠公劇話:《王瑤青昔排天香慶節》,《立言畫刊》第314期,1944年。。王在清末曾入選內廷供奉,他排演的《天香慶節》,據云為根據內府本改編者。此后,臺灣成功大學黃雍婷的《清代宮廷中秋承應戲曲研究》(2010),日本學者磯部祐子《略論節戲中的月令承應戲》(2013)、《清代宮廷戲曲〈天香慶節〉考述》(2014)、《宮廷本〈天香慶節〉的特點以及對民間戲曲的影響》(2018),在文獻挖掘深度和立論準確性上,都在前人基礎上有所超越。此外,戴云從燕九承應戲《慶樂長春》中記載的民俗史料出發,還原了清代北京地區賽社場景,以戲證史,將清代中前期北京周邊地區燕九賽社的生活場景形象地展現在讀者面前,其研究方法頗足借鑒(15)戴云:《舊京賽社一瞥——燕九承應戲〈慶樂長春〉中的賽社場景描寫》,《中華藝術論叢》2007年第1期。。宴戲是在宮廷宴饗演出時使用的戲本,最著名的當屬乾隆晚期為英使朝貢所編的《四海升平》,葉曉青在《乾隆為馬戛爾尼來訪而編的朝貢戲》中詳細介紹了乾隆本《四海升平》的主要內容和編撰緣起,文末附錄乾隆本文本(16)葉曉青:《乾隆為馬戛爾尼來訪而編的朝貢戲》,《二十一世紀》2008年第2期。。《〈四海升平〉考》則在葉文基礎上,對現存《四海升平》的各種版本進行了比勘,梳理了其版本序列。此外,帝王行獵后宴會上演出的《行圍得瑞》(17)李躍忠:《清代宮廷承應戲〈行圍得瑞〉的文化功能簡論》,《中國古代小說戲劇研究叢刊》 2016年第1期。,開場喜慶劇《開筵稱慶》《賀節詼諧》(18)李躍忠:《滿清宮廷承應喜慶劇〈開筵稱慶〉〈賀節詼諧〉研究》,《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15年第4期。,以及篇幅較長的儀典承應劇《春臺葉慶》(19)史健男、劉鐵:《清代宮廷戲曲〈春臺葉慶〉考證》,《中國典籍與文化》2019年第1期。都曾得到學者的關注,使人們對于清宮宴戲承應形態認識地更加深入。
綜合研究方面,薛曉金、丁汝芹主編的《清宮節令戲》(2014),收錄了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館、首都圖書館收藏的昇平署節令戲94個,加以標點、注釋,排印出版,全部戲目按照承應節令編排,每類前撰有導言,極大地方便了普通讀者。羅燕的《清宮承應戲及其形態研究》(20)羅燕:《清代宮廷承應戲及其形態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從整體上討論了清宮儀典劇的來源、劇本形態等問題,從國家禮樂制度的角度分析了儀典承應戲呈現的共同特征。張瑩《清宮月令承應戲禮俗融合的文化意義》(2018)則從文化史的角度,討論了清宮儀典承應戲的價值。
前人研究為我們提供了扎實的文獻基礎和多元的分析角度,但梳理本領域的進展亦可發現,個案研究為其大宗,即使是宏觀角度的論述,也主要從清宮承應戲的文本特征、藝術價值、文化意蘊等角度展開,尚未有論者從儀典戲的內容特征和劇作結構的角度進行深入研究。目力所及,唯有民國著名戲曲史家齊如山在研究了家藏康熙年間內府承應劇抄本后,發現其中的幾段在內容和結構上與宋雜劇均有相似之處,據此提出“宮中承應戲的結構,可能是直接來于宋之雜劇,且可能還沒有多大的變動(21)齊如山:《齊如山回憶錄》,北京:新華書店1998年,第223頁。在回憶錄中,齊氏并謂,針對承應戲的問題,作《承應戲研究》一書,但此書筆者遍索未見,愿得之者教我。”。惜齊氏此文今已不傳。因此,仍有必要從內容和劇作結構的角度來對清代宮廷儀典承應戲的整體結構進行分析。
三
清宮儀典承應戲存世數量甚夥,僅就種類來說,遠遠超過內府曲本的其他類別。但其內容與結構方面的相似性極高,這為我們概括儀典戲的整體特征提供了可能。通過對現存儀典戲的整理分析,其特征表現為以下三點:
首先,以短劇為主,絕大部分為單出。多出戲長二至十六出不等,雖然情節先后相連,串演完整的故事,但其中的單出拆出單演亦無不可。比如《故宮珍本叢刊》第662冊《八佾舞虞庭》,卷端題“第十二出 八佾舞虞庭”;同冊《虹橋現大海》卷端題“第五出 虹橋現大海穩渡鯨波”,可見其本為長劇中的一出,后被拎出單獨演出。
其次,故事情節方面,圍繞頌圣的中心,多從仙佛故事、風土民情、瑞呈花舞等中選材。即昭梿所謂:“群仙神道、添籌錫禧,以及黃童白叟、含哺鼓腹者”(22)昭梿:《嘯亭雜錄》,何英芳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378頁。。
第三,演出場所、時地有明確的限制性。儀典戲是宮廷獨有的一類劇目,民間劇場演出,雖然也在開場上演吉祥戲目,但規模較小,主要用作暖場。儀典戲則已成為宮廷演出的典例,不僅規定開團場必須演出此類戲目,即使到了晚清,帝后嗜好皮黃,以昆弋腔為主的儀典戲仍然活躍在清宮戲曲舞臺上。
由于儀典戲具有上述特征,雖然其數量龐大,但內容和結構卻頗有共通之處。下面試以兩例來解析儀典戲的結構特征。
首先是一個單出戲的例子。《故宮珍本叢刊》第661冊《慶壽萬年》(23)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661冊128-130頁。,演圣主(皇帝)圣誕,南極壽星帶領群仙獻蟠桃祝壽之事。開場由南極壽星首先上場:
(扮壽仙執壽字,鶴童、鹿童執手卷、拐拄,作引南極壽星從仙樓上,仝唱)……恭逢當今圣主萬壽圣誕,正老人星呈祥獻瑞之時,因此宏開壽宇,晉祝皇都,統領諸壽仙,恭獻長生壽酒,九熟蟠桃,以隆慶典。現在分遣鶴童、鸞女,邀請瀛海洞府諸仙去了。你看蓬萊佳氣,上映丹霄,果然是熙朝嘉瑞也。
(東王公白)南極仙翁相召,一同前往……
(南極壽星白)恭逢當今圣主萬壽圣誕,恰喜蟠桃九熟,我等往度索山采取呈獻,叩祝神州,慶賞蟠桃大會,多少是好……
(南極壽星白)來此已是度索山,諸位仙真,看老人獻壽祝嘏者……
(南極壽星將拐拄、手卷作入地井,現大壽字科。內奏樂,扮眾壽星、壽仙各執壽字分上走式科,仝唱)……
(東方朔白)……
(南極壽星白)這也使得。你可進山采取蟠桃來……
(南極壽星白)東方子,你可將八寶云車載此蟠桃先往,我等隨后來也。
拋開具體情節,本劇的結構可被分解為:南極壽星出場引出獻壽由頭——群仙奉召同往摘取蟠桃——南極壽星串場、完成轉場——群仙歌舞獻壽——南極壽星致辭、收結全場。
再舉長劇一例。國家圖書館藏《九九大慶》(索書號:A03433),共九卷,每卷為一種,每種8、12出不等。其中,第一種《四靈效徵》(24)此劇第一出云“當今圣皇、圣后同月誕辰,當今十洲三島,洞天福地,仙真凡夫婦,齊眉成雙捉對者,同往神州慶祝”,且全劇“寧”字均不缺筆,筆者曾以清史核之,道光之前,帝后同月誕辰者惟嘉慶帝與其第二位皇后——孝和睿皇后,故推斷國圖本《九九大慶》為嘉慶萬壽承應戲。共十二出,出目如下:議祝遐齡、籌朝玉陛、元龜撮合、龍鳳交爭、扶仇幻相、識破原形、仙逐龍飛、祥開麟現、急援同人、強諧連理、四靈畢至、萬壽無疆。劇演:圣皇(皇帝)、圣后(皇后)同月誕辰,木公和金母商議以洞天福地真凡夫婦齊眉成雙捉對者同往神州慶祝。有云從子(黃龍)欲往獻壽,但因無配不能同往。先知老叟(烏龜)為其謀劃求娶九苞仙子(鳳凰)。仙子不從,黃龍強聘。雙方各尋幫手,連番大戰。其間,眾仙人、瑞獸紛紛登場,打斗場面熱烈,是本劇的主體部分。最后,木公金母前來制止雙方,同往神州獻瑞,獻萬壽無疆之舞,呈四靈獻瑞之像。
相比《慶壽萬年》,劇情不可謂不復雜,場面之熱鬧、出場人物之多也遠勝前劇。我們使用同樣的方法拆解劇情結構,其基本流程如下:
木公邀請金母商議為圣主、圣后祝壽事宜——金母提議以三界真凡夫婦同往獻壽——木公派神使召集符合要求的仙人——黃龍得知此信,欲往獻壽,因不符合條件,強求鳳凰仙子為配——鳳凰仙子不從,黃龍、鳳凰各尋助力、連番大戰——木公、金母前來調解群仙大戰——木公、金母率群仙來到萬壽山呈祥獻瑞——木公、金母致辭收結全場。
兩劇在情節容量上大相徑庭,但劇情結構卻驚人的相似,不管劇情如何展開,出場人物多或少,儀典戲的“套路”一以貫之。首先由“南極壽星”“木公、金母”這樣的角色出場,引出稱祝的由頭,然后展開歌舞、雜技、武打等表演,最后再由“南極壽星”等“總結發言”,表達稱頌之意,收結全場。不論劇本長度如何,儀典戲都保持了類似的結構,這應當是清宮能在短時間內積累起如此龐大數量的儀典戲本之內因所在。
四
結構上的相似性給創作帶來了便利,但是,清代宮廷戲曲演出幾乎是伴隨著清王朝建立同時開始的,期間并沒有給宮廷劇作家們留下充足的創作時間。而且,熟悉宮廷演劇的讀者應該已經感到,清宮儀典戲的內容與結構有一些“似曾相識”。我國古代宮廷演劇的傳統由來已久,但有完整劇本存留的,唯明清兩代,我們對清宮儀典戲結構的溯源就從明內府本開始。
明《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中“教坊編演”類目下的18個雜劇,屬于明代內府曲本。其一般套路,是在第一折或楔子中,由某一仙真召集群仙提出向人間帝王祝賀之事,接下來的兩到三折,演出一個完整的仙佛故事,末折呼應頭折,群仙畢集,呈祥獻瑞,表達稱頌之意。試舉一例說明。
脈望館本《賀升平群仙祝壽》,四折。演下方國母(太后)圣誕,南極大仙奉上帝之命召集群仙祝壽。上、下洞八仙、山神、柳樹精等各尋奇珍為祝壽之禮。最后,群仙齊集紫宸殿,在南極仙翁帶領下,呈祥獻瑞,恭祝圣壽。其劇本結構如下:頭折由南極仙翁首先上場,述慶賀情由——群仙依次出場商議以何種寶物獻壽——第二、三折演群仙尋寶、相約祝壽的過程,此時南極仙翁不再出場——第四折南極仙翁又首先出場:
(南極仙領仙童上,云)……貧道有一篇祝壽的致語,權為供獻。則等眾神仙來與國母祝壽。這早晚敢待來也……(南極仙云)四位仙長,您來了也。您有何祝壽的仙物也。(鐘離云)上仙,貧道有一金瓶蓮花權為供獻……
(按:以下情節為鐵拐李獻瑞煙葫蘆;韓湘子獻牡丹仙花;國舅獻笟篁金牌等寶物為祝壽之禮。南極仙在其中起到串場的作用,問答模式均如引文。)
(正末云)上仙,松、竹、梅花來了也。(南極仙云)你四個仙女祝圣母之壽者。(四仙女齊唱)【出隊子】……
(南極仙云)好、好、好,您祝罷壽,也擺在一壁,眾群仙都跪者。(眾跪科)(南極仙做念致語科,云)伏以孟春佳節,律應夾鐘,肇春萌復始之期,遇圣母遐齡之兆,群仙頓首,萬壽遙瞻。賴仁慈化育群黎,崇善事感通天地。禎祥佳集,宇宙康寧,萬邦稽首,同荷雨露之恩,士庶歡騰,共祝如天之壽。桑麻映日,皆因仁孝之誠,禾黍盈倉,仰賀慈恩之惠。人天共賀,海宇齊同,謹扮丹誠恭為獻頌:南極垂光耀九天,壽星高拱在華筵。臣民同獻長生福,敬祝千秋萬萬年。(25)《古本戲曲叢刊》四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58年版。下文脈望館本引文,均出自《古本戲曲叢刊》四集本。
南極仙翁在劇中的作用,與清宮儀典戲的“南極壽星”“木公金母”并無二致,發揮串聯全場的功能。其余17種明教坊編演雜劇,都有類似的角色,他們一般不是雜劇的主角——“正末/旦”,而是首先出場的“沖末”,扮演的角色多為“殿頭官”“南極星君”之類,其性質完全一致。
相比明內府本,清宮儀典戲的形態更加靈活,并不嚴格按照雜劇或傳奇的規制編寫,或長或短,全憑演出內容而定。但從劇本結構的角度,二者的相似性還是十分明顯的,不論是明內府本中的“沖末”,還是清宮儀典戲的漫天神佛,充當整部戲串場人的角色,其實都游離在核心劇情之外。如果將一場儀典戲的演出比作一臺晚會,這個串場的角色就類似于“主持人”,他并不直接參與劇情,但卻將不同的表演段落、先后出場的角色有機地串聯起來,引導整場演出按照既定方向進行。而同樣功能的角色,在中國戲劇史上并不陌生。
由于資料的匱乏,學界對于中國宮廷戲劇史的描述,大多至宋代才深入細節。《宋史》卷一四二《樂志十七》載宋代三大節教坊承應的過程,據其記載,宋代的宴饗演出,以盞為單位,大約從第六盞開始,以“樂工致辭”為標志,樂舞、雜劇演出開始(26)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348頁。,樂工以“致辭”“口號”的形式,在其間穿針引線,區分表演段落,引出新的節目。由于正史的記載側重于宮廷典儀,主要陳述的是宮廷演出的程序,對具體的演出內容著墨不多。《東京夢華錄》卷九“天寧節”(注:宋徽宗生日)“宰執親王宗室百官入內上壽”條,對皇帝壽宴演出程序和內容記述地更加詳細,整個宴會共持續九盞,從第四盞開始,演出進入主體部分,雜劇、隊舞紛紛上演(27)孟元老等:《東京夢華錄(外四種)》,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第52-55頁。。記載南宋制度的《武林舊事》卷一“圣節”“天基圣節排當樂次”條所錄增至“初坐”“再坐”等三十多盞(28)孟元老等:《東京夢華錄(外四種)》,第348-354頁。,但基本演出程序,兩宋并無差別。為了便于說明,我們將之簡化如下:
第四盞:參軍色念誦致語、口號→雜劇色和聲→參軍色再作語引導大曲舞出場
第五盞:參軍色念致語引導小兒隊出場→小兒隊隊首擎隊名牌→參軍色問小兒班首→小兒班首進口號、雜劇色和聲→小兒隊舞→小兒班首進致語、引導雜劇入場→雜劇畢,參軍色再作語,放小兒隊下場
第七盞:參軍色作語引導女童隊入場→女童隊首擎隊名牌→參軍色問女童隊班首→女童班首進口號→女童隊舞→女童班首進致語、引導雜劇入場→雜劇畢,參軍色再作語,放女童隊下場
完整的一場演出,按照參軍色→雜劇色→參軍色→小兒班首→參軍色→女童隊首→參軍色的出場順序依次進行。
“參軍色”可謂整場演出的靈魂人物,在演出過程中,參軍色通過念誦“致語”“口號”,起到了連綴演出,調度場面的作用。將參軍色比之明內府本的“沖末”,清宮儀典戲的“南極壽星”“木公金母”,至少在功能上是完全可以畫上等號的。
但是,問題隨之而來。宋教坊承應中,參軍色并不參與具體的演出,他只通過念誦“致語”起到串場的作用,小兒隊、女童隊首進獻致語,也是在其各自的演出結束后,并不屬于之前隊舞表演的一部分。而明清內府本中,承擔“參軍色”作用的角色,雖然出場不多,但都是劇中人無疑。因此,僅從形態上的相似性來說明二者之間的關系,說服力是不夠的。我們需要從宋教坊演出的內部,以及明清承應儀典戲的文本中尋找更多的證據。這時,“參軍色”串場的工具——“致語”,引起了我們的注意。
“致語”,或“樂工致辭”,又稱樂語,按照現代漢語的解釋,致語就是致辭的意思。宴會致辭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而在宮廷宴饗場合,“致語”與“樂”的關系密切,是“禮樂”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對“致語”的來源,明徐師曾《文體明辯序說》有比較系統的解釋(29)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羅根澤校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第169-170頁。。概言之,致語就是在宮廷筵宴時由樂工口誦,贊頌帝王美德、稱揚天下賓服之語。在結構上,分為致語和口號兩部分,致語文辭典雅,多為對偶文字,對仗排比工整。口號則為詩體,或七言,或四言(30)黃竹三:《“參軍色”與“致語”考》,《文藝研究》2000年第2期。。
前文已及,在宋代教坊演出中,“致語”是“參軍色”的串場詞,其內容除了引出后續表演的套話,主體是稱頌帝王功德之辭。此時,細心的讀者也許已經發現了,在前引脈望館本《賀升平群仙祝壽》的演出中,“致語”已經登場亮相了。無獨有偶,脈望館本《寶光殿天真祝萬壽》,演虛玄真人思凡下界,呂洞賓下凡點化之事,上述情節又以長生大帝召集群仙向“圣人(人間帝王)”祝壽串聯起來。至第四折時,主體劇情已經完結,群仙在長生大帝的帶領下,向人間圣主呈祥祝壽,壽星念完頌詞后,長生大帝云:“是好祝壽的致語也”,隨后念誦駢文口號。
本折與全劇的故事主線關聯不大,拎出單演亦無不可,但作為祝壽的內府本,又是全劇的旨歸所在。劇中,群仙祝壽已畢,壽星出場念誦的祝頌之詞,被明確標明為“致語”,形制上也遵循了致語的標準格式,由駢文和七言詩組合而成。可以作為明內府本承襲了宋代教坊演出傳統的確證。
那么,清儀典承應戲的情形如何呢?筆者目力所及,沒有哪個戲本明確出現“致語”一詞。但是,如果對前文介紹的清宮儀典戲特征還有印象,對于其“媚神頌圣、征瑞稱祥”的評價應該不會感到陌生。得到這樣的評價,清儀典承應戲中無處不在的頌圣之詞是“罪魁禍首”。
《故宮珍本叢刊》第685冊收《天保九如》,為一部十六出的大戲,演圣主萬壽、皇后千秋,東華帝君傳齊洞天福地群仙令其各獻方物,向神州獻瑞之事。經過一系列的戲劇沖突后,在最后一出,東華帝君、花王率眾花仙進獻《天保九如之章》,其辭云:
【天保九如章】圣皇御極,膺天命兮受福薦臻,履方盛兮謙謙令德,成自性兮大寶有箴,握金鏡兮道洽堯心。仁德并兮所親惟賢,綱維正兮執兩用中,聰明圣兮如山如皋,天保定兮惟天佑圣。豫皇情兮惟圣承天,法天行兮躬耕籍田,歲功成兮虔祀先農,錫豐登兮圣功典學。文教興兮國學臨雍,多士盈兮圣代右文,頌休明兮如日如月,世升恒兮我皇繼述。率由舊章,丕承謨烈,之紀之綱,春蒐靈囿,秋狩岐陽,圣人神武,弓矢斯張,殄滅邪教,賓服遐荒,越南南掌,來享來王,上治日臻,莫敢或遑,綿綿壽考,如陵如岡。惟天為大,我皇則之,圣祖垂裕,我皇式之。惟天為圣,孚佑我皇,臣工賢哲,天子當陽。于萬斯年,載篤其慶,子孫千億,瓜瓞繁昌。如松之茂,如柏之長,如川方至,萬壽無疆。(31)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685冊,第431-432頁。
從其起到的作用和內容的思想傾向上來看,與宋代教坊承應和明內府本中的“致語”并沒有什么區別。清宮儀典戲基本上都有這樣或長或短的稱祝之詞,與一般念白不同,此類祝詞多為對仗的駢體文,可以看作致語的變體。
“致語”在明清內府本中的出現與發展,是宋教坊承應與明清宮廷儀典劇演出一脈相承最直接的證據。皇權時代,天下系于一人之身,皇室是內廷演出的直接服務對象,演劇亦為“娛人”。在宮廷演出的場域,觀眾在與演員、戲本構成的交互關系中占據了絕對主導的地位,演出結構、劇本內容必須圍繞著觀眾的視角設計。在這種封閉的編演環境下,呈祥獻瑞、歌功頌德必然成為劇作者和演出者唯一正確并可能的選擇。這是宮廷演劇能夠從宋代一直到明清,仍然在結構上保持高度相似性的根本原因。也是清代儀典戲展現“千人一面”“媚上頌圣”精神特質之癥結所在。今天,我們當然可以從藝術性、觀賞性的角度對此提出批評,但是,戲曲史研究本就應當關注觀眾與演出之間的互動,這種文化史視角才能讓我們的戲曲史“活”起來,呈現出它在歷史長河中鮮活的面貌。
五
在對宋教坊演出、明清儀典戲的結構進行比較分析后,我們還需解決最后一個問題。宋代的“參軍色”并不參加演出,而明清內府本類似角色都由劇中人擔任,這種角色內化是如何發生的?是否體現了宮廷演劇發展的某種規律呢?
宋代的教坊演出,用參軍色將歌、舞、百戲、雜劇演出結合在一起,各個演出段落之間是分隔的,參軍色與前后的表演沒有關聯。對一場演出來說,這樣的結構并無問題。但是,自宋元南戲和元雜劇誕生以來,戲曲演出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在宮廷和民間舞臺上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
宮廷是一個特殊的演出環境。如果說民間劇壇強調的是創新和發展,那么,宮廷演出,特別是宴饗演出,則需要保持和繼承其儀式性。自宋代以來的宮廷宴饗演出,已經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模式,如華麗的致語,駁雜的演出內容,以及通過致語、參軍色串聯起的演出內容。明清內府儀典戲,其實就是繼承了宋教坊演出傳統的一類特殊劇目,從文本角度來說,這類劇目并沒有太高的藝術性。但它具有強烈的儀式感,富麗堂皇的辭藻,以及豐富多彩的演出形式,非常適合宮廷宴會的需要。與宋教坊演出不同的是,明清內府儀典戲是以本為單位的,繼承自前代宮廷承應演出的種種要素,必須在一個統一的主題之下,換言之,作為一出戲,它的結構應當是完整的,不能讓觀者“出戲”。
明清內府本的應對方法是結構內化,將類似“參軍色”的角色從戲外移到戲內,由他將一些原本并不關聯的戲劇要素統一起來,組成一場完整的演出。這應被看作戲曲表演發展成熟的表現。這種內化處理,首先保持了劇本的完整性;其次增強了演出的戲劇性,雖然明清儀典承應戲的關目設計遠不如同時期民間流傳的雜劇、傳奇那么豐富多彩,但是相對于宋教坊演出,既保持了相對完整的結構,又使之統一在某一特定主題之下,全劇沒有游離在劇情之外的人物,保持了演出的連貫性。
同理,清代的內府儀典戲祝頌之詞較前代為短,也是創編手法提高的表現。致語雖然能夠直接表達對帝王的贊美之情,但是在演出中加入大段與情節無關的文辭,影響了演出的連貫性,同時也使得演出時間被拉長。相對于明教坊雜劇,清代的儀典戲更加精煉,演出時間比較短,藝術發展的內在需求,導致了“致語”的簡化。
綜上,通過宋教坊演出史料和明清內府儀典承應戲的對比可以看到,明清內府本,吸收了致語的內容,通過角色內化,繼承了宋教坊承應演出的基本結構,是在繼承宋代以來宮廷演出傳統基礎上繼續發展的產物。正如我們一再強調的那樣,清代儀典承應戲,雖然并沒有太高的思想內涵,但是身處宮廷這樣一個特殊的演出舞臺,在結構和形態上都保留了大量前代同類型演出的痕跡,是我們探索歷代宮廷文化藝術活動的重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