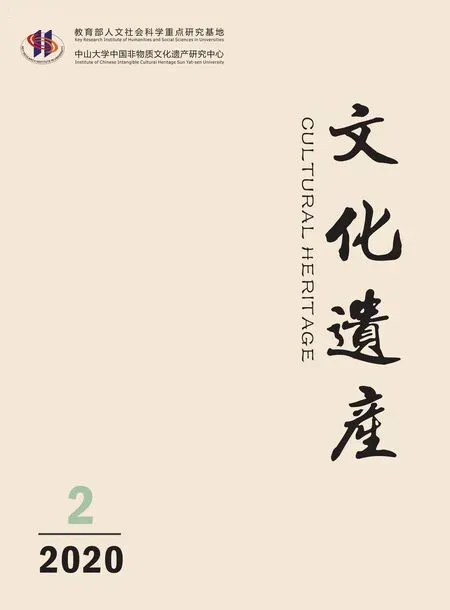明代外交視域下的萬壽慶典承應戲《祝圣壽萬國來朝》研究*
王春曉
有明一代,帝王壽誕(又稱“萬壽”或“圣節”)是與冬至、正旦、郊祀一樣舉國慶祝的重要節日。每逢萬壽,皇帝往往會親至奉天殿接受文武群臣及各國貢使的朝賀。典禮之后的御宴上,則會由隸屬禮部的教坊司承應演出樂舞、百戲、雜劇等文藝節目祝壽增歡。慶典活動中演出的雜劇多為專為祝賀萬壽編演的“宮戲”,這類戲曲又被專稱為 “萬壽慶典承應戲”。今存的明代萬壽慶典承應戲主要收錄在趙琦美《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中,凡八種,多“以神仙傳奇為壽”(1)朱有燉:《瑤池會八仙慶壽引》,蔡毅編:《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匯編》,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第820頁。,思想、題材、結構非常單一。但在此八種明宮萬壽慶典承應戲中,《祝圣壽萬國來朝》(以下簡稱《萬國來朝》)卻極具特殊性。該劇不像其他七劇一樣以神仙道化為依托,而是以漢高祖時期群臣祝壽為故事框架,以古頌今。雖然學界多認為此劇“事極無稽,曲文亦庸劣,特切末甚繁,且登場人物,每折數十至百余人之多,熱鬧之極”(2)王季烈:《孤本元明雜劇提要》,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7年,第56頁。,但倘將之置于明朝對外交往的視域下加以探賾,則會發現:劇中展現的外國朝貢活動與明憲宗成化初期的歷史文獻載記相符,很可能是最初創編于成化年間,劇作的禮樂特征也十分突出。《萬國來朝》雜劇所搬演的“獻吉祥千邦進貢,祝圣壽萬國來朝”(3)《古本戲曲叢刊》編輯委員會:《古本戲曲叢刊》四集“祝圣壽萬國來朝”,上海:商務印書館1958年,第28頁。,不僅是借氍毹演禮祝壽,更是其時東亞大陸上國家、地區間關系的藝術化呈露。
一、創編時間
《萬國來朝》雜劇現有明代趙琦美脈望館抄本,劇末題記寫“小谷本”(4)《古本戲曲叢刊》編輯委員會:《古本戲曲叢刊》四集“祝圣壽萬國來朝”,第28頁。,為趙琦美轉抄于小谷藏本而來。該抄本不分折、未抬頭、多錯訛、無穿關,標屬“本朝教坊編演”類目,學界多認同此雜劇為明代教坊司為慶祝某位帝王萬壽所特意編寫的宮戲,但對其創編時間卻罕少詳考。王季烈《孤本元明雜劇提要》論曰:“其時當為鄭和下西洋好勤遠略之際,內廷太監,撰此以媚人主”(5)王季烈:《孤本元明雜劇提要》,第56頁。,提出該劇的創編時間為明代施行主動外交策略、派遣鄭和船隊七下西洋的永樂、宣德時期。王論未明確其觀點之依據,可信度待商,但據其思路考索《萬國來朝》所演的“四夷朝貢”活動,卻會覓得與雜劇創編時間相關聯的種種端緒。
(一)高麗貢海青
《萬國來朝》雖以漢代為背景,但內容中反復頌贊“圣明”,所演的朝貢活動也具有突出的明代特色,借漢頌明傾向明顯。受雜劇體制之囿,劇中對朝賀各國的地理、風俗、貢物均有紹介,但詳盡敘述的只有高麗,其描摹的重點又在捕獲貢物白色海東青的過程:
(凈扮高麗頭目架海青上云)……我乃高麗國邊廷上頭目高高在上的便是。昨日跟著邊將大人打圍耍子去。則見海那邊飛過來這個雪白的蟲蟻來,上面有些花花的黑道兒,落在彭(疑誤,當為“樹”)上,張著口,原來是肚里饑,害渴了。我舀了一盆水來,放在地下,灑了一石谷子。他看見真個飛將下來了,著我跑向前走,一把拿住。我說是個白鷹,我們邊將說,不是白鷹是個海青。我說,怎末是海青?他說海青是祥瑞。……(正末扮邊將上云)某乃高麗國邊將是也,收得海東青一連,此乃靈禽異鳥,世之無價,不敢隱諱,獻與國王,走一遭去也呵。……(凈云)說著說(疑誤,當為“話”),可早來到也。走了一日左右,則在這里。……(國王云)邊將,你來的正好,我如今收拾方物,要去大國京師進貢天朝,祝延圣壽,不想獻(疑誤,當為“你”)獻此一連海青,端的是靈禽異像,世之絕寶。……(凈云)國王,這個海青是我拿住來。……怕你不信時,著看去,那谷子就都長出苗兒來了。若種的高了,明年飛將一群海青來,多捉住幾個,養的熟了,放飛耍子,可不好?……(國王云)令人便打點上等緞布一千匹、海東青一連、白鹿一只,明日是吉日,便索長行。(6)《古本戲曲叢刊》編輯委員會:《古本戲曲叢刊》四集“祝圣壽萬國來朝”,第11-14頁。
高麗國(明初沿用舊稱“高麗”,后改用新國號“朝鮮”稱之,劇中稱“高麗”)向明廷進貢海東青確有其事,今細按《明實錄》可查知:
(成化二年三月)壬戌,朝鮮國王李瑈遣陪臣金乙孫等貢海青等物,賜宴及衣服、彩段等物有差。(7)“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明憲宗實錄》卷二十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1965年,第541頁。
(成化二年十月)丙寅,朝鮮國王李瑈遣陪臣金永需等赍表、貢馬及白鵲等物慶賀萬壽圣節。(8)“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明憲宗實錄》卷三十五,第703-704頁。
(成化二年十二月)辛酉朝鮮國王李瑈遣陪臣趙瑾等奉表及海青等物來賀明年正旦節。(9)“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明憲宗實錄》卷三十七,第743頁。
(成化三年正月)辛未,朝鮮國王李瑈遣陪臣崔景禮等來朝,貢海青、文魚,賜景禮及賀正旦陪臣趙瑾等宴,并金織衣、彩段等物有差。(10)“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明憲宗實錄》第三十八,第752頁。
成化二年(1466)三月至成化三年(1467)正月的一年間,朝鮮國王李瑈三次派遣陪臣向明朝進貢海青、白鵲、馬、文魚等,“海青”即“海東青”的別稱。《萬國來朝》中,高麗邊廷頭目又反復申說“我跟邊將回去,到明年多拿幾個來,顯的有孝心”(11)《古本戲曲叢刊》編輯委員會:《古本戲曲叢刊》四集“祝圣壽萬國來朝”,第15頁。,暗示進獻海東青不只一次——均與成化二年至三年間朝鮮國進貢的史實相符。
(二)皇帝壽誕時間
此外,劇中又曾兩次敘述捕獲海東青的過程,強調被擒之海東青是剛從海邊飛來、饑渴羸憊,方才被誘捕等等,凸顯祥瑞乃應帝王壽誕之喜而見,透露了帝王壽誕時間的線索。海東青又稱海青,小型猛禽,今已難覓其蹤,舊時載記稱海東青為冬徙鳥類,自東方大海飛至大陸,故稱“海東青”,馴化后可作獵鷹,以能搏擊天鵝而聞名。《元史·地理志》載:“有俊禽曰海東青,由海外飛來,至奴兒干,土人羅之,以為土貢。”(12)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1400頁。《日下舊聞考》“海東青”條轉錄《析津志》云:
海東青產遼東海外,隔數海而至,常以八月十五渡海而來者甚眾。古人云疾如鷂子過新羅,是也。尼嚕罕田地是其渡海之第一程,至則人收之,已不能飛動矣。蓋其來饑渴困乏,羽翮不勝其任。自此始入東國。……嘗諏錫寶齊,云:海青一翅七日或八九日始得至尼嚕罕,其氣力不支,或饑而眼亂者多溺死,凡能逮此地者,無不健奮。……錫寶齊者,國言養鷹之蒙古名也。(《析津志》按:尼嚕罕,滿洲語畫也,舊作努兒干,今譯改。)(13)于敏中:《日下舊聞考》,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年,第2414-2415頁。
是知《萬國來朝》雜劇中所敷演的捕獲海東青的情節與史料所載的海東青習性相符。劇中鷹乃剛渡海而來,則其被捕獲的時間很可能是在中秋前后。另據清楊賓《柳邊紀略》載:“遼以東皆產鷹,而寧古塔尤多。設鷹把勢十八名,每年十月后即打鷹,總以得海東青為主。海東青者,鷹品之最貴者也。……既得,盡十一月即止。不得,則更打至十二月二十日不得,不復更打矣。”(14)楊賓:《柳邊紀略》,周誠望等標注《龍江三紀》,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0-91頁。清代寧古塔與元代之奴兒干均屬遼東極寒之地,毗鄰朝鮮,若寧古塔地區打鷹始于十月之后,則海東青的渡海活動亦有可能持續至十月之后。劇中高麗王又曾說“更那堪路遠迢遙用心機”(15)《古本戲曲叢刊》編輯委員會:《古本戲曲叢刊》四集“祝圣壽萬國來朝”,第14頁。,強調貢道遙遠。明代朝鮮的朝貢路線曾經改變,洪武時期朝鮮使臣前往南京朝貢需提前三個月出發,“帝在金陵時,我國使臣前期三月而發行可也”(16)[日]末松保和:《李朝實錄》,“太宗實錄”,日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53-1954年,第5冊617頁。;永樂皇帝遷都北京后,朝鮮的朝貢旅途縮短,但從出發至北京仍約需兩個月左右。也就是說,雜劇搬演時所慶賀的明代帝王生辰當在海東青渡海的兩個月后,即十月至十二月間。憲宗生辰在十一月初二,與劇作的情節相符。另外,《萬國來朝》中頌贊“百姓們薄稅輕差得自由”(17)《古本戲曲叢刊》編輯委員會:《古本戲曲叢刊》四集“祝圣壽萬國來朝”,第7頁。,詠唱“賀萬壽,永長生”(18)《古本戲曲叢刊》編輯委員會:《古本戲曲叢刊》四集“祝圣壽萬國來朝”,第23頁。,均與憲宗在位時減稅、信佛道的史實一致。綜合來看,《萬國來朝》初次編演于成化時期的可能性很大。
歷史上,朝鮮國王一年之內三次進貢海東青的行為在明廷引發了憲宗及朝臣的警惕,成化三年正月戊子(二十二),憲宗敕諭朝鮮國毋獻珍異:
去歲孟冬,王遣金永需進白鵲,季冬遣趙瑾進海青,未幾又遣崔景禮繼進。三閱月間,三次進貢,王之勤誠,固為可見。然朕即位之初,已詔各處不許進貢花木鳥獸。況白鵲瑞異之物,海青羽獵之用,朕以稽古圖治為用,得賢安民為瑞,于瑞禽鷙鳥,澹然無所好之。得王所獻,徒以置諸閑處而已。王繼今進貢,宜遵常禮,勿事珍奇,況王羅致此物,不免勞民,取其嗟怨。昔者周武主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然惟受其服食器用,于旅獒則卻之,朕所法也。王詩書禮義之國,豈其未知此乎?王其忱念之。(19)“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明憲宗實錄》卷三十八,第761-762頁。
此諭之后,朝鮮暫停進貢海東青;弘治初年孝宗即位后又貢,被飭止,遂不再貢。但是朝鮮之所以會在成化二年三月至次年正月間多次進貢海東青等祥瑞,并非無因。成化二年,憲宗皇帝二十歲加冠成年,意義重大,朝鮮貢獻稀有方物正與此有關。且成化三年正月后朝鮮不再進貢海東青,并不能否定《萬國來朝》一劇創編于成化時期的可能性——此劇的關鍵內容與成化初期的史實相符,禁止進貢海東青,并不影響明代宮廷在戲劇中借此情節肯定朝鮮的忠順。另據曾永義《明雜劇概論》:
以上《慶長生》等十劇大抵都是憲宗時代的內廷供奉劇,上文曾說“憲廟好聽雜劇及散詞,搜羅海內詞本殆盡。”由這些教坊編演的雜劇,我們也可以看出憲宗時代內廷制作及搬演雜劇之盛。《五龍朝圣》雖有嘉靖紀年,亦可能是成化時作,其他諸劇雖未能斷定,但大致也是成化前后的作品。(20)曾永義:《明雜劇概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174頁。
憲宗皇帝好雜劇,明代稗史多有載記。曾永義先生的多部趙琦美抄本宮廷雜劇可確定為成化間編演的結論,也旁證了同屬“本朝教坊編演”的《萬國來朝》初創于成化時期的可能。
二、禮樂性質
作為專為帝王圣節創編的雜劇,《萬國來朝》的特殊性又在于:它以劇演“禮”的同時又是“禮”的組成部分。這是一部會在萬壽慶典中演出的,以蕃國朝貢禮儀、萬壽慶典禮儀為主要內容的雜劇。劇中所涉之“禮”,涵蓋了“蕃國禮”“朝禮”等多種禮儀,戲曲的演出活動亦與明代“大宴儀”“大宴樂”等關系緊密。
(一)以戲演禮
《萬國來朝》演皇帝萬壽將至,“命文武公卿延慶壽,東虜、西戎、南蠻、北狄偏邦小國都來朝貢,進奉奇珍異寶禎祥等物,拜表稱臣,共祝圣壽”(21)《古本戲曲叢刊》編輯委員會:《古本戲曲叢刊》四集“祝圣壽萬國來朝”,第3頁。。其脈望館鈔本不分折,但全劇可約略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無曲,第二、三、四、五部分由末角唱北曲一套,與傳統雜劇楔子加四折相當:楔子演回回國王備無瑕白玉、青獅子等方物將往漢朝朝賀萬壽;第一折寫蕭何與張良、韓信等人相聚回顧定鼎之績,商議“差人前去關津隘口迎接各國使臣”(22)《古本戲曲叢刊》編輯委員會:《古本戲曲叢刊》四集“祝圣壽萬國來朝”,第7頁。;第二折,安南國王、單于國王、高麗國王、河西國王、遼陽女直等搜羅珍貴方物啟程朝貢;第三折,曹參、韓信等人觀吐蕃使者進貢之白虎、金錢豹,“著此使臣在館驛中安下,等各處進貢來全了時,萬壽之辰,文武官員祝延圣壽”(23)《古本戲曲叢刊》編輯委員會:《古本戲曲叢刊》四集“祝圣壽萬國來朝”,第23頁。;第四折是全劇之高潮,演圣節當天四夷朝使各攜奇珍異寶在丹墀陳列,文武群臣在贊禮官、讀制辭官的引導下行禮拜賀。劇作以戲曲的形式藝術性地呈現了萬壽慶典之際千邦進貢、萬國來朝的盛況,其對諸蕃之朝貢過程的呈現與明代朝貢禮高度一致。《明會典》“蕃王禮·蕃使朝貢”:
洪武十八年定:蕃國初附,遣使奉表進貢方物。先于會同館安歇。禮部以表副本奏知,儀禮司引蕃使習儀,擇日朝見。其日錦衣衛陳設儀仗,和聲郎陳大樂于丹陛,如常儀。儀禮司設表案于奉天殿東門外丹陛上、方物案于丹陛中道之左右。設文武百官侍立位于文武樓南,東西相向。蕃使服其服,捧表及方物狀,至丹墀,跪授禮部官員受之,詣丹墀置于案。執事者各陳方物于案畢,典儀內贊、外贊宣表,展表官、宣方物狀官各具朝服,其余文武官常服就位,儀禮司官奏請升殿。皇帝常服出,樂作;升座,樂止。鳴鞭訖,文武官入班。叩頭禮畢,分東西侍立。引禮引蕃使就丹墀拜位。贊四拜,典儀唱進表,序班舉表案,由東門入,至于殿中,內贊贊宣表,外贊令蕃使跪,宣表宣方物狀訖,蕃使俯伏,興,四拜,禮畢。……其蕃國常朝及為國事謝恩、遣使進表、貢方物皆如前儀,唯不宣表。(24)申時行等:《大明會典》卷五十八,明內府萬歷十五年(1587)刻本。
自此可知,明朝蕃使初附或日常朝貢(蕃王來朝禮制規格更高,但程序相似)的禮制均包括迎接、安置、習儀、朝見等必要的儀程,《萬國來朝》的敘事線索與貢儀相符。由于明代朝貢制度的強化,對外交往以“華”統“夷”的傾向性更為突出,明廷對于來“朝”蕃國所“貢”之方物格外重視,陳列及呈送方物既是朝見儀禮的重要組成,也往往會被載入實錄等正史。《萬國來朝》除利用大量篇幅鋪陳各國搜羅進貢方物的用心用力之外,還在第四折集中展現了圣節當天四夷貢使爭向丹墀陳列方物的盛況:
(回回國王引哈麻撒捧珍珠一盤,小回回三人捧無瑕白玉、二人牽獅子同上。云)某乃回回國王是也。離別了本國,來到神京。今日遇萬壽之辰,引著小回回將奇珍異獸入金門進貢去來。(安南國王引卒子四人,二人捧寶山珊瑚樹、二人牽四牙白象同上。云)某乃安南國王是也。自從離了本國,來到京師,今日祝延圣壽去來。(單于王引木朵剌、奴廝哈二人捧貂鼠,小番四人,二人牽駱駝、二人牽馬同上。云)某乃單于王是也,自從來到京師,今日是萬壽圣節,小番牽著駝、馬等物祝延圣壽去來。(高麗國王引卒子六人,二人托高麗布二盤,二人牽白鹿、二人架海青紅籠子同上。云)某乃高麗國王是也。將此白鹿一只、海青一連、高麗布二匹與圣皇祝壽走一遭去。令人快快的行。(河西國王引小河西四人,二人捧靈芝寶瓶、二人牽麒麟同上。云)某乃河西國王是也。今日祝圣壽朝見圣人,小河西行動些。(女直總管引小番四人牽馬二匹同上。云)某乃女直總管是也。小番牽著馬匹,祝延圣壽去來,快快行。(土番五人,二人牽白虎、二人牽金錢豹同上。云)我乃土番是也。今日牽著這兩個貓兒,金門里祝壽去來。(蕭何云)兀那四夷人等,將禎祥異獸擺列在丹墀,等文武群臣來了時同見天顏。(25)《古本戲曲叢刊》編輯委員會:《古本戲曲叢刊》四集“祝圣壽萬國來朝”,第24-25頁。
《禮記正義》“孔穎達疏”:“正義曰:‘夫禮者,經天地,理人倫,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禮運》云:‘夫禮必本于大一。’……禮者,理也。其用以治,則與天地俱興,故昭二十六年《左傳》稱晏子云:‘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并。’”(26)鄭玄、孔穎達:《禮記正義》,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5頁。“禮”是正人倫、治天下的法則,“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27)鄭玄、孔穎達:《禮記正義》,第14頁。“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君臣、父子,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非禮不誠不莊”(28)鄭玄、孔穎達:《禮記正義》,第17頁。。“禮”既是社會秩序之準繩,又是行為踐履的規范,細分為“五禮”:“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祇),以兇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之昏姻。”(29)孔安國、孔穎達:《尚書正義》,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第74頁。朝貢之禮屬“賓禮”,唐代起,賓禮“僅限于接待宴請蕃國君王、使臣,原屬賓禮的百官朝覲禮,則歸于嘉禮。換言之,賓禮就是朝貢禮”(30)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年,第205頁。。
明代重禮,太祖朱元璋于制禮作樂上尤其用心,并視禮為華夷關系的重要象征,提出“夷狄奉中國,禮之常經;以小事大,古今一理”(3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明太祖實錄》卷九十,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1965年,第1582頁。。朱元璋的意志被貫徹到禮的制定中,明代將朝貢禮作為賓禮核心內容,并對蕃王蕃使朝貢、遣使等禮儀作了極為詳盡的規定。明代的蕃王來朝禮定于洪武二年(1369),《明集禮》在其“賓禮·蕃王朝貢·總序”部分特別概括了歷代以來賓禮發展,明代制定賓禮時態度之鄭重可見一斑:
先王修文德以柔遠人而夷狄朝覲,其來尚矣。殷湯之時,氐羌遠夷來享來王。太戊之時,重譯來朝者七十六國。周武王克商,大會諸侯及四夷,作王會。《周禮·秋官》:象胥氏掌蠻夷、閩貊、戎狄之國使,而諭說焉。漢設典客及譯官令丞以領四夷朝貢,又設典屬國及九譯令。武帝元鼎六年夜郎入朝,自后外夷朝貢不絕。……唐設主客郎中掌諸蕃來朝,其接待之事有四:曰迎勞、曰戒見、曰蕃王奉見、曰宴蕃國主,其儀為詳。……宋奉朝貢者四十余國,皆止遣使入貢,雖蕃王未嘗親入朝見,而接見之禮見于禮書者與唐略同。元太祖五年,畏吾兒國王奕都護來朝世祖;至元元年,勅高麗國王植令修世見之禮,六月,植來朝于上都。其后,蕃國來朝,俟正旦、圣節、大朝會之日而行禮焉。……今具其儀作蕃王朝貢篇。(32)徐一夔等:《明集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50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18-19頁。
成化時期的賓禮遵太祖之制,《萬國來朝》作為以朝貢為主要內容的雜劇,又由隸屬禮部的教坊司承應演出,對賓禮相關內容描摹尤稱一絲不茍。此外,該劇對萬壽朝賀禮的刻畫也非常細密、謹確:

《大明會典》的“萬壽圣節百官朝賀儀”相對簡略,僅寫明儀禮與冬至、正旦百官朝賀儀相類,致詞有差且不宣制。綜合“正旦、冬至百官朝賀儀”及“萬壽圣節百官朝賀儀”,可知明洪武時期所定萬壽圣節百官朝賀儀大致如下:
……鳴鞭,報時,雞唱曉。對贊唱:“排班”。班齊,贊禮唱:“鞠躬。”大樂作。贊:“四拜,平身。”樂止。典儀唱:“進表。”大樂作。給事中二人詣同文案前導引,序班舉案由東門入,置殿中,樂止。內贊唱:“宣表目。”宣表目官跪宣訖,俯伏興,唱:“宣表。”展表官取表,宣表官至簾前,外贊唱:“眾官皆跪。”宣表訖,內外皆唱:“俯伏,興,平身。”序班即舉表案于殿東。外贊唱:“眾官皆跪。”代致詞官跪于丹陛中,致詞云:“恭惟皇帝陛下萬壽令節,(至三十年,改‘令節’為‘圣節’),臣某等誠歡誠忭,敬祝萬萬歲壽。”賀訖。……贊禮唱:“俯伏,興,平身。”樂止。贊:“搢笏,鞠躬,三舞蹈。”贊:“跪。”唱:“山呼。”百官拱手加額,曰:“萬歲。”唱:“山呼。”曰:“萬歲。”唱:“再山呼。”曰:“萬萬歲。”凡呼萬歲,樂工軍校齊聲應之。贊:“出笏,俯伏,興。”大樂作。贊:“四拜,平身。”樂止,儀禮官跪奏禮畢。中和樂作。(34)申時行等:《大明會典》卷四十三。
另據《大明會典·萬壽圣節百官朝賀儀·朝賀樂》可知,萬壽慶典中“百官行禮奏【萬歲樂】【朝天子】之曲”(35)申時行等:《大明會典》卷四十三。,與雜劇中奏【朝天子】相同。也就是說,《萬國來朝》第四折中所演之百官朝賀場景,與《明會典》所記明洪武時期所定的萬壽圣節百官朝賀儀完全一致。除《萬國來朝》之外,今存的其他明代宮廷雜劇中往往也有與禮相關的內容,但那些戲中的禮往往體現在劇末的“望闕謝恩”部分,并不像《萬國來朝》一樣在戲曲舞臺上嚴格遵照禮制演出相關內容。《萬國來朝》以戲演禮是應其演出場合生的,這種做法不僅增加了萬壽御筵儀式感,亦令參與其事的四夷朝使在看戲中觀禮,間接宣講了明廷的“華夷”政策。
(二)以戲為禮
明初的大宴儀及大宴樂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基本定制,大宴饗中帝王及文武官員的一切行為均須遵禮而行,帝王及百官的就席、宴飲、離席等均有禮樂伴和,教坊司總其事。 明代的“大宴饗樂歌”一般包括樂歌、樂舞和百戲,演出制度極為嚴苛。《萬國來朝》所演的四夷朝貢與當時大宴饗樂歌中“撫安四夷之舞”“八蠻獻寶承應”等彼此呼應、相輔相成,很有可能是本身便是“大宴饗樂歌”中百戲的組成部分,這也使得此劇的禮樂性質尤其突出。
永樂時期曾對大宴饗用樂之制有所調整,但程序變化不大。明初宮廷大宴樂之節奏概如下表:

洪武、永樂時期大宴樂歌節奏及曲目
明代宮廷大宴常有外國朝使參與,洪武大宴儀中第三爵所演之《撫安四夷之舞》(文舞)、第六爵所奏之“八蠻獻寶承應”都直接關涉外交。永樂時期雖對九奏的次序進行了調整,但《撫安四夷之舞》仍得以保留。兩個時期的《撫安四夷之舞》的內容及表演要求與《萬國來朝》可謂異曲同工,《大明會典》:
奏《撫安四夷之舞》。舞士十六人。東夷四人,……西戎四人,間道錦纏頭,明金耳環,紅纻絲細褶襖子,大紅羅生色云肩,綠生色沿,藍青羅銷金汗袴,紅銷金沿,系腰合缽,十字泥金數珠,五色銷金羅香囊,紅絹擁項,紅結子,赤皮靴。南蠻四人,……北狄四人, 戴單于冠,貂鼠皮檐,……四夷各為一行,舞作拜跪朝謁、喜悅俯伏之狀。舞師二人,執幢以引之。(洪武間定殿內侑食樂)(36)申時行等:《大明會典》卷七十三。:
奏《撫安四夷之舞》。……高麗舞四人,皆服笠子,青羅銷金胸背襖子,銅帶,皂靴。琉球舞四人,皆服綿布花手巾,青羅大袖襖子,銅帶,白碾光絹間道踢袴,皂皮鞋。北番舞四人,皆服狐帽,青紅纻絲銷金襖子,銅帶。伍魯速回回舞四人,皆服青羅帽,比里罕綿布花手巾,銅帶,皂靴。(永樂間定殿內侑食樂)(37)申時行等:《大明會典》卷七十三。
洪武時期的《撫安四夷之舞》中各以四人分扮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四夷朝使,服飾描述詳細(與今存《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中內本穿關相似)。至永樂時期,舞者所扮之四夷則明確為高麗、琉球、北番和伍魯速回回,演員服飾描述較簡略,但民族、地域特征非常明顯。而無論是洪武時期還是永樂時期的《撫安四夷之舞》,其樂章唱誦的內容也都與《萬國來朝》雜劇思路相似。洪武《撫安四夷之舞》樂章由四支曲組成,第一曲【小將軍】曲辭云:“大明君,定宇寰。圣恩寬,掌江山。東虜西戎,北狄南蠻,手高擎,寶貝盤。”(38)申時行等:《大明會典》卷七十三。永樂時樂章增為五支,【小將軍】曲辭改為“順天心,圣德誠。化番邦,盡朝京。東夷歸服,舞于龍廷。貢皇明,寶貝擎”(39)申時行等:《大明會典》卷七十三。,重點頌揚永樂時期鄭和下西洋后眾多東南亞及非洲國家(諸國在明代被列入“東南夷”)來華的盛況。此外,明初萬壽慶典的宴樂中還會演出“九夷進寶隊舞”等以朝貢為內容的樂舞,“百戲”會以朝貢為內容亦在情理之中。從大宴樂節奏來看,洪武時五奏、六奏、七奏之后的“百戲承應”皆有演出雜劇之概率;永樂時雖無類似 “奏百戲承應”的明確要求,然六、七、八、九奏的樂章均為單支曲,內容簡短,與筵席之漸入高潮不相適應,故仍在這部分演出百戲、雜劇的可能。成化時期的大宴饗用樂是無論是遵洪武之制還是遵永樂之制,都有在禮樂中演出《萬國來朝》等萬壽慶典雜劇的可能。
值得關注的還有,《萬國來朝》中的諸國均可對應明朝周邊的國家或地區,且與洪武、永樂時期《撫安四夷之舞》中之“四夷”存在一定對應關系。劇中前往京都朝貢的國家或地區凡有七個,對諸夷的稱謂中,安南、高麗、女直的名稱與明代基本一致,其他四國指代的民族或地區也均有跡可循。“回回國”,明時無此稱之國,劇中將其列入西戎,稱其國“東連沙塞,西接金城,南近黃河,北臨山岳”(40)《古本戲曲叢刊》編輯委員會:《古本戲曲叢刊》四集“祝圣壽萬國來朝”,第1頁。,“人人善念看經,個個持齋把素”(41)《古本戲曲叢刊》編輯委員會:《古本戲曲叢刊》四集“祝圣壽萬國來朝”,第1頁。。據《大明會典》“朝貢三·西戎上”:“自陜西蘭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七十里,為嘉峪關,嘉峪關外,并稱西域。而陜西以南,并四川,抵云南外檄,并稱西番。西域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42)申時行等:《大明會典》卷一百七。;“(哈密)其國部落,與回回、畏兀兒三種雜居,非貴族不相下。永樂二年,以封元孽安克帖木兒為忠順王,而授其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為指揮等官,分居苦峪城。……諸番貢使,皆由哈密譯送。成化元年,令哈密每年一貢,以八月初旬驗放入關”(43)申時行等:《大明會典》卷一百七。。結合劇中回回國王哈麻撒被回回國王傳喚時“正在叫佛樓上”(44)《古本戲曲叢刊》編輯委員會:《古本戲曲叢刊》四集“祝圣壽萬國來朝”,第1頁。的情況來看,此回回國很可能是指主動內附明朝的“土魯番回回”,也就是信仰佛教的畏兀兒人。(45)參見鐘焓《民族史研究中的“他者”視角——跨語際交流、歷史記憶與華夷秩序語境下的回回形象》,《歷史研究》2008年第1期。洪武《撫安四夷之舞》西戎人裝扮為“紅銷金沿,系腰合缽,十字泥金數珠”,亦當系佛教徒;永樂《撫安四夷之舞》亦有“伍魯速回回舞”,對應的也是四夷中的“西戎”。成化元年,哈密每年一貢,八月初旬入關的話,至京之期亦在憲宗壽誕之前,貢使參與萬壽慶典適逢其期。“單于國”之稱,明時亦無之。《萬國來朝》中其國王自稱“生居塞北,長在沙陀,能騎劣馬,善拽雕弓,駝馬成群,牛羊遍野”(46)《古本戲曲叢刊》編輯委員會:《古本戲曲叢刊》四集“祝圣壽萬國來朝”,第8頁。,貢物為駝、馬、貂鼠皮。今按《明會典》“朝貢三·北狄·迤北小王子”條有:“虜自天順、成化以來,更立數王,然皆稱小王子,自是頻年入貢。(成化)元年,貢使六千余人,準放一千五百余人。……至京者,以五百人為率,貢道皆由大同,入居庸。……貢物:駝、馬、貂鼠皮、海青。”(47)申時行等:《大明會典》卷一百七。是知劇中單于國王極有可能代指明代天順、成化以后入貢的瓦剌部落首領。(洪武《撫安四夷之舞》有“北狄四人,戴單于冠”)“土番”當即吐蕃,漢代無此稱,唐以后用指青藏高原上的藏族政權,明代稱其為“烏思藏”:“西番古吐番地,元時為郡縣。洪武初,因其舊職。于是烏思藏番僧,有闡教王、闡化王、輔教王、贊善王,統化番民,又有護教王、大乘法王、大寶法王,凡七王,俱賜銀印,令比歲或間歲朝貢。成化十七年題準,令每三年一貢。”(48)申時行等:《大明會典》卷一百八。“河西國”明時亦無之,劇中稱其“東連寧夏,西接土番,南近長城,北臨紫塞”(49)《古本戲曲叢刊》編輯委員會:《古本戲曲叢刊》四集“祝圣壽萬國來朝”,第15頁。,是則其地在烏思藏與寧夏間,當為明之“長河西”:“洪武十六年置長河西等處軍民安撫使司,每年一貢。”(50)申時行等:《大明會典》卷一百八。
據《大明會典》中禮部主客清吏司之區劃:高麗(朝鮮)、安南為東南夷(在雜劇中又被稱為“南蠻”),女直屬東北夷,回回國(哈密衛區域)為西戎,單于國(迤北小王子)屬北狄,土番(烏思藏)、河西(長河西)則為西戎。從這個角度來看,《萬國來朝》可稱是角色更多、排場更復雜、內容更豐富的“八蠻獻寶”或“九夷進寶”。劇作將大宴樂《撫安四夷之舞》中的四夷或高麗、琉球、北番、回回等四夷進一步拓開、細化,以一部雜劇的規模在大宴饗九奏間鋪排了“東虜西戎南蠻北狄,偏邦小國都來朝貢,進奉奇珍異寶禎祥等物,拜表稱臣,共祝圣壽”(51)《古本戲曲叢刊》編輯委員會:《古本戲曲叢刊》四集“祝圣壽萬國來朝”,第3頁。的盛況。
《萬國來朝》在內容中以戲演禮,劇作本身又是朝賀禮樂的一部分,體現了明代朝貢制度及華夷觀念中的重禮傾向。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曾有論曰:“在古代觀念上,四夷與諸夏實在有一個分別的標準,這個標準,不是‘血統’而是‘文化’。所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狄進于中國則中國之’,此即是以文化為‘華’ ‘夷’分別之明證,這里所謂文化,具體言之,則只是一種‘生活習慣與政治方式。’”(52)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第41頁。某種意義上來講,“禮”被視作“華”高于“夷”的根本標準,在古代中國的對外交往,特別是明清時期的朝貢制度中一直占有重要位置。費正清《中國的世界秩序——傳統中國的對外關系》中曾以“他者”的視角提出:“東亞社會——中國、朝鮮、越南、日本及小島王國琉球——都是由古代中國分衍出來,并在中國文化區域內發展起來的。這個地區深受中國文明的影響,例如漢語表意文字系統、儒家關于家庭和社會秩序的經典教義、科舉制度,以及中國皇朝的君主制度和官僚制度等等。中國因其地大物博,歷史悠久,自然成為東亞世界的中心。”(53)[美]費正清:《中國的對外秩序——傳統中國的對外關系》,杜繼東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1頁。雖然費正清更傾向于用“中國的世界秩序”而非“朝貢”來指稱傳統中國的對外關系,但他在文章中也認為“文明”,也就是“禮”,在明清時期中國的對外交往(特別是與東亞的國家、地區的交往)中意義重大。
雖然一直有中外學者爭論從中國與其他國家間關系的雙向性考量,稱“朝貢”為“封貢”或“封賞”更為恰當,(54)參見李云泉《話語、角度與方法:近年來明清朝貢體制研究的幾個問題》,《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2期。但“朝貢”這一語匯在明清時期中國的官方文獻中是事實性地被廣泛使用的。由于明朝是在推翻蒙古統治之后建立的漢族統治帝國,其在與周邊國家或地區進行交往時,尤其注重強調華夷秩序中的華夏正統性,試圖建立以明朝為中心、四夷圍拱朝貢的天下秩序,宣揚“大明一統錦華夷”(55)《古本戲曲叢刊》編輯委員會:《古本戲曲叢刊》四集“祝圣壽萬國來朝”,第13頁。,并以“朝貢”為政治框架,開展經貿、文化活動。出于朝貢制度本身對“朝”儀與“貢”物的側重,明廷會在重要涉外場合的禮樂中奏演“朝賀”“獻寶”等內容的樂舞雜劇既是對前代禮樂的承繼,又是對大明風范的張揚。《萬國來朝》之重禮,正是對其時中外交往的真實反映。
結 語
萬壽慶典承應戲演出場合和觀眾的特殊性決定了這類戲曲“幾乎無一劇不是很討厭的頌揚劇。董其昌所謂‘欲效楚人一炬’者,正是指此等劇而言。在結構的雷同、故事的無聊、敘述的笨澀方面,尤為‘前無古人,后無來者’”(56)鄭振鐸:《鄭振鐸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66頁。。以創編于成化時期的《萬國來朝》來講,作為一部會在萬壽慶典大宴饗中在帝王及中外貴賓面前演出的禮樂雜劇,它所傳達的思想只能是明朝的國家意志,展現中外交往狀況只能是四夷依制納貢、遵禮朝賀。但這類戲曲卻也并非毫無價值。萬壽慶典雜劇創編的目的決定了它的保守、板滯,端肅有余活潑不足,但它的這種禮樂特征恰恰是文人戲曲或民間小戲所無法承荷甚至不能觸及的。另外,慶典承應戲演員的超凡技藝,排場、服飾、切末等精良繁奢,也彌補了其內容、結構上的不足。《萬國來朝》各折中登場的人物在七十人以上(含漢朝文武諸將有名姓者27人,各國貢使41人),作為貢品的動物十余只、各類方物近十種。該劇的穿關雖不存,但據《大明會典》中所載之四夷服飾亦可推知其演出時服飾、切末之繁奢和場面的盛大,這也是家班或民間戲班難望項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