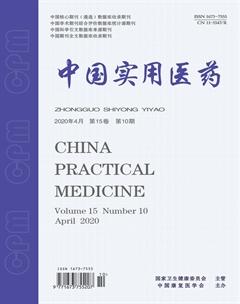VSD技術聯合外固定支架治療脛腓骨開放性骨折伴軟組織缺損效果觀察
羅潔誼 滕范武 諶小豐

【摘要】 目的 觀察對脛腓骨開放性骨折伴軟組織缺損患者行負壓封閉引流(VSD)技術聯合外固定支架治療的臨床效果。方法 68例脛腓骨開放性骨折伴軟組織缺損患者, 根據隨機數字表法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 每組34例。對照組患者實行外固定支架治療, 觀察組患者實行VSD技術聯合外固定支架治療。比較兩組患者創面愈合時間、感染發生情況。結果 觀察組患者的創面愈合時間(14.03±3.22)d短于對照組的(20.88±4.02)d, 感染發生率0低于對照組的17.65%, 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 給予脛腓骨開放性骨折伴軟組織缺損患者行VSD技術聯合外固定支架治療可有效促進創面愈合, 降低感染發生率, 應用價值較高。
【關鍵詞】 脛腓骨開放性骨折;軟組織缺損;負壓封閉引流技術;外固定支架
DOI:10.14163/j.cnki.11-5547/r.2020.10.037
目前, 脛腓骨開放性骨折多是受外力撞擊所致, 高空墜落、交通事故均是造成該疾病的主要因素, 故該疾病患者多伴有大面積皮膚缺損、挫傷, 甚至有骨外露, 故對該疾病的治療不僅僅只是將骨折復位, 如何處理軟組織缺損也至關重要。且一旦處理不當, 極易導致感染, 影響患者預后[1-3]。傳統臨床對該疾病的主要治療方式為外固定支架, 重視保護局部軟組織的血液供應能力, 有利于骨折愈合, 但無法將深部組織液引流出, 愈合慢, 感染發生率較高[4-6]。VSD作為創面與引流管的中介, 能做到全面引流, 改變了傳統創面或創腔的引流方式, 現為探究將VSD技術與外固定支架聯合應用于該疾病患者治療中的臨床效果及應用價值, 特選取2013年3月1日~2019年10月31日本院進行治療的68例脛腓骨開放性骨折伴軟組織缺損患者作為研究對象, 收集相關資料, 并進行分析, 現具體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選取本院2013年3月1日~2019年10月31日收治的68例脛腓骨開放性骨折伴軟組織缺損患者, 根據隨機數字表法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 每組34例。對照組中女14例, 男20例;年齡21~62歲, 平均年齡(40.93±7.03)歲;致傷因素:高空墜落者3例,?壓砸傷者15例, 交通傷者16例;受損部位:中下部位12例, 中部15例, 中上部位7例;軟組織受損面積:2.2 cm×4.6 cm~7.8 cm×12.8 cm。觀察組中女13例, 男21例;年齡21~62歲, 平均年齡(40.93±7.04)歲;致傷因素:高空墜落者5例, 壓砸傷者12例, 交通傷者17例;受損部位:中下部位13例, 中部10例, 中上部位11例;軟組織受損面積:2.1 cm×4.8 cm~7.9 cm×12.9 cm。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治療同意書已被患者及其家屬簽署, 且經過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
1. 2 方法 所有患者均于術前接受相關檢查, 對身體其他部位的損傷積極處理, 再進行骨折處修復。對照組患者實行外固定支架治療, 患者給予聯合阻滯麻醉或全身麻醉, 將患者調整為仰臥位體位, 將消毒后的鋪單鋪在手術暴露區, 對骨折處創口進行清理, 將受到嚴重污染或脛前失去血運的軟組織徹底清除。應用相應的手術入路將腓骨骨折端暴露, 進入點為受創面, 應用相應的固定裝置進行支撐, 以起到將腓骨的長度進行恢復的目的。再復位脛骨骨折, 固定選用單臂外固定支架。在距離骨折端7 cm左右的脛前處進行鉆孔, 將2~3枚外固定螺釘置入, 應用相應尺寸的單臂外固定架將脛骨進行調整并給予固定。如脛骨骨折觸及到踝關節, 固定可選用超關節外固定架, 并在跟骨中置入外固定螺釘進行固定。復位碎骨塊, 根據骨折受損程度, 應用縫線、克氏針鋼絲以及螺釘等方式輔助內固定。觀察組患者實行VSD技術聯合外固定支架治療, 于復位完畢后, 應用正常肌肉或軟組織將外露骨質進行覆蓋。結合創面大小選擇相應尺寸的VSD, VSD材料包括:三通連接頭, 連著負壓吸引瓶的一端, 是連接帶壓力表的電動吸引器, 一端帶16號硅膠管(測孔長30 cm), 聚氨甲酸乙酯薄膜(20 cm×15 cm), 聚乙烯醇縮甲醛泡沫(1.0 cm×10.0 cm×15.0 cm)并連接一條硅膠管, 提供廠家為成都吉泰醫療器械有限公司。將缺失的軟組織應用負壓海綿進行填補, 填補需嚴實, 再將皮膚周緣應用針線縫合, 對創面應用生物貼膜進行包扎, 并通過吸引器檢查包扎的是否嚴實, 有無漏氣。封閉后的創面應對負壓情況進行強化觀察, 如薄膜下有積液出現或癟陷的VSD恢復原狀, 提示負壓的效果失去, 應重新包扎。如持續有效, 則1周后將VSD拆去, 如創面無骨外露且有良好的肉芽組織生長, 則應用游離植皮進行修復。如創面邊緣有肉芽組織生長且創面清潔, 但有骨外露者, 應用皮瓣移植修復, 如有骨缺損者, 可應用異體骨或自體骨移植修復;如創面有較多膿性分泌物流出或無良好的肉芽組織生長者, 可將創面進行清理, 并再次應用VSD 負壓吸引。
1. 3 觀察指標 比較兩組患者創面愈合時間、感染發生情況。
1. 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20.0統計學軟件處理數據。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x-±s)表示, 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檢驗。P<0.05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觀察組患者的創面愈合時間(14.03±3.22)d短于對照組的(20.88±4.02)d, 感染發生率0低于對照組的17.65%, 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3 討論
VSD的創始人為Fleischmanb博士, 后經裘華德等加以改良而廣泛應用于臨床。經國內外多年研究表明[8, 9], 該技術可有效縮短創面肉芽生長時間, 并有利于創面清潔度, 降低術后感染發生率, 在軟組織損傷治療中有較高的應用價值。現為探究將該治療方案應用于脛腓骨開放性骨折伴軟組織缺損患者治療中的臨床效果, 特做此研究。
本研究表明, 觀察組患者的創面愈合時間(14.03±3.22)d短于對照組的(20.88±4.02)d, 感染發生率0低于對照組的17.65%, 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究其原因, 該疾病患者多血運較差, 脛前皮膚較薄, 受到高能量損傷后極易導致大面積皮膚軟組織缺損, 如受損后未給予有效固定, 感染發生率較高。結合本研究結果得出負壓吸引結合沖洗保證引流通暢和創面處于相對干凈的環境, 結合外固定支架固定技術, 各自發揮作用, 從而更好使該疾病的患者得到康復。外固定支架在治療該疾病的內容及關鍵問題:外固定支架固定后, 如創面恢復時間較長, 極易誘發成角、螺釘松動以及釘道感染等并發癥, 致使骨不連發生, 延遲骨折愈合時間, 不利于患者的康復。故提高固定的穩定程度尤為重要。在對骨折初步整復時, 應盡可能將成角和旋轉畸形消除, 盡可能將支架與螺釘平行, 提高固定牢固性[10, 11]。同時, 骨折線同側的兩釘之間距離與其所承受的力量成正比, 承受力量越大, 支架固定效果越佳。故在置釘時, 應盡可能調大2枚釘之間的距離[12]。將固定螺釘置入后, 在骨最大直徑處將螺釘穿入, 所有螺釘應垂直于骨干的縱軸, 平行與踝、膝關節冠狀平面, 使活動時所受到的扭力得以降低, 進而提高固定的穩定程度。固定螺釘與皮膚之間應無張力。固定螺釘置入時, 應注意不要對關節囊以及關節面造成損傷, 調控好進針的角度, 避免腓骨下端受到螺釘前端推頂而對關節活動造成影響。手術結束后, 應對骨折是否發生移位以及外固定架旋鈕是否有松動強化觀察。強化對釘道護理, 以防發生釘道感染[13]。而VSD存在的主要問題:如創口周圍有不規則的深淺度者, 在材料置入時, 容易造成創面無法充分與材料接觸。且患者在接受外固定支架治療后, 創面封閉困難度較大, 漏氣發生率高。為解決這一問題, 可繼續生物膜覆蓋并加大吸引壓力, 產生持續負壓來代替封閉不嚴密的不足。對于骨外露的創面, VSD只是一個過渡手段, 待創面肉芽生長后還需應用其它方法覆蓋創面, 如轉移皮瓣或游離皮瓣等。造成引流成功與否的主要原因為調整有效負壓。多以-125~-450 mm Hg(1 mm Hg=0.133 kPa)的負壓為最佳, 如負壓過高, 極易誘發創面出血, 一旦發生出血, 應及時給予解決措施, 包括手術注射、停止負壓引流等方案。如負壓過低, 極易導致引流管被堵塞, 引流效果受到影響等問題出現, 故調控引流通暢度尤為重要, 經分析, 引流堵塞發生的主要因素為引流區粘稠引出物或壞死組織過多, 引流系統無法將其順利引出。故堵塞發生后應根據具體情況給予相應的解決措施。因此根據患者創面實際情況調整負壓是VSD技術中的操作要點[14, 15]。
綜上所述, 對脛腓骨開放性骨折患者應用VSD技術聯合外固定支架進行治療, 可有效縮短創面愈合時間, 并降低了術后感染發生率, 臨床應用價值顯著。
參考文獻
[1] Kliushin NM, Sudnitsyn AS, Subramanyam KN, et al. Manage-ment of neurologic deformity of the ankle and foot with concurrent osteomyelitis with the ilizarov method. Foot Ankle Int, 2018, 39(2):226-235.
[2] 繆旭東, 閆喬生, 賈晶, 等. 腓腸肌肌皮瓣結合髓內釘治療脛骨中段開放骨折伴軟組織缺損. 中國矯形外科雜志, 2016, 24(2):188-190.
[3] 宗雙樂, 闞世廉, 蘇立新, 等. 鄰接皮瓣聯合外固定架急診治療兒童開放性脛腓骨骨折并軟組織缺損. 中國骨與關節損傷雜志, 2015, 30(10):1111-1112.
[4] Masquelet AC. Induced membrane technique: pearls and pitfalls. J Orthop Trauma, 2017, 31(Suppl5):S36-S38.
[5] Meleppuram JJ, Ibrahim S. Experience in fixation of infected nonunion tibia by Ilizarov technique-a retrospective study of?42 cases. Rev Bras Ortop, 2016, 52(6):670-675.
[6] Tetsworth K, Sen C, Herzenberg JE, et al. Bone transport versus acute shortening for the management of infected tibial non-unions with bone defects. Injury, 2017, 48(10):2276-2284.
[7] 常曉, 張保中, 張萬利, 等. 組合式外固定支架治療脛骨遠端骨折. 中華創傷骨科雜志, 2016, 18(4):346-350.
[8] 吳錚, 任靜, 劉克廷, 等. 外固定架固定治療開放性脛腓骨骨折的療效分析. 中國骨與關節損傷雜志, 2018, 33(8):859-860.
[9] 王任明, 陳霞. 脛腓骨開放性骨折外固定支架臨床運用研究進展. 貴陽中醫學院學報, 2014, 36(5):149-151.
[10] 李振. 應用外固定支架方法治療脛腓骨骨折療效. 中國傷殘醫學, 2018(10):8-10.
[11] 李忠偉, 任鵬, 張樹文. 組合式外固定架輔助顯微外科技術治療開放性脛腓骨遠端骨折合并軟組織缺損. 骨科, 2018, 9(2):112-117.
[12] 李志波. 組合式外固定架治療伴有軟組織損傷的脛腓骨遠端骨折. 臨床骨科雜志, 2016, 19(4):455.
[13] 閆利輝. 脛腓骨遠端骨折以環形外固定架進行治療的臨床分析. 中國衛生標準管理, 2015, 6(7):55-56.
[14] 宮玉鎖, 鄭建鵬, 陳國棟. 外固定架治療脛腓骨開放性骨折臨床分析. 甘肅科技, 2019, 35(15):155-156.
[15] 高文飛, 王衛東, 宋瑞鵬. 外固定架聯合VSD 及皮瓣移植治療開放性脛腓骨骨折合并軟組織缺損的效果分析. 河南醫學研究, 2018, 27(17):3098-3099.
[收稿日期:2019-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