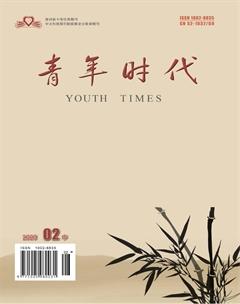“一事不再罰”原則淺議
王瑛
摘 要:中國頒布的《行政處罰法》當中明確表明了,針對當事人所實施的同一違反法律規定的行為,不可以做出兩次以及超過兩次罰款的懲罰。這便是我國“一事不再罰”所要求的基本出處。本文旨在探尋該原則的起源與發展,探討何謂“一事”,并初步探究行政處罰與刑罰處罰的關系以及環境立法中“按日計罰”與該原則的相符性。
關鍵詞:一事不再罰;行政處罰;按日計罰
一、一事不再罰原則的起源與發展
一事不再罰的原則是早在古羅馬時代就誕生了的。在這個時期,法院所實行的是一審以及最后確定案件的判決,針對已然形成裁判并且具有法律形式的約束力的案件,除非法律作出其他規定的,否則不可以再次提起訴訟以及開展審理活動。這就是一事不再理原則。該原則被廣泛運用于民事案件的審理判決中。該項原則在大陸法系國家以及英美法系國家的法律規定當中都有所體現。
一事不再理的原則在我們國家現在的法律制度中也有一些表現的地方,如民事訴訟以及行政處罰等領域。在民事訴訟領域,一事不再理原則主要是通過禁止重復起訴這一概念予以體現。2001年,最高院頒發的《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1]7號)規定:“當事人在侵權過程中未提出賠償要求,那么在訴訟結束后人民法院就不在給予受理,根據同一侵權事實進行賠償的,人民法院也不予受理。”盡管此條文并未清晰地闡明了一事不再理的含義,但依照最高院編定相關司法解釋的闡述,此條規定主要是根據一事不再二理的原則進行的。
在行政法立法方面,我國的行政規章以及地方的立法中也早就已經規定過一事不再罰的原則。在1990年的9月,按照《道路運輸違章處罰規定》:“在一次運輸的過程中,同一種的違章行為如果已由一個道路運輸管理機關作出處罰了,那么其他的道路運輸管理機關就不得再對其進行重復的處罰。”
1996年的3月,我國確定頒布的《行政處罰法》是我國首次在法律上來正式確定一事不再罰的原則。但是該法只作出了“一事不能兩次罰款”的規定,而不是“對當事人的同一違法行為,行政部門不可以依據同一事件以及同一緣由做出兩次以及以上的懲罰。”但縮減版的規定依然沒有平息學界的紛爭。首先,我們需要了解“同一違法行為”具體指的是什么?其次,就是關于行政處罰以及刑罰處罰之間的關系,也就是針對確定屬于犯罪行為的違反法律規定的行政活動,是否可以同時做出行政領域的懲罰以及刑法領域的懲罰,倘若同時做出兩種懲罰,那么是不是就跟一事不再罰原則之間產生了沖突。
二、一事不再罰原則中的“一事”
針對《行政處罰法》當中一事不再罰的要求的解釋以及運用關鍵在于“一事”的認定。何謂“一事”,國內學者提出如下4種學說。
一是違法行為說:覺得已是不在法當中的的含義,是“相對人的一件違反法律的事項”。他認為所謂的侵犯只是一種行為或是一種很自然的感覺,而且是脫離于法規范評價的。
二是違反法規說:認為將具體行政法律規定當作一個違反法律規定的行為。盡管排除了自然行為說的不確定性,然而,具體行政法律規范依然是有待確定含義的詞語,與此同時,還易于導致他人做出錯誤理解。
三是行政法益說:行政管理法還規定了,要以行為對法律利益所造成的實際損害來作為標準,如果在同一法律當中與同一違法行為是一樣的,那么就可以用管理目的來進行區別。
四是構成要件說:認為根據應當接受行政上的懲罰的行為的構成要件以區別一件事以及數件事,也就是符合同種違法構成要件等,判定其為一件事,如果可以用來滿足多個違法構成要件的,那么就視為是數件事。構成要件說是基于違反法規說得來的,具備更為確定的含義。近幾年以來,構成要件說得到了諸多學術專家的認可和推廣。
在筆者看來,一事不再罰原則得以產生以及發展的原因是,其最終目標是限制行政部門的權力,這也是行政法存在的意義。因而我們在對構成要件說和自然行為說進行取舍時,必須要考慮的一個問題:哪種學說更有利于限縮行政機關的職權?如果適用自然行為說,對于牽連性的違法行為,相對人實施的手段行為、結果行為、目的行為都可以被看做一個“身體動靜”,行政機關可以處罰多次,枉顧原則之理念顯然是不合理的。相比較之下,構成要件說的范圍明顯狹窄了很多。所以在筆者看來,針對在一事不再罰中有所提及到的一事,應采用構成要件說,即符合一個違法所構成的要件那么就是一事,同時適當結合行政法益說。
三、行政處罰與刑罰處罰的關系
針對已然屬于犯罪行為的,違反法律規定的行政活動,是不是可以同時做出行政領域的懲罰以及刑罰領域的懲罰,倘若同時作出兩種懲罰,那么是不是就相對的違反了一事不再罰的規定呢?
互為替代說:認為對違反法律行為的懲罰,僅可以在行政領域的懲罰以及刑事領域的懲罰當中,采用其中一種。
并列適用說:認為對于同個違反法律規定的行為,不但要對其做出刑事懲罰,還要適用行政處罰。
附條件并科說:亦被稱作“免除代替”,覺得刑事領域的懲罰和行政領域的懲罰能夠并列適用,但是其中一種懲罰執行完結之后,不需要再執行另外一種懲罰的情況下,得以免于執行。
筆者認為,無論是行政部門亦或是刑事部門,如果查找到同一違反法律規定的活動亦或是犯罪活動的相關資料,就應當首先進行立案、先行作出調查、先行確定懲罰,行政部門對于有施行犯罪活動嫌疑的,選擇對該行為人進行移送而不中止調查活動以及作出懲罰,刑事司法部門對于必須馬上做出能力罰的犯罪活動則應當和行政執法部門作出商議之后在第一時間內作出懲罰決策。和財產有關的懲罰應當嚴苛遵守一事不再罰的規范,不管是行政部門先行作出行為人必須繳納罰款抑或是沒收行為人財產的決策,或者是司法部門先行作出行為人必須繳納罰金或是沒收行為人的財產的決策,后面做出決策的部門都不可以再次施行財產罰。針對人身自由法,司法機關所作出的判決應當優先于行政執法部門所做出的決策。針對不同類型的懲罰,則都適用并罰方法。
四、環境立法中“按日計罰”與該原則的相符性
環境污染具有持續性以及復雜性的特征,導致環境保護工作面臨了巨大的壓力,利用法律制度的設計規制環境污染問題成為現代社會環保工作的重點。為了突破守法成本高昂而違法成本低廉的窘困境地,新出臺的《環保法》確定了以日為標準計算罰金的規定。
將按日計罰定位為“行政處罰”不可避免的面臨如何正確處理其與“一事不再罰”的關系。以日為標準計算罰金的規定和一事不再罰規定是不是有矛盾呢?
首先,環境以日為標準計算罰金的規定全新的承擔責任方式,適用的是具有持續性特點的違反法律規定排放污染物的行為,其具備如下特征。
一是適用對象的限定性。環境領域違反法律規定行為的類型大體上可被劃分為程序性的違法行為以及實體性的違法行為兩類。
二是計罰方式的特殊性。針對具備持續性特征的,但凡是有違反法律所規定的排放污染物行為,以日為標準計算罰金的規定中,計算的單位是日,三十日為最長單個計罰周期是其不同于其他行政處罰手段的特點。
三是計罰程序的行政性。計罰程序的執法主體是環境行政機關,因此程序應當符合相關行政法律法規與原則,要求執法者嚴格遵守“程序正當”、“比例原則”等行政法原則。
其次,我國環境按日計罰不屬于“執行罰”。從新《環保法》第59條合法性層面來看,法律保留原則簡單來說就是我們的一些行政行為只能在法律所規定的情況下才能進行,如果法律沒有做出相關的規定那么就不得進行。即“法無明文規定不可為”,《行政強制法》中就已經很明確提出過了,行政強制執行是根據法律予以確定的。法律規范中未明確表明行政部門有權利作出強制執行行為的,做出對應的決策的行政部門僅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請,要求法院代為實施強制執行。因此,以日為標準計算罰金的規定不應當被視為是“執行罰”。
因此,在筆者看來,屬于行政處罰范圍的一日為標準計算罰金和“一事不再罰”并不存在矛盾,只是運用一定的立法技術為了完成某種特定的目的和行政任務,就按日計罰而言,他們的主要目的也只是為了加大對違法企業的懲治力度,以破解“違法成本低”的困境。
參考文獻:
[1]楊瀚宇,李暉.我國環境按日計罰制度法律問題研究——以《辦法》修改為背景[J].職工法律天地,2018(20):38-41.
[2]王健.論一事不再罰原則中的“一事”[J].法制博覽,2018(9):216.
[3]練育強.行刑銜接視野下的一事不再罰原則反思[J].政治與法律,2017(3):123-131.
[4]陶亮.淺議按日計罰制與一事不再罰原則的沖突——以重慶天價罰款事件為例[J].法治與經濟,2011(3):6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