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中共對淪陷區研究的“范式”建構
——以毛澤東《研究淪陷區》為文本
周 東 華
1939 年延安“時事問題研究會”整理編輯的《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一書,比較系統地展示了當時中共搜集整理的有關淪陷區問題的史料。毛澤東為該書撰寫了一篇不長的序言《研究淪陷區》,成為抗戰時期中共探討淪陷區問題的重要文獻。1○1958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翻印此書,方便了學者們引用該書從事淪陷區問題研究。2015 年高瑩瑩在回顧淪陷區問題研究時認為“時至今日,書中所列舉的日偽政權、奴化教育、移民、宣傳、偽軍、經濟掠奪、日軍暴行等內容依然是淪陷區研究的主要對象”,2○可見該書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淪陷區研究”,具有“范式意義”。收錄在書中的毛澤東的這篇序言,雖然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關注,但學者們僅在研究、梳理相關問題時簡要介紹、引用、評述該文,目前尚未專題研究。3○從學術史角度看,最近數年有關淪陷區的研究正在悄然復興,尤其是關于淪陷時期江南城市史的研究,新文化史范式正在挑戰長期以來“抗戰”主旨下的淪陷區研究路徑與方法。4○如何融通淪陷區研究的新舊范式,進一步推動淪陷區研究發展,成為目前抗戰史研究必須解決的問題。筆者認為,毛澤東1939 年10 月1 日發表的這篇文章,為新時期如何進一步研究淪陷區問題,提供了可供借鑒的“范式”。
一、《研究淪陷區》的旨趣
毛澤東《研究淪陷區》一文雖然1182 字,但內在邏輯清晰,指出了抗戰相持階段淪陷區研究的意義、路徑、方法和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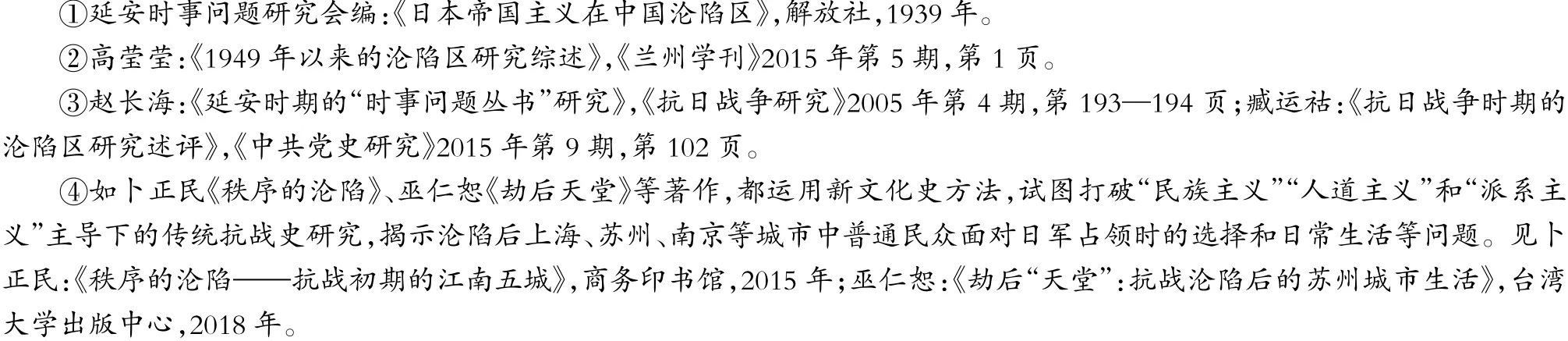
第一,毛澤東指出“淪陷區研究的問題是刻不容緩了”,因為淪陷區問題是“敵我相持階段的極端重要的問題”,“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生死問題”。對此,毛澤東從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中國共產黨的抗爭兩個角度作了闡釋。從日方看,毛澤東開篇指出:“中國淪陷區問題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生死問題”,因為“在目前階段”(即“抗戰相持階段”),日軍侵略從“正面軍事進攻,大規模的戰略進攻”轉變為“政治進攻和經濟進攻”兩方面。所謂的“政治進攻”,“就是分裂中國的抗日統一戰線,制造國共摩擦,引誘中國投降”;而所謂“經濟進攻”,“就是經營中國淪陷區,發展淪陷區的工商業,并用以破壞我國的抗戰經濟”,其中“經濟進攻”對于日本帝國主義的生存尤為重要,日軍“為達其經濟進攻之目的”,必將采取對中共抗日根據地的軍事進攻,“彼對我游擊戰爭的‘掃蕩戰爭’”;采取政治進攻,“需要建立統一的偽政權”;進行心理進攻,“需要消滅我淪陷區人民的民族精神。”在這種嚴峻情況下,對中國共產黨的抗爭來說,“淪陷區問題,成了抗戰第二階段——敵我相持階段的極端嚴重的問題”,因為“在中國”,抗戰相持階段“是確保未失地并準備收復淪陷區的階段”;是“最積極的支持游擊戰爭”的階段;是“改革國內政治”的階段。
第二,毛澤東認為“破壞敵人計劃實現我們計劃”的前提是“了解敵人的情形”,從“研究中”找到“我們對付它的方法”,毛澤東認為這是現階段進行淪陷區研究的重要意義。他說:“在這個問題上,有敵人的一面與我們的一面。在我們的一面,是如何支持游擊戰爭的問題,研究這個問題,不待說是十分重要的。在敵人的一面,是敵人在淪陷區已經干了些什么并將要怎樣干,研究這個問題,乃是研究前一問題的起點。”毛澤東從理論上說明了研究淪陷區極端重要,那么“目前階段”中共方面對“敵人情形”的“了解”情況如何呢?毛澤東說:“可是在這個方面,在淪陷區中敵人干了些什么并將要怎樣干這個問題方面,抗戰干部中沒有研究或沒有系統研究的,乃是十人而九。這就指明:我們對于這個問題喚起注意的重要性與必要性了。”那么,如何才能解決中共缺乏“了解敵人情形”的干部問題呢?毛澤東提出學習、研究的方法論。
第三,毛澤東指出“研究一切重要的時事問題”的“科學方法論”,應“廢棄”“‘瞎子摸魚’,閉著眼睛瞎說一頓”這種作風,“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或者說,“研究時事問題須先詳細占有材料”。為此,延安組織了“時事問題研究會”,針對“日本問題、淪陷區問題、國際問題、抗戰中的中國問題”四大內容,開展“研究討論”。在此基礎上,“分別搜集材料”;“著手編輯”《時事問題研究叢書》;“用綜合文摘體裁”形成“材料書”“出版參考書”。毛澤東說:“現在出版的《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簡稱《日本在淪陷區》)”,是“研究淪陷區情況的第一本書”。該書一共3 編,第一編收錄“敵人在淪陷區的經濟侵略”,分為日寇經濟侵略概論、以及在東北、華北、華中和華南的經濟侵略、日寇搜刮民間物力、中國工業損失的總概算、海關被劫和日寇開發占領地之困難及其內部矛盾等章節;第二編為日寇在淪陷區的政治進攻,分為傀儡組織、奴化黨派、奴化教育、移民、征兵、宣傳和偽軍政策7 部分;第三編為日寇在淪陷區的暴行,分為日寇在東北、華北、華中和廣州的暴行4 章。從內容看,該書確實是一部“材料書”,收錄當時延安可以搜集到的公開出版資料。
第四,毛澤東特別強調,“這一類的時事問題叢書,僅僅是材料書,問題是沒有解決的”,因為“它是重要的材料,但僅僅是材料,而且還是不完全的材料”,因此須在“材料書”基礎上,更進一步,從“史料中引出結論”。他說:“要解決問題就須要研究,須要從材料中引出結論,這是另外一種工作,而在這類書里面是沒有解決的。”1○毛澤東進而提出,“這樣系統的研究時事問題”,是“為一切抗戰干部們供給材料”,并且,毛澤東強調這“實在是必要與重要的了”。也就是說,毛澤東認為包括《研究淪陷區》在內的時事問題研究叢書,針對的讀者群是“一切抗戰干部們”。那么,毛澤東為什么要將讀者群界定為“一切抗戰干部們”呢?
二、為一切抗戰干部們供給材料

1935 年12 月27 日,毛澤東發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指出從1931 年九一八事變開始,日本帝國主義就企圖將中國變成其殖民地,“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圍暫時還限于東北四省”;1935年華北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者野心膨脹,企圖“占領全中國”、企圖將全中國變成“日本獨占的殖民地狀態”,“威脅到了全國人民的生存”,給“中國一切階級和一切政治派別提出了‘怎么辦’的問題。反抗呢?還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兩者之間呢?”毛澤東斷言:“目前是大變動的前夜。黨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1○黨的任務由誰來擔當?毛澤東稱“我們的革命依靠干部”。這種觀點在1937 年5 月7 日發表的《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一文中有明確的體現。
毛澤東說:“我們在國內的任務,也從軍事的變到政治的。我們不需要陰謀詭計,我們的目的在團結資產階級和國民黨中一切同情抗日的分子,共同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為此,毛澤東強調“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毛澤東的理由是,第一,“在一個四億五千萬人的中國里面,進行歷史上空前的大革命”,領導者不能是“一個狹隘的小團體”;黨組織也不能依靠“一些委瑣不識大體、沒有遠見、沒有能力的領袖和干部”。第二,中共的革命經驗證明,“中國共產黨早就是一個大政黨”,“它有許多好的領袖和干部”,“但是還不夠”,“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干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第三,“干部”和“最好的群眾領袖”必須符合下列特征:“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于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第四,干部決定一切,學習培養干部。“我們無疑地應該學習這些東西,把自己改造得更好一些,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革命水平”,但是還不夠,“還要作為一種任務,在全黨和全國發現許多新的干部和領袖”。2○
偉大的革命需要偉大的黨,偉大的黨由許多最好的干部構成,但是,七七事變后的中共卻沒有那么多的“最好的干部”,1937 年10 月毛澤東坦稱,中共有四個“弱點”。第一是統一戰線不夠,“黨員對統一戰線的策略的了解也不深刻”;第二動員群眾的力量還薄弱,“黨員不能深入群眾中去”;第三,“組織力量的薄弱,落后于政治影響”;第四,“有獨立工作能力的干部缺乏”。為此,毛澤東指出,“應該依靠已得的陣地,糾正自己的弱點,發展我們的工作,使黨能在抗戰中起決定的作用”,“加強對干部的教育、培養與提拔,‘干部決定一切’”。3○在毛澤東看來,“抗戰干部”的教育、培養與提拔的實現途徑在于“學習”。
毛澤東以身作則,通過學習和研究,提升自我修養,成為“最好的干部”。據1937 年8 月從慶陽步校到達延安在毛澤東身邊的郭化若回憶稱:洛川會議前,“一天我去看他,他正在研讀《聯共黨史》。……主席說:‘不讀書不行呀,人家不是說我狹隘經驗論嗎?再說抗日戰爭有許多新情況、新問題要研究,沒有理論武器不行。’”4○同年10 月19 日,毛澤東在陜北公學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大會上講話,指出陜北公學的主要任務就是培養抗日先鋒隊。10 月23 日,他又為陜北公學題詞“要造就一大批人!”他說:“這些人是革命的先鋒隊。這些人具有政治遠見。這些人充滿著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這些人是胸懷坦白的,忠誠的,積極的與正直的。這些人不謀私利,唯一的為著民族和社會的解放。這些人不怕困難,在困難面前總是堅定的,勇敢向前的。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風頭主義者,而是腳踏實地富于實際精神的人們。中國要有一大群這樣的先鋒分子,中國革命的任務就能夠順利的解決。”5○

學習和研究可以造就“抗戰干部”,那么學習什么?向誰學習?如何學習?研究什么?1938 年10 月14 日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很好地回答了這些問題。第一,應當學習革命理論、學習歷史知識,研究實際運動。他說:“一般地說,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都要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和趨勢,并經過他們去教育那些文化水準較低的黨員。特殊地說,干部應當著重地研究這些,中央委員和高級干部尤其應當加緊研究。”第二,應當向民眾學習、向環境學習、向友黨友軍,甚至向敵人學習。他說:“共產黨員又應成為學習的模范,他們每天都是民眾的教師,但又每天都是民眾的學生。只有向民眾學習,向環境學習,向友黨友軍學習,了解了他們,才能對于工作實事求是,對于前途有遠見卓識。”第三,應當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問題相結合來學習。他說:“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境。……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第四,毛澤東指出,抗戰干部要善于“研究當前的運動”的特點和規律性,并得出“如何指導這個運動”的結論。也就是說,學習和研究的目的是為解決“實際問題”。“如何研究?用馬克思主義的工具——唯物辯證法。向誰研究?我們的先生多得很——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資本家、地主、日本帝國主義,還有全世界,他們都是我們的研究對象,同時又都是我們的先生。我們應該向他們或多或少的學到一點東西”。但是,毛澤東指出:“直到今天,我們還沒有懂得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部,也還沒有懂得中國的全部。運動在發展中,又有新的東西在前頭,新東西是層出不窮的。”1○
為弄清楚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的“全部”,就必須有學習和研究的資料,但是在延安這樣的資料實在太少了。1937 年底,毛澤東希望留在身邊研究抗戰軍事戰略的郭化若利用延安的“參考書”研究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毛說:“寫戰略,應找些必要的參考書看看,如黃埔的戰略講義,日本人的論內外線作戰,德國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蔣百里的《國防論》,蘇聯的野戰條令等,其他可能找到的戰略書,報紙上發表的抗戰以來論戰爭的文章通訊亦須搜集研究。先就延安城有的搜集(商借)來看。”結果,郭化若“按照主席的手令……跑遍了延安城各大學、圖書館,稍與戰略沾邊的書都找了來,雖有一定收獲,但仍感資料不足”。2○
到1939 年6 月時事問題研究會準備編輯時事問題叢書時,還是覺得“時事問題的材料書太少又不普遍,敵后方及我后方之僻遠地方找不到報紙刊物,為抗戰干部們明了時事問題與研究時事問題之一大苦悶”,為此,解放社“特從這本《戰爭中的日本帝國主義》起,用‘綜合文摘’的辦法,編輯關于日本、中國、國際三方面的時事問題材料,名曰‘時事問題叢編’,藉供抗戰干部們的迫切需要”。3○毛澤東《研究淪陷區》為序言的《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也是這樣一部“為一切抗戰干部提供材料”的資料書。
三、用“科學方法論”解決淪陷區問題
在《研究淪陷區》一文中,毛澤東特別強調抗戰干部學習和研究材料書必須運用“科學方法論”,解決實際問題。那么,1939 年10 月1 日前后,中共面臨的實際問題是什么?毛澤東為何在抵達延安后學習唯物史觀?研究軍事戰略?撰寫《論持久戰》?提出“淪陷區研究刻不容緩”?楊奎松《毛澤東為什么要寫〈論持久戰〉?》一文很好地回答了前三個問題,筆者不再贅言,僅就“淪陷區研究刻不容緩”這一問題,再作深入剖析。
毛澤東在1938 年10 月14 日《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將中共黨內存在的脫離中國實際的觀點和做法的國際主義定性為“應該認真地克服”的“嚴重的錯誤”,他說:“把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分離起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做法,我們則要把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隊伍中存在著的一些嚴重的錯誤,是應該認真地克服的。”4○這種錯誤是什么?按照楊奎松的論述,指的是1937 年12 月9—12 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明等帶著莫斯科的指示精神,以“國際主義”觀點直截了當否定了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提出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的對日作戰戰略和毛澤東爭取領導權和保持獨立性的說法。5○正是在此次會議后,毛澤東要求他的軍事參謀郭化若好好研究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以“批駁這種觀點”。郭化若回憶稱:“全面抗戰展開后,全國各階層思想很活躍,除了失敗主義者散布的‘亡國論’和性急的朋友議論‘速勝論’外,在中國共產黨內和一部分群眾中,還有輕視游擊戰爭的傾向,只把希望寄托在正規戰爭上,或者寄托在國民黨軍的作戰上。”6○在抗戰相持階段,按照毛澤東的判斷,日軍的進攻由軍事進攻轉變為政治進攻和經濟進攻,更加容易引起“亡國論”,消弭淪陷區的抗日決心。為破解這種狀況,毛澤東強調用“科學方法論”,即在“唯物史觀”指導下,將“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兩者“緊密地結合起來”,在淪陷區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將抗戰出路告訴淪陷區的民眾。毛澤東將這種“科學方法論”指導下的淪陷區堅持抗戰的路徑,稱為“畫‘豆腐塊’”。

1938 年3 月3 日在陜北公學畢業送行會上,毛澤東明確提出“城市速決戰日本可以取得勝利,鄉村持久戰是我們取得勝利”的觀點。他說:“有個青年從長沙寫信來說:‘中國必亡。設若武漢失掉,則大塊地方都完了,還有什么辦法?’我說,我們陜北公學同學出去一定有辦法,辦法就是畫‘豆腐塊’,在大路附近畫‘豆腐塊’。在‘豆腐塊’邊上我們暫時沒有辦法,因為那是大路、大城市,被日本據有優勢武器的兵種占領著,這就是說,‘中國不是亡國,而是亡路’。日本得到了城市、大路的速決戰,也就得到了鄉村、小路的持久戰。比方,陜北延安被占領了,我們就會在其他小塊,無數鄉村,無數小路打持久戰。”毛澤東進而要求畢業生們到敵后去堅持游擊戰,畫“豆腐塊”。他說:“這次你們畢業后要分兩部分去工作,一部分在后方發展民運工作,另一部分要到‘豆腐塊’里去。也許有人怕去畫‘豆腐塊’。”為此,他特意舉了聶榮臻在五臺山“創造了一支二萬五千人的大隊伍”的成功案例激勵大家,毛澤東說:“我們要把這個例子告訴全國被占領或將被占領的區域的人民,使他們看到抗日的辦法與出路。我們堅決反對被占領區域沒有辦法的說法,在這方面我們還可以講講十年內戰時期許許多多的經驗。”1○這就表明,毛澤東認為在“被占領或將被占領的區域”,運用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略是堅持抗戰的根本出路,有力地鼓舞了陜北公學畢業的抗戰干部們的抗戰信心和決心。
在淪陷區堅持抗戰,一方面必須“畫‘豆腐塊’”,另一方面還要開展“輿論戰”。在《論持久戰》發表后大約3 個月后的1938 年10 月12 日至14 日在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做了《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報告,明確用“新階段”概括抗戰的最新階段與特征。毛澤東指出:抗戰相持階段的到來即是“新階段”,“新階段中,正面防御的是主力軍,敵后游擊戰爭將暫時變為主要的方式”,“只要有廣大的敵后游擊戰爭存在”,“只要我們的抗戰堅持下去,日本的這條可憐命運是大體確定了的”。毛澤東認為在新階段“高度發揚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克服一部分人的悲觀情緒,堅決擁護政府繼續抗戰的方針,反對任何投降妥協的企圖,堅持抗戰到底”這一任務,“比過去任何時候為重要”。為此,他提出對日發動“輿論戰”。毛澤東說:“運用一切宣傳手段,報紙、刊物、學校、宣傳團體、文化藝術團體、軍隊政治機關、民眾團體,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向前線官兵、后方守備部隊、淪陷區人民、全國民眾,作廣大之宣傳鼓動,堅定地有計劃地執行這一方針,主張抗戰到底,反對投降妥協,清洗悲觀情緒。”為更好達到這一目標,毛澤東同樣認為“輿論戰”必須堅持“科學方法論”,從三方面同時下手:第一方面,“利用已經產生并正在繼續產生的民族革命典型(英勇抗戰、為國捐軀、平型關、臺兒莊、八百壯士、游擊戰爭的前進、慷慨捐輸、華僑愛國等等)”,向前線后方國內國外,廣為傳播;第二方面,“揭發、清洗、淘汰民族陣線中存在著與增長著的消極性(妥協傾向、悲觀情緒、腐敗現象等等)”;第三方面,“將敵人一切殘暴獸行的具體實例,向全國公布,向全世界控訴”。就“當前”而言,毛澤東認為應該“設立一定機關,系統的收集一切敵軍暴行,制成具體的文書、報告,宣揚國外,喚起全世界注意,起來懲罰日本法西斯”。2○
由此可見,針對淪陷區存在的“亡國論”,毛澤東堅持運用“唯物史觀”,認清抗戰新階段,堅持敵后游擊戰爭;運用“輿論戰”,反對投降妥協、清洗悲觀情緒、堅定抗戰決心。應該說,這是毛澤東主張學習和研究時事問題的初衷,也是時事問題叢書編纂的初心,更是他主張用“科學方法論”解決淪陷區實際問題的方法論。
1943 年8 月2 日,周恩來說:“我們黨在這三年做了比過去二十年還要偉大還要有更多成就的工作。對全國說,我們黨兩度制止了內戰的危機,堅持了敵后最艱苦的游擊戰爭,堅強了八路軍、新四軍的領導及各抗日根據地的撐持。因此穩定了淪陷區人民的抗日情緒和意志,維系了大后方對抗戰前途的信心和希望。……有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和指示,在這三年來許多緊急時機、許多重要關鍵上,保證了我們黨絲毫沒有迷失了方向,沒有走錯了道路。沒有比這三年來事變的發展再明白的了。過去一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同志領導或其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尾的證明其為錯誤了。我們黨22 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串著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1○周恩來的這段話,高度肯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和指示,在緊急時機、危難時刻、重要關鍵上,指導了敵后游擊戰爭、保證了穩定了淪陷區人民的抗日情緒、維系了大后方對抗戰前途的信心和希望,也對毛澤東1937 年底—1939 年底2 年左右的學習和研究唯物史觀、學習和研究抗日軍事戰略、學習和研究時事問題,更對1939 年10 月1 日毛澤東《研究淪陷區》一文的重要歷史貢獻,做了高屋建瓴的總結。
毛澤東《研究淪陷區》這篇短文,某種程度上可以稱為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共研究淪陷區問題的開山之作,其所主張的堅持“唯物史觀”指導,運用“科學方法論”,根據“調查”,正面直視抗戰時期的淪陷區問題,收集有關淪陷區的各種檔案資料、研究中國共產黨在淪陷區的抗戰策略和史實、研究日本帝國主義在淪陷區“干了什么和即將干什么”、研究淪陷區存在的“亡國論”及其具體表現、研究有關淪陷區苦難和抗爭的輿論等,既指出淪陷區研究必須充分掌握各方史料,尤其是“對手方”的史料;又明確淪陷區研究必須堅持“抗日戰爭”這一對中華民族而言無庸告別的“民族主義”立場;亦表明了淪陷區研究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讓史實說話、讓歷史發言”的科學方法論。對于今后的淪陷區研究而言,這樣的路徑與方法,顯然具有重要的“范式”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