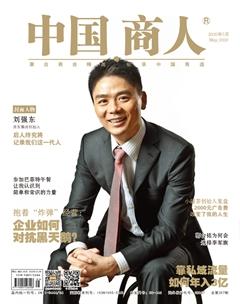小罐茶創始人復盤:2000元廣告費改變了我的人生
杜國楹

我生于1973年,今年47歲。1994年年底我離開河南,自此之前我在河南生活了22年。1995年我被派到天津,在天津待了四年半,1999年來到北京。
這47年大概可以分成6個階段:
第一階段,我是一個被嚇大的孩子,人生的第一個20年我是跟父母在一起度過的,個性可能跟我的父母和家庭關系非常大。
第二階段,我是一個不安分的老師,大學畢業之后教了兩年書,這是一段重要的人生經歷。
第三階段,我是一個當了銷售冠軍的打工仔,雖然我只打過兩年工。很多人問我,上世紀90年代,我從月薪151元怎么變成年收入50萬元的?就是這兩年打工的銷售獎金。
第四階段,我經歷了一段人生從巔峰到谷底的過程,這是到目前為止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經歷,在第一次創業過程中,我很早就坐了“過山車”。
第五階段,是一發不可收拾的連續創業。“過山車”坐完之后到現在,幾次創業其實是連續的順勢而為。
第六階段,一項后半輩子的事業。
我的商業生涯和人生的最終夢想到底是什么,我一直在不斷地問自己。今天,我把人生中的這六個階段一起分享給大家。
勤奮成為我的一種習慣
一直到今天
90后的孩子應該很難理解什么是“被嚇大”的。我家是傳統的“一工一農”家庭,這樣的家庭現在很少見。如果我爸爸還在,今年已經90歲了,我們兄弟姊妹有五個,我是最小的一個,大哥比我大19歲。
上世紀50年代,我父母結婚的時候,一個在城里一個在農村。我父親是典型的傳統家長作風,每次他從外面回家,咳嗽一聲,我母親都不敢說話。
我小時候學習好,從我記事開始,如果考了第二名就是意外。因為我害怕,如果我考不好被我父親知道了,我母親會受牽連。從上學,到教書,到打工,到創業,幾乎無一例外,我必須是第一,沒有第二。就這樣,勤奮成為一種習慣,一直到今天。
二十多年來,我曾帶過無數人跟我一起創業,所有這些團隊里誰最勤奮,誰最拼?20年前是我,20年后還是我。在我的公司里,無論是管理層還是普通員工,只要他仔細觀察半個月或一個月,就可以發現,這個公司沒有人比我更勤奮。
勤奮是一種習慣,第一也是一種習慣。我的這一習慣與幼時對父親的恐懼有很大關系。盡管從小我沒有挨過我父親一個耳光,因為我學習最好、很乖。但我是被嚇大的,因為怕挨打,自己變得靠譜了。
除了勤奮,我的家庭還給了我正直善良的傳承。我小的時候放暑假、寒假時會跟我母親一塊去城里找父親。有一個畫面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我們離開的時候,父親會把我們所有的包全部檢查一遍,確保廠里的一顆螺絲釘都沒有被帶走。
逢年過節,有親戚朋友到我家來玩,父親會把好吃的、好喝的都拿出來招待客人,只要客人一走就會鎖進柜子,不讓自己的孩子碰。
當年我下海的時候是偷偷走的,我父親不知道,我沒敢告訴他。此前,我一直也不理解我父親為什么對我們這樣刻薄與嚴厲,雖然我接受,但內心是極度想反抗的。
后來我發現,我所具有的拼勁同身邊的人不太一樣,我才意識到這種品質對我一生的價值。第一個項目做起來之后,1998年春節回家吃年夜飯,我喝多了,撲通一下跪在我父親面前,告訴他,我第一次深刻地理解了他對我幼時的教育,流著眼淚,發自內心地感激他的刻薄與嚴厲。
如果說我母親給了我善良的本性,那么我父親就給了我勤奮、正直和舍得的品質,這些品質讓我終身受益。
一個不安分的老師
我從師范學院畢業之后,教了兩年書,是初三的化學老師。在大學讀書時,我是宣傳部部長,學校發現這個小伙子極有激情,所以一畢業就安排我當了初三的班主任。
教書的時候,說實話,我內心無比地熱愛教育,但是每月的工資只有151元,盡管我有著狂熱的事業心,工作做得也還不錯,但卻還要繼續“啃爹”。我的內心實在是不甘,難道我的一生就要這樣嗎?我已經看到了未來,這個未來跟我曾經想象的工作、事業、人生不太一樣,我不甘心就這樣過一輩子。于是,我萌發了離開的念頭。我偷偷地不辭而別,我們家只有我母親知道。我想,“干不好我絕不會再回來”。
一個當了銷售冠軍的打工仔
1995年2月17日,我來到了天津。我人生中,每一個歷史性日子我都記得很清楚,我到天津的第一天是1995年2月17日,開始做茶是2012年6月20日,隨時隨地都能想起來。
有一家公司讓我去接替天津辦事處的經理。當時整個天津地區的月銷售額是7000元,公司給了我一輛自行車、一間小平房,算是辦事處。每月工資350元,比我當教師時翻了一番多,還是不錯的。
最初,我接手了大概不到10個銷售終端。我想這不行,10個終端加一個平房怎么能夠賣貨呢?必須接著鋪貨。從1995年2月17日到7月15日,我跑了5個月,大概鋪到100個終端左右,銷售額漲到了17000元。
但是我很快發現,終端的銷售效率在下降,貨有點賣不動了。
1995年7月15日,是我人生一個重要的改變節點。我所有關于營銷的理解,都是從這一天開始的,2000元廣告費改變了我的人生。
那一陣子,我經常躺在床上納悶,租的宿舍也沒有電視,只有一臺收音機。晚上睡不著的時候我就聽廣播,結果發現廣播里能做廣告。此前,我們曾去打聽過電視廣告的價格,太貴了。天津的報紙廣告我們也做不起,一個月只有1萬多塊錢的銷售額,隨便打一個廣告就要一兩萬,老板也不會同意。

我想,電臺的廣告應該會便宜,就去問了一下,一次2000元。但公司依然沒有先例,大概6月底的時候我向老板申請,要2000元廣告費,7月份終于批了。7月15日晚上,電臺播了一次廣告。
如果你能查到歷史上的天氣記錄,肯定知道1995年7月16日早上,天津瓢潑大雨。早上一睜眼我就絕望了,心想壞了,這一次廣告白做了。夏天的暴雨大得看不見人,我干脆躺在床上,沒下床。
到了10點多,BP機響了。我想,這時候怎么還會有人找我?我去胡同口的公共電話亭里回了電話,是天津市百貨大樓一樓的樓層經理呼我,他說:“小杜趕快來,商場里你公司的柜臺前排著隊呢。”
我穿上衣服就到了公交車站,我的住處離百貨大樓很近,一站地。到那一看,整個商場沒有人,一樓我們的柜臺前排起了長龍。
我的人生就從那一天開始改變。此前我從來不知道廣告的威力,突然發現產品還是那個產品,努力了四五個月,月銷售從7000元干到了17000元,做了一次廣告,第一天銷售額就到了二三萬元,已經超過了過去1個月的銷售額。
那一天讓我對營銷和傳播有了全新認識。同樣一個東西,過去也很努力,但就是賣不掉,只因為缺少傳播,打過廣告之后,變化如此之大,讓我非常震撼!
從那時起到1996年12月我離開的時候,一年半時間,產品的月銷售額達到了298萬元,全國第一。那家公司全國所有省會的辦事處經理,都至少去天過津兩次以上,在當地學習。
1996年底,我創業去做背背佳,清算之后公司一次性付給我49萬元獎金,這是我的第一筆創業資金。
一段從巔峰到谷底的人生
創辦背背佳,意味著我人生一個新歷史階段的開始,這是一段從巔峰至谷底的過程。
1997年初,我用50萬元注冊了這家公司,天津壹品科技。因為我當過老師,所以我很自然地關注到了家長對孩子坐姿的擔心和這方面的市場需求,背背佳代替的是家長的提醒。這次創業,我要做全國市場,就走向了電視。事實上,電視廣告跟用戶的溝通邏輯,與電臺廣告是一樣的。到1998年,背背佳實現了全年4個多億的銷售,年底我們帳上趴了1.2億元現金。
通過電臺廣告,我每月7000元的銷售額變成290萬元;通過電視廣告和營銷,一年又干到4個多億。這時,我覺得營銷無所不能,是一個典型的、徹頭徹尾的營銷主義者。
當年,我第一次打廣告時沒有錢,從老板那里申請了2000元經費;第二次做背背佳也只有50萬元,不敢大折騰;1998年,帳上趴著1個多億,我決定要大手筆投入,于是做了一款矯姿內衣的產品,在全國大打廣告。
那是上個世紀90年代,我們拍一條廣告片花了800萬元,把韓國最好的女子組合Baby Vox請來做代言;生產端也沒做測試,一備貨就備了好幾千萬。我想,我的水平還用測試嗎?不需要,我看準的,必成!
結果,廣告打下去掉坑里了。我不甘心,又做了其他產品,繼續打廣告,連續三次,直接死掉。2000年底,大概只用了兩年時間,三個大手筆投入的項目均以失敗告終,我直接破產了。
我欠了經銷商4600萬元外債。創業以來,我從來沒有向銀行貸過款,都是經銷商把款打給我,我發貨。貨沒賣出去被退回來,我的錢也花了,只能給經銷商打欠條。
那時候我手機一天24小時開機,急得頭上長了三處至少有一塊錢硬幣那么大的斑禿。每個月掙的錢全都還債,一直還到2003年,只還了不到1000萬元,我非常痛苦。
那是年輕時代的狂躁,覺得我就是天下第一,什么都可以改變,一切皆可顛覆,不尊重常識。經歷這件事后,我明白了商業的本質我們顛覆不了,所有的顛覆都只是形式,哪怕有1萬種、10萬種變化,底層邏輯變不了。
1998-2003年這段時間,至今仍是我人生最寶貴的經歷。我意識到,廣告是好產品的放大器,也是壞產品的加速器。一個人掉坑里,再走出來的時候,才知道別人在課上無數次跟你講過,與你自己親身經歷過完全是兩碼事。
很多人曾問我,現在怎么看這段經歷?我說:“來得早!來得徹底!來得刻骨銘心!”沒有這次經歷,就沒有我的今天。如果我在今天,40多歲接近50歲的時候,才第一次有這樣的經歷,我真不一定能再起得來。二十幾歲的時候,一人吃飽全家不餓,沒結婚,父母也可以不管,對失敗的承受能力相當強。但如果是今天這個年紀,承擔的壓力就太多了,失敗對一個人的摧殘,比你年輕時要痛苦得多。
從下海到破產,再到把帳還完,我用了8年的時間,完成了創業的第一個閉環。
一發而不可收拾的連續創業
第一次失敗之后,我又先后創業好記星、E人E本、8848手機,一直到做了小罐茶。今天,小罐茶之前所有的公司我都已經賣掉,產權上跟我幾乎沒有關系了,最早的背背佳十幾年前就已經跟我沒有關系,茶葉是我后半輩子的事業。
在別人眼里,這些是我一次次創業的成功,在我自己心里,這是一次次夢想的破滅。沒有人生下一個孩子是為了賣孩子,每個項目都是我的孩子。最后沒辦法,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我們做出賣的選擇。
當然,今天新一代的創業者,可能從第一天開始就有賣公司的計劃。但是我相信,每一家公司、每一個品牌、每一段創業經歷,成長的背后,都有一份難以割舍的情感。真正賣公司的時候,非常痛苦。
在我賣掉一家公司之后,如果這家公司有任何事需要我,我都會隨叫隨到,甚至會推掉現在公司的事情,為以前的公司無償出力。因為我覺得他們是沒有爹的孩子,我有愧疚感。每次我都要用兩三年的時間才能走出這種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