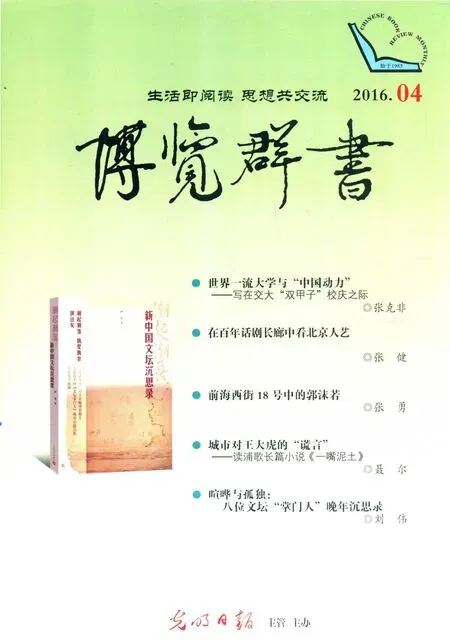《戀愛的犀牛》:劇場之小與人氣之大
劉平
新時期以來,小劇場話劇的創作與演出出現了“紅火”勢頭,其原因,一是小劇場話劇適應時代要求,滿足觀眾審美要求;二是小劇場話劇創作風格多樣,顯露出強勁的探索、實驗的勢頭;三是小劇場話劇演出運作方式靈活,多以自由組團演出為主,票房收入可觀。
中國的小劇場話劇誕生于20世紀20年代,最有名的是田漢1927年在上海成立的“南國社”,曾演出過《蘇州夜話》《南歸》《湖上的悲劇》《名優之死》等話劇,影響遍布大江南北。解放后小劇場話劇曾沉寂了幾十年,至上世紀80年代初在中國舞臺上再次興起,以《絕對信號》《屋外有熱流》等為代表,立即受到戲劇界的熱情關注,也受到觀眾的歡迎。此后,小劇場話劇的創作勢頭發展旺盛,已成為整個話劇創作的重要一翼。受此影響,民營話劇社團也大量出現,其話劇作品影響了大量年輕觀眾,同時也為話劇事業發展培養了一批編劇、導演、演員等方面的人才。
但是,有一個問題始終沒有得到很好地解決,即與觀眾的關系問題。對于那些相對比較寫實的小劇場話劇作品,觀眾比較喜歡,也容易接受,而那些實驗性很強的劇目,大多數觀眾并沒有完全接受。有人說,實驗戲劇是“小眾戲劇”,沒必要考慮觀眾的接受問題。漸漸地,大多數觀眾便離“實驗的”小劇場戲劇越來越遠了。但《戀愛的犀牛》的出現卻讓觀眾眼前一亮,由此也促成了實驗戲劇創作者觀念上的轉變。
/壹/
《戀愛的犀牛》是一臺由民營話劇社團——孟京輝戲劇工作室創作演出的小劇場話劇,編劇廖一梅,導演孟京輝。該劇1999年首演,一經上演便收獲很好的口碑,創下了連演40場、場場爆滿的奇跡。2011年,該劇參加文化部在上海舉辦的“全國小劇場優秀劇目展演”,觀眾反響強烈,獲得優秀劇目獎牌。至2012年該劇已演出1000場,成為新時期以來小劇場話劇的一部經典作品。
《戀愛的犀牛》的成功,與導演孟京輝的戲劇觀有直接關系。孟京輝被稱為“先鋒戲劇”導演,他說:
實驗戲劇不排斥商業性,我覺得那種專門排給外國人看,讓那些似懂非懂的洋鬼子給頒個獎,或者到國外藝術節轉一圈,回來演出都沒人看的戲沒什么價值。以前,我也愿追這個時髦,或者弄一些讓人看不懂的戲,看著觀眾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的樣子,心里還無比快意。后來我才覺得,戲劇必須是觀眾能迅即了解,即刻感受并產生共鳴、共同創造的藝術。以前為了自己個人的需要,沒有考慮觀眾的戲現在看來沒什么意義。(《北京晚報》1999年6月4日)
然而,此前孟京輝的創作觀念并非如此。他排演《禿頭歌女》時,在演出快要結束時,突然停頓三分鐘,觀眾也不知發生了什么事。他說:“當時就是想和觀眾較勁,我就是不讓你好好欣賞。”1997年,孟京輝獲得日本一個獎學金,在日本看了很多戲,對他啟發很大,回來后,創作觀念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他說:
我感覺我需要一種更多人的交流,但是在和更多人進行交流的時候,不可能完全像以前那樣很任意、很任性。你必須將很任性的東西,在美學上讓更多的人接受。更多的人其實是支持你的人,沒有這些人你就無的放矢了。我感覺,我的先鋒、前衛就表現在和更多人接觸上。
(孟京輝、解璽璋:《關于“實驗戲劇”的對話》,《劇本》1999年第10期)

《戀愛的犀牛》就是他在這樣的創作思想指導下創作的。
《戀愛的犀牛》是一出實驗戲劇,講述了兩個愛情偏執狂在愛的欲望旅程中所發生的故事。劇中的男主角馬路是犀牛飼養員,愛上了性感神秘、做秘書工作的女孩明明。為了獲得明明的歡心,馬路為她做了能做的一切,并努力地改變著自己。比如天天洗澡、換襪子、學電腦、獻花、嚼口香糖……以至對其他的女孩都失去了興趣,為此受到同伴的嘲笑,說他過分夸大了一個女人和另一個女人之間的差別,在人人都懂得明智選擇的今天,他仿佛是人群中的犀牛——實屬異類。可明明并不愛馬路,她心里愛的是藝術家陳先,盡管陳先并不愛她,不斷地羞辱她、折磨她,都不能改變她愛他的決心。但馬路的愛也不能改變明明對他的冷漠態度。看得出來,《戀愛的犀牛》的作者講這個故事并不在于關注馬路與明明的戀愛結果,而是在嘲笑一切的世俗觀念而贊美這種執著于愛的精神。
/貳/
該劇的成功與孟京輝的導演風格有很大關系。孟京輝是一個很有個性的導演,其導演風格常常是從追求形式感出發,以形式裹挾內容,在舞臺上展現一種形式美,并在關注社會現實的過程中與時代保持著一定距離,用反諷、黑色幽默和激烈的手法,在戲中體現出一種詩情和激情,表現出一種反抗,使作品產生一種具有爆發力的“狠”勁兒,吸引觀眾來參與。《戀愛的犀牛》的演出就體現著他的這種藝術風格,整個演出集戲劇、音樂為一體,強烈的形式感,夸張的表演,幽默、戲謔的語言,既是前衛的,又是現實的。張廣天為這個戲寫的幾首歌,既加強了該劇的音樂性和節奏感,也有助于故事的表達,渲染了劇中的情緒,感染著觀眾去思考并產生共鳴——
這是一個物質過剩的時代,
這是一個情感過剩的時代……
我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我們有太多的東西要學,
我們有太多的聲音要聽,
我們有太多的要求需要滿足。
這首歌經由郭濤(飾馬路)那質樸無雕琢的嗓音唱出來,比一般的流行歌曲更耐聽。它不僅渲染了劇情,而且也感染著觀眾,使原本一個普通的愛情故事具有了吸引觀眾的藝術感染力。
愛情是蠟燭,給你光明,
風兒一吹就熄滅。
愛情是飛鳥,裝點風景,
天氣一變就飛走。
愛情是鮮花,新鮮動人,
過了五月就枯萎。
愛情是彩虹,多么繽紛絢麗,
那是瞬間的騙局,太陽一曬就蒸發。
愛情是多么美好,但是不堪一擊。
聽著這樣的歌,聯想到自己,看看周邊的人們與家庭,人們會情不自禁地去思考劇中發生的一切,品評劇中的人物,頓時會產生一種感同身受的情緒。
當明明對馬路展示了一點兒好的臉色,馬路就突然詩性大發——
一切白的東西和你相比都成了黑墨水而自慚形穢,
一切無知的鳥獸因為不能說出你的名字而絕望萬分
…… ……
你是不同的,唯一的,柔軟的,干凈的,天空一樣的,
你是我溫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
帶著陽光味道的襯衫,日復一日地夢想。
你是純潔的,天真的,玻璃一樣的,
你是純潔的,天真的,什么也污染不了,
你是純潔的,天真的,什么也改變不了,
陽光穿過你,卻改變了自己的方向。
我的愛人,我的愛人,我的愛人,我的愛人……
正是這樣近似瘋狂的摯愛情緒,讓馬路做出了非凡的舉動。馬路為對明明表達真心不但把自己買彩票中獎的500萬送給明明,還親手殺死了自己心愛的犀牛,把犀牛的心獻給明明。可是,明明都毫不猶豫地拒絕了。于是,馬路便以愛的名義綁架了明明,“不準她離開自己”。
/叁/
郭濤的表演特別值得一提。憨頭憨腦的馬路,為討好明明笨手笨腳地學打字,嘴里咀嚼著明明愛吃的那個牌子的口香糖,為向明明表白心跡而殺死心愛的犀牛,以至最后粗暴地綁架明明以達到自己的目的。郭濤以質樸的形象,毫不做作的表演,把一個犀牛一樣的偏執的人——馬路的個性表現得淋漓盡致,以至有人感到他似乎就有犀牛一樣的性格,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戀愛的犀牛》自1999年首演后又有過多個演出版本,甚至演到了首都劇場的大舞臺,至今仍然常演不衰。2012年8月7日至8月12日,《戀愛的犀牛》在保利劇院以13年來的五版演員陣容完成它的千場紀念版演出。該劇還被翻譯成英文、意大利文、羅馬尼亞文、韓文,每年都在世界各地的劇團和民間劇社上演,更是全國高校劇團排演最多的一出戲。
《戀愛的犀牛》演出的成功,無疑鼓舞了那些熱衷于實驗戲劇創作、又被觀眾問題所困擾的戲劇人。這之后民營話劇團體不斷涌現,除此前出現的牟森的“戲劇車間”、林兆華戲劇工作室、鄭錚的“火狐貍劇社”、蘇蕾的“星期六戲劇工作室”和上海的現代人劇社等外,又出現了李伯男導演工作室、戲逍堂話劇工坊、盟邦戲劇工坊、三拓旗劇團、龍馬社、田沁鑫戲劇工作室、黃盈工作室、陳佩斯的大道文化公司等,創作演出的劇目也逐年增多,接連出現了《非常麻將》(李六乙編導)、《情感操練》(火狐貍劇社)、《切·格瓦拉》(黃紀蘇等編導)、《玩偶》(程博峰編導)、《我不是李白》(盟邦戲劇工坊)、《有多少愛可以胡來》(戲逍堂)、《剩女郎》(李伯男)、《隱婚男女》(李伯男)、《托兒》(陳佩斯大道公司)、《圓明園》(張廣天編導)、《單身公寓》(上海現代人劇社)、《花事如期》(龍馬社)、《兩只狗的生活意見》(孟京輝導演)等,其演出都收到了比較好的劇場效果,對新時期話劇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