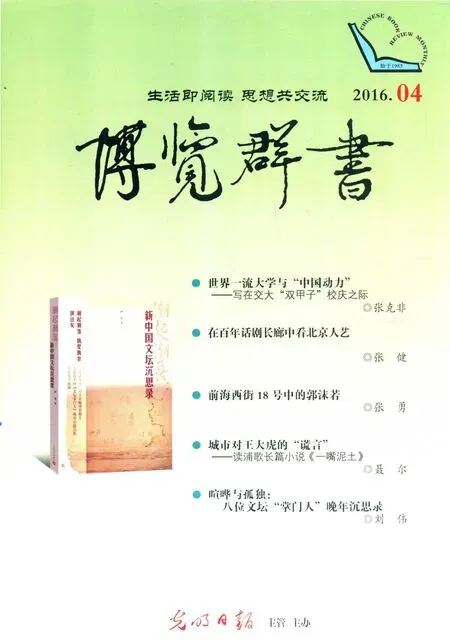韓愈與“抑遏蔽掩”之美
劉寧
北宋蘇洵對(duì)韓愈古文有一個(gè)非常著名的評(píng)價(jià):
韓子之文,如長(zhǎng)江大河,渾浩流轉(zhuǎn),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近視。(蘇洵《上歐陽內(nèi)翰第一書》)
很多深入韓文三昧的人,也從各種角度回應(yīng)蘇洵的見解。明代茅坤認(rèn)為韓文渾涵,勝過“卓犖峭直處,太露氣岸”的柳文(《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十九);清代文論家儲(chǔ)欣稱贊韓文“俯仰呼應(yīng)處,深意頓挫”(《唐宋八大家類選》卷十);余誠(chéng)則認(rèn)為韓愈“筆意曲折渾涵,絕不輕露”(《古文釋義》)。
/壹/
蘇洵所謂“抑遏蔽掩”,究竟具有怎樣的內(nèi)涵,為什么后世論者以此為韓文妙境而傾心不已?力大思雄的韓文,有著長(zhǎng)江大河一樣奔涌的氣勢(shì),這條大河又在什么意義上,讓人感到深沉與含藏?這是很值得思考的問題。事實(shí)上,誠(chéng)如歷代論者所言,如果沒有這種深沉而徒逞氣勢(shì),韓文就不成其為韓文,就不會(huì)成為有著強(qiáng)烈感染力、深受推重的文章典范。
“抑遏蔽掩”的特點(diǎn)是“不使自露”,這意味著鋒芒的收斂與含藏,然而韓愈的文章其實(shí)是很有不平之氣的,他把自己的不少作品稱為“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上宰相書》)。他為自己與天下志存古道之士的有才無位而憤郁、而不平。《進(jìn)學(xué)解》《送窮文》兩篇“是最典型的代表。此外,他的許多書、序、墓志銘、祭文、廳壁記等,也常書寫志士坎坷之悲。表面上看,這種不平之氣,似乎是對(duì)《離騷》失路之悲、不遇之嘆的繼承;但仔細(xì)體會(huì),兩者還是有顯著的不同。屈原對(duì)自己忠心被謗,懷才失位的遭遇表達(dá)了強(qiáng)烈的不滿。《離騷》,對(duì)讒毀之小人有著無比的憎恨與憤怒。詩(shī)意激揚(yáng)澎湃,鋒芒畢露。然而韓愈的不平之鳴,卻常常出之以吞抑的筆墨。他的《進(jìn)學(xué)解》全從自嘲落筆,說自己“學(xué)雖勤而不由其統(tǒng),行雖修而不顯于眾”,感嘆自己能過上“月費(fèi)俸錢,日糜廩粟,……乘馬從徒,安坐而食”的生活,就足以慶幸,決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在《送窮文》中,他刻畫窮鬼糾纏自己的無賴之狀,道盡對(duì)其驅(qū)而難去的窘迫:
凡此五鬼,為吾五患。饑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fù)然。蠅營(yíng)狗茍,驅(qū)去復(fù)還。
這些自嘲的筆墨,迥異于屈原自述身之察察的自信筆致。韓愈還有許多狼狽無助的身世之嘆,例如《答李翱書》云:
仆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于人,以度時(shí)月。當(dāng)時(shí)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dāng)痛之時(shí),不知何能自處也。……嗟乎,子之責(zé)我誠(chéng)是也,愛我誠(chéng)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已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dú)安能使我潔清不污,而處其所可樂哉?非不愿為子之所云者,力不足勢(shì)不便故也。
面對(duì)李翱這位最好的朋友,韓愈道盡自己的無能、無力與無助。這個(gè)汩沒于人生世路、難以“潔清不污”的詩(shī)人形象,完全不似屈原那樣高潔孤傲、纖塵不染。當(dāng)然,如此的自嘲、自嘆之語中,還是有著奇崛不平之氣,是以自嘲來嘲世,然而筆意的曲折頓挫,讓憤激的鋒芒變得沉郁。
/貳/
要進(jìn)一步理解韓文鋒芒的含藏,就要特別體會(huì)他申發(fā)“不平則鳴”之說的《送孟東野序》。這篇為孟郊鳴不平的文章,其立意取向和楚辭也是頗為不同的。孟郊50歲方才科舉及第,不久被任命為溧陽尉,他帶著難以排遣的失意即將赴任,臨行之際,韓愈以此文來勸慰他。如果用《離騷》式的筆法,這樣一篇文字,往往會(huì)直斥讒佞之當(dāng)?shù)溃袘嵱兴局还n愈全不措意于此,而是氣勢(shì)磅礴地申發(fā)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一段宏大的議論: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fēng)撓之鳴;水之無聲,風(fēng)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文中的“不平則鳴”,究竟是專指坎懔愁怨、憤激不平,還是既包括憤激愁怨,也包括“鳴國(guó)家之盛”的歡樂之鳴,歷來論者頗有爭(zhēng)議。持前一種觀點(diǎn)的,如何焯在《義門讀書記》中說:“吾終疑‘不平則鳴四字與圣賢善鳴及鳴國(guó)家之盛處,終不能包含。”持后一種觀點(diǎn)的,以錢鍾書為代表,他說:“韓愈的‘不平和‘牢騷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憤郁,也包含歡樂在內(nèi)。”(《七綴集·詩(shī)可以怨》)前一種觀點(diǎn)有很大影響,但如果從行文本身來看,顯然后一種觀點(diǎn)更符合文義,韓愈并沒有明確將歡樂之鳴排除在外。這就引出一個(gè)問題,既然韓愈寫作此文的目的是寬慰孟郊心中的愁悶,那么他在開篇長(zhǎng)篇鋪敘這一段喜憂兼具的不平則鳴,其間所包含的“歡樂之鳴”豈非離題和冗贅?有學(xué)者就對(duì)此表達(dá)過疑惑,認(rèn)為這么一大段議論,游離了為孟郊失意之悲而感憤的主旨,是韓文立論有失嚴(yán)謹(jǐn)之處。(參見周振甫《怎樣學(xué)習(xí)古文》)
其實(shí),韓愈文中所說的“不平則鳴”,不過是對(duì)人心興發(fā)感動(dòng)、觸物起情這一傳統(tǒng)的認(rèn)識(shí),做了別致新穎的表達(dá)。無論憤激還是歡樂,都會(huì)讓人心動(dòng)而鳴。韓愈是要以宇宙萬物興發(fā)感動(dòng)這種普遍的現(xiàn)象,來樹立高絕而神圣的天命,其不局限于愁怨而著眼于萬物興感的常情與一般,正體現(xiàn)出立論的宏大。他認(rèn)為,志士的價(jià)值在于與天命相合。他所希望于孟郊的,是要將個(gè)人安頓在這個(gè)偉大的天命之下。韓愈不無傲岸地指出,在歷史上,只有最優(yōu)秀的人,才最善鳴,也才最能體現(xiàn)天命,而魏晉以下之人,“其聲清以浮,其節(jié)數(shù)以急,其辭淫以哀”,自然去天命愈遠(yuǎn),而孟郊雖然是一介寒士,但他是善鳴者,在他身上體現(xiàn)著偉大的天命。文章沒有斤斤于牢騷怨艾之辭,而是從宏大的天命立論,以縱橫開闊的筆墨概括古今善鳴者的偉大價(jià)值,只在結(jié)尾處以“東野之仕于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將孟郊的失意,在看似不經(jīng)意間,一筆帶過。韓愈要用偉大的天命來激勵(lì)孟郊,令其心胸恢廓而淡然于一時(shí)的得失。錢基博對(duì)此文有一個(gè)極為精妙的點(diǎn)評(píng):
憑空發(fā)論,妙遠(yuǎn)不測(cè),如入漢武帝建章宮、隋煬帝迷樓,千門萬戶,不知所出;而正事正意,止瞥然一見,在空際蕩漾,恍若大海中日影,空中雷聲。
在錢氏看來,寬慰孟郊之愁怨,這是此文的“正事正意”,然而韓愈沒有斤斤于此。他對(duì)“不平則鳴”的磅礴議論,全然著眼于天道之常,其樹立天命的高絕立意,“如入漢武帝建章宮、隋煬帝迷樓,千門萬戶”,廣大開闊。這就形成了“不怨之怨”的獨(dú)特筆致,易楚騷之激越而為抑遏深沉。
/叁/
韓愈古文之深意頓挫,還體現(xiàn)在命意的委婉。其千古傳誦的名篇《送董邵南序》,就是其中最值得玩味者。董邵南科舉坎坷,人生陷入困境,不得不遠(yuǎn)赴河北投靠藩鎮(zhèn)以求得進(jìn)身之路。河北藩鎮(zhèn)對(duì)中央朝廷懷有異心,從忠于唐王室的角度來講,董的做法顯然是有問題的,其選擇的不妥與失當(dāng),顯而易見。韓愈完全可以對(duì)他直接加以勸阻和批評(píng)。然而這篇臨別贈(zèng)序,卻完全沒有簡(jiǎn)單地從譏責(zé)落筆。其行文非但沒有一句批評(píng),反而一步步勸勉鼓勵(lì),但在勸行中,則暗寓規(guī)諫和阻攔。吳楚才、吳調(diào)侯稱此文“僅百十余字,而有無限開闔,無限變化,無限含蓄”。(《古文觀止》卷八)其開闔變化處,就在于明送而暗留。那么,韓愈靠什么來挽留董呢?清人林云銘說:“通篇以‘風(fēng)俗與化移易句為上下過脈,而以‘古今二字呼應(yīng),曲盡吞吐之妙。”(《古文析義》初編卷四)這個(gè)看法注意到韓愈用河北風(fēng)俗的變化,來提醒董邵南不要一意孤行,不要對(duì)河北抱不切實(shí)際的幻想。然而以“古今”勾連意脈還只是形式上的巧妙,韓愈的深刻用心,其實(shí)是在著眼于董邵南之為豪杰的立意。
文章開篇說: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jìn)士,連不得志于有司,懷抱利器,郁郁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
韓愈沒有把董邵南視為一個(gè)僅僅到河北去謀求仕途出路的落魄士子,而是將其視為 “懷抱利器”、身負(fù)才識(shí)的豪杰之士。董希望奔赴的河北,則是“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的豪杰之地。豪杰之士而到豪杰之地,韓愈相信他一定會(huì)遇到知音、改變際遇。然而文章進(jìn)一步從古今變化落筆,疑慮燕、趙作為豪杰之地,是否早已不復(fù)往昔。這種從豪杰之士落筆的立意,正大而委婉,它沒有將董邵南遠(yuǎn)赴河北的行為視為一種功名利祿的尋求,而是看到其中英雄落魄的失意與無奈。韓愈深知,功名利祿之徒,不會(huì)以投靠藩鎮(zhèn)為恥,而只有道義為守的豪杰之士,才會(huì)懂得去就與操守。他寫作此文,就是要喚起董邵南心中的豪杰之氣。他相信作為豪杰的董邵南,一旦他看到今之燕、趙早已不復(fù)往昔,一定會(huì)幡然悔悟。文章最后一段,更直接點(diǎn)出豪杰之士當(dāng)報(bào)效朝廷的命意:
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吊望諸君之墓,而觀于其市,復(fù)有昔時(shí)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文章對(duì)董的河北之行,一步步寫來,皆是勸勉,而勸勉的種種,其實(shí)都是在一步步喚醒其心中的豪杰之氣,盼其能以豪杰自立而省悟自己此行之不妥。如此委婉的規(guī)諫,顯然已不僅僅是辭章布局的巧妙,而是與董邵南在精神上以豪杰相待而期其自省的良苦用心。
韓文澎湃激情中的沉郁,還表現(xiàn)在深沉的自責(zé)與自律。他的《祭十二郎文》就飽含深深的自責(zé)。因游宦在外,韓愈對(duì)老成生病的情況沒能及時(shí)了解,更沒有料到老成如此年輕,竟然這么快就撒手人寰。老成于貞元十九年(803)去世。韓愈從貞元二年到長(zhǎng)安求仕,至此已經(jīng)在仕進(jìn)之路上奔波十幾年,飽經(jīng)坎坷,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發(fā)蒼蒼,而齒牙動(dòng)搖”。在痛失親人的巨大悲痛中,他沒有一味傾瀉懷才不遇、人生失意的憤激,而是為自己沒能照顧好老成而深深自責(zé):
嗚呼!汝病吾不知時(shí),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yǎng)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fù)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yǎng)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mèng)相接。吾實(shí)為之,其又何尤?
這段悲愴的文字,是整篇文章的高潮。千百年來,它撞擊在無數(shù)讀者的心上,是古今祭文中最沉痛的旋律。深長(zhǎng)的凄愴無奈中,回蕩著無法寬釋的自責(zé),令沉痛難以自拔。其實(shí),世路身不由己,無法照顧好家人,別人不會(huì)以此苛責(zé)韓愈,然而韓愈就要以此“苛責(zé)”自己。在這種苛責(zé)里,我們讀出了他對(duì)親人的愛,更讀出了他永不放棄的對(duì)責(zé)任的承當(dāng)。
當(dāng)然,在凄愴的祭悼中,仍然回蕩著作者對(duì)自己坎坷遭遇的無奈與不甘,但如果只有憤激的失意之悲,而沒有作者在深沉自責(zé)中的承當(dāng),就不會(huì)形成此文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作為祭文中的“千年絕調(diào)”,文章所書寫的,是精神的痛苦,更是精神的悲壯,唯有悲壯,才會(huì)撞響藝術(shù)的洪鐘大呂之聲。
委婉的勸諫、深沉的自責(zé),這些獨(dú)特的筆法,在更豐富的意義上呈現(xiàn)了韓文“不怨之怨”的深刻內(nèi)涵,讓韓文于奔涌中有低回、澎湃中有沉郁。這正是蘇洵所謂長(zhǎng)江大河“抑遏蔽掩”的體現(xiàn)。這種獨(dú)特的文風(fēng),體現(xiàn)了韓愈在強(qiáng)烈的淑世之心中,對(duì)道德內(nèi)守的深刻追求。
/肆/
韓愈關(guān)切世事、其心中有憤激、有不平,然而他同樣非常關(guān)注士君子要以道自守,立身高遠(yuǎn),不要斤斤于外在的、一時(shí)的榮辱得失。在《答李翊書》中,他說:
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
他期望士君子要追求精神的自立,不要被他人的好惡所左右。在談到其古文學(xué)習(xí)體會(huì)時(shí),他認(rèn)為一個(gè)有志于學(xué)古文的人,一定立意高絕、以圣人為法,必須擺脫時(shí)俗趣味的干擾,甚至提出,如果時(shí)俗之人稱贊自己,那就深可憂慮,因?yàn)檫@說明自己古文的造詣還很有欠缺:“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yù)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在《與馮宿論文書》中,他說:“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質(zhì)諸鬼神而不疑耳。” 這種對(duì)外在毀譽(yù)全然蔑棄的態(tài)度,造就了韓文傲岸的骨力,也是他能含藏憤激的鋒芒而使文風(fēng)趨于渾涵的原因所在。
強(qiáng)烈的用世之心中,與高絕的內(nèi)圣追求,這兩者在韓愈身上形成微妙的融合。在《答陳生書》中,他勸慰失意的陳生:
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chéng),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nèi),彼圣賢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為眾人;所謂順乎在人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于其初。
然而,韓愈真能徹底做到“平吾心而隨順之”嗎?在《答李翊書》中,他說“仁義之人,其言藹如”,然而韓文似乎并非純?nèi)坏摹疤@如”。事實(shí)上,強(qiáng)烈的憂世之念,使韓愈難以擺脫世事不公所帶來的憤郁不平,但內(nèi)圣所追求的精神超越與超脫,讓他的憤激有了頓挫和內(nèi)斂。清代桐城三祖之一的劉大櫆,稱韓文“雄硬直達(dá)之中,自有起伏抑揚(yáng)之妙”,韓文不怨之怨這種飽含張力的筆法,就是其文風(fēng)張力、精神張力的折射。
蘇洵的“抑遏蔽掩”之說,道出了韓文奔放中的深沉、憤激中的悲壯,精當(dāng)?shù)亟沂玖隧n愈的心曲和韓文命筆的曲折。在韓文流傳的一千多年時(shí)間里,這個(gè)見解獲得無數(shù)響應(yīng),成為韓文最經(jīng)典的評(píng)語之一,是絕非偶然的。今天倘要深入感受韓文的藝術(shù)力量,仍然要不斷體會(huì)其“抑遏蔽掩”的含藏與深沉。
(作者系全國(guó)政協(xié)委員、中國(guó)韓愈研究會(huì)副會(huì)長(zhǎng)、中國(guó)社科院文學(xué)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