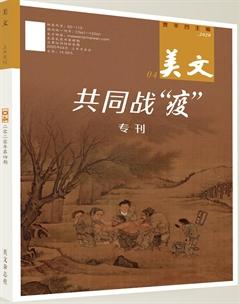我的抗疫關(guān)鍵詞
張華
集結(jié)號
2020年2月2日中午,《美文》雜志CEO穆濤老師打來電話,溫暖的問候、關(guān)懷和祝愿之后,給我下達(dá)了寫作任務(wù),口氣中帶著他一貫的自信和不容分說。他說:“中央政府吹響了打贏阻擊戰(zhàn)的集結(jié)號,咱們雜志也要‘結(jié)集一下,出一期專輯。你負(fù)責(zé)聯(lián)絡(luò)澳門特區(qū)和國外的幾位作者,加上你自己,分別就新冠疫情這一國際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寫篇紀(jì)實性散文,半月內(nèi)交稿,多紀(jì)實,少評論。其他作者我負(fù)責(zé)聯(lián)絡(luò)。” 隨后他就把電話掛了。本來想問問,為何時限是半個月,也沒來及問。
了解這位CEO的人都知道,他說話愛開玩笑,但做事從不開玩笑,而是說一不二,雷厲風(fēng)行。果然,幾天后就發(fā)來了他親自聯(lián)絡(luò)的作者名單,而我負(fù)責(zé)聯(lián)絡(luò)的作者名單空著。我明白,這實際上是在“督戰(zhàn)”。
我迅速起草了一個約稿函,邀請澳門科技大學(xué)人文藝術(shù)學(xué)院院長張志慶教授和拉脫維亞、伊朗、埃及的幾位博士生就自己在這場戰(zhàn)役中的經(jīng)歷進行寫作。發(fā)出之后,一邊等待他們的回復(fù),一邊為我的寫作打腹稿。
我就職的北京語言大學(xué)和兼職的陜西師范大學(xué),也都在打響阻擊戰(zhàn)的第一時間下達(dá)了“不離家,不返校”的重要通知或指揮部令,這是組織上吹響的號令,既是戰(zhàn)斗必須,也是職責(zé)所在,自然要服從安排,聽從指揮。同時,我也把穆濤老師的這次約稿視作寫作人的一次戰(zhàn)斗動員令,視作寫作人的沖鋒集結(jié)號。
據(jù)我所知,在京高校中,中國人民大學(xué)是較早“封校”的,隨后,包括北京語言大學(xué)在內(nèi)的在京高校也陸續(xù)發(fā)出了“封校”通知。2月4日,單位領(lǐng)導(dǎo)發(fā)來短信:“張老師,您有時間的時候能不能給同學(xué)們寫幾句寄語,幾百字就行,咱們集起來,我不定期地給同學(xué)們發(fā)一篇,讓大家安心在家學(xué)習(xí)。可以是學(xué)業(yè)的、健身的、生活的、修身的、人生觀價值觀的,都可以。”出于教師職業(yè)本能,應(yīng)為穩(wěn)定學(xué)生情緒,做好輿情引導(dǎo)盡力所能及之力,我未加思索滿口答應(yīng)。有生以來,要么作學(xué)生,要么教學(xué)生,自認(rèn)為還是了解學(xué)生的,于是寫下短文《有老師在,不用害怕》。單位將其傳到學(xué)校專設(shè)的抗疫網(wǎng)站“聽·師說”欄目,并向“喜馬拉雅網(wǎng)絡(luò)電臺”推送,助力全國學(xué)子筑牢心理防線,上線1天,點擊量即突破12萬,隨后幾天超過30萬。
日記,方方與“官方”
接下任務(wù),寫什么?怎么寫?卻成了難題。寫作邀請函發(fā)出后,張志慶教授回復(fù)說:“估計寫不了,沒有激情。” 我回復(fù)說:“理解,我也是。” 嚴(yán)格說,志慶教授和我都算不上寫作人,更不是作家,即使發(fā)表過一些作品,也以學(xué)術(shù)論文為主,偶爾寫一點散文,也都帶著些論文氣。何況,頭腦已經(jīng)被“文學(xué)理論化”了,有了些寫作的條條框框,所以,在我們看來,論文需要有點激情才能寫出來,文學(xué)作品就更需要激情了。倒是我的那幾位外籍博士研究生不乏激情,一位回復(fù)說:“我放假就回國了,但每天都看新聞。我可以寫抗病的文章,還想給武漢捐款。”另一位,在接到我的邀請之前,其實已經(jīng)接受了國內(nèi)外多家媒體的采訪,還在北京語言大學(xué)的專網(wǎng)上發(fā)表了抗疫演講,代表埃及留學(xué)生聲援武漢。她回復(fù)說:“老師告訴我們說,做文學(xué)研究的,要搞些文學(xué)創(chuàng)作,我要把我這次的經(jīng)歷寫出來。” 還有一位,來自伊朗,說是伊朗使館已號召并發(fā)起伊朗人的捐助活動,她對這場戰(zhàn)爭也算是有獨特經(jīng)歷和感受,所以也可以寫。
收到外籍博士生的回復(fù)后,我又給志慶教授發(fā)信息說:“古人云:唯有文字是砍不掉的。今天的文字,雖然未必能在多大程度上呈現(xiàn)災(zāi)難的傷痛,但畢竟留下些文字總比沒有要強。”然后又問:“澳科寒假短,開學(xué)采取了什么措施?”他回答說:“沒回來的不讓回來;回來的湖北籍或送回或隔離。”我又說:“寫寫澳門眼下景象和措施也可以呀。”他發(fā)了兩張戴著口罩在辦公室上班的照片作為回復(fù)。我又說:“看看網(wǎng)絡(luò)上的文章,不知能否刺激下激情?”隨后,發(fā)去一篇寫北京下雪后街巷面貌的網(wǎng)文《北京格勒保衛(wèi)戰(zhàn)》給他。
作慣了指導(dǎo)別人寫學(xué)位論文的老師,作慣了“為別人做嫁衣裳”的專欄編輯,可能是一位好導(dǎo)師、好編輯,但真正自己執(zhí)筆寫起來,不僅會有“激情之憂”“條框之困”,還會有“素材之缺”。更何況,對我來講,遵守各級政府、單位、社區(qū)、街道“宅”在家里不出門幾乎就是我的一種職業(yè)習(xí)慣、生活習(xí)慣,我平時就是“能不出門則不出門”。只不過,這時“宅”在家里,從電視、廣播和網(wǎng)絡(luò)上獲得的消息,幾乎都是有關(guān)這次抗疫戰(zhàn)爭的。
于是,重溫了賈平凹的《生一次病,就懂人性了》。然而,沒有親歷傳染病,也沒有賈老師的功力,肯定寫不出這樣的話:“當(dāng)我站在鐵柵欄內(nèi)向外張望那些歧視我們的人群時,總是想:別神氣十足以為你們干凈吧,或許,你們是沒有查出乙肝的病人,我們是查出了乙肝的健康人!”
于是,讀到了現(xiàn)任湖北作協(xié)主席李修文的口述《我的心是亂的,現(xiàn)在沒法寫作》。這同樣是“寫作”,一種無法寫作的“寫作”。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其實,志慶教授所言的“沒有激情”豈是真的沒有激情?是心情太亂、太復(fù)雜,無法寫作的一種表達(dá)罷了!
于是,看到了方方的“武漢日記”、俞敏洪的“抗疫日記”、“武漢讀書日記”、“疫區(qū)日記”以及各路媒體的各種音頻的、視頻的、圖文的“日記”。我從小有記日記的習(xí)慣,今年1月11日參加山東大學(xué)舉辦的《曾繁仁生態(tài)美學(xué)文集》出版學(xué)術(shù)研討會,發(fā)言談到與曾繁仁先生的師生交往時,還專門提及這個習(xí)慣。但是,我一直不認(rèn)同將日記作為一種文體用來發(fā)表作品,日記更多還應(yīng)該是屬于“私人”,主要還是寫給自己看的吧。所以,我不能用我的日記響應(yīng)這次集結(jié)號。再說,如果日記只是記,而不評論,再怎么記也記不過“大數(shù)據(jù)”。當(dāng)然,我相信這只是方方的“武漢日記”,她一定還有一份完全屬于她自己的方方“日記”。畢竟,有些心里話想說卻不能寫,而能寫的又不想說,只好說給自己的“日記”聽。
是呀,“學(xué)術(shù)無禁區(qū),課堂有紀(jì)律”,是對教師的要求,新聞出版也有必須堅守的要求和原則。但是,為什么那么多人寧信“方方”,不信“官方”,這難道不應(yīng)該引起某些所謂“官方”的思考嗎?方方,畢竟提供了一些官方看不到的“信息”,何況,真方方只有一個,假“官方”卻有很多。從2月15日開始,所有來京人員,不論是否來自疫區(qū)均需隔離。這是利國利民、利己利他的好政策、好措施,盡管是硬性要求,但一定能得到廣大群眾的理解,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然而,我們社區(qū)得到這樣的消息是從物業(yè)服務(wù)的微信群里看到、有人“提心吊膽”地轉(zhuǎn)發(fā)的消息,群里的人也是“將信將疑”接受的——不少人問:“真的嗎?”真不明白,這時的官方,為什么就不能理直氣壯地發(fā)布這樣的官方消息和官方要求呢?
隨后,從“今日頭條”看到轉(zhuǎn)發(fā)人民網(wǎng)北京頻道的這樣一則消息:
今天下午,北京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舉行第二十二場新聞發(fā)布會。北京市疾病預(yù)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龐星火介紹,一返京人員正常上班未隔離觀察,已經(jīng)導(dǎo)致其所在單位幾十人隔離。龐星火介紹,近期某個確診病例年前自駕回老家過年,參加了親戚朋友多次聚會聚餐。雖然個別親戚當(dāng)時有感冒癥狀,他們都沒在意。大年初六一家人開車回到北京,初七這個病例正常上班。過完元宵節(jié),他聽說老家聚會的有確診了。他想起近期有感冒的癥狀,果然后來確診……“因為這個病例回京后沒有隔離觀察14天,他導(dǎo)致了他單位幾十個人被隔離。”龐星火說,更為值得關(guān)注的是,這名患者在食堂吃飯時,在處理餐盤時,和他一起聊天的密切接觸者沒有戴口罩。這個聊天對象當(dāng)時被確定為密切接觸者,昨天也被檢測為陽性。龐星火提示,這位病例是外地返京人員,我們提示,一定要在家居家隔離14天,并與家人保持距離……
其實,在官方正式發(fā)布此消息前,民間即已有了這樣的消息“流出”:北京防疫將升級——西城區(qū)一個機關(guān)工作人員,不是湖北回來的,沒有隔離觀察,就直接上班了,結(jié)果發(fā)燒確診了。導(dǎo)致與其接觸過的60多人被帶走隔離。市委領(lǐng)導(dǎo)前兩天剛到西城指導(dǎo)防疫工作,得知此事震怒,所以才發(fā)布的所有回京人員必須隔離這樣的命令。
看,坊間“流傳”的消息沒有任何不好與不恭吧,而且會為官方加分添彩,可惜人家官媒就是不這么說,而是習(xí)慣于用那種“遮遮掩掩”“吞吞吐吐”“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新聞腔。
果然,過了幾日后,另外半張“臉”才徹底讓公眾看見——“今日頭條”梳理了一下北京確診病例的“故事”,沒有被刪帖,所以大家就認(rèn)為被官方認(rèn)可了。為什么官方報道不能像民間消息那樣講實情呢?有人調(diào)侃說,官方是把言論自由留給了民眾,把不自由留給自己,同時又給“刪帖者”以“就業(yè)崗位”。豈不知刪帖不僅無濟于事,而且常常事與愿違,常常壞事。畢竟,在信息時代真相靠捂是捂不住的,也是不合常理的。這次疫情告訴我們,廣大人民群眾的知情權(quán)不應(yīng)被剝奪,尊重公眾的知情權(quán),讓真相盡早公之于眾,是最好的辦法,是最優(yōu)的對策,是最近的路。習(xí)近平主席要求把人民群眾的疾苦放在心間,人民的利益至上,疫情當(dāng)前又具體指示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這次“大考”,某些代表官方的官員到底做得怎樣,一定會有一個評判。習(xí)主席曾強調(diào)“增強憂患意識、防范風(fēng)險挑戰(zhàn)要一以貫之”,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xiàn)代化的要求,官方必須有拷問自我的勇氣和擔(dān)當(dāng)。
好了,“不說了!”再說就不是“多紀(jì)實,少評論”了。我明白,這是《美文》雜志一直倡導(dǎo)的“大散文”風(fēng)格。寫到這里,我也開始明白了為什么穆濤老師把稿約時限定為半個月了—— 在他看來,半個月的時間,抗疫斗爭一定能夠發(fā)生積極變化,或者被有效遏制。
疾病,哈佛,美帝
《淮南子·說山訓(xùn)》一書中說:“良醫(y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圣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
“中國病了!”平時,這么說會引發(fā)歧義甚至?xí)耙馃怼钡摹5牵谶@樣大的疫情面前,無論是平民還是官員,無論是國內(nèi)還是國外,大家都知道也都說過“中國病了”!這場疫情是國之病,國之殤。
此時,《美文》“漢風(fēng)專刊”下一期也到了交稿的最后期限,我在主持人語《文學(xué)與疾病》中寫道:“本來這期并無計劃寫這樣一個選題,但是,‘新冠疫情突然來臨的特殊時期,無論如何也難以把‘抗疫從思緒和生活中揮去,因為來自四面八方的疫情信息,飛揚著,充斥著,寫作,必然會把其‘呼吸進去.......”
其實,每個人都會生病,每個國家也一樣,用文學(xué)的語言也可以說“人類病了”“地球病了”。文學(xué)也會“生病”,這很正常,重要的是如何對待“疾病”。正確對待,有的病可以預(yù)防,有的病可以減輕,有的病可以治愈,如果諱疾忌醫(yī)或掩耳盜鈴,不僅會致病,還會使病情加重甚至致命。于是,在“文學(xué)與疾病”中,我又寫道:“當(dāng)然,也可以對‘文學(xué)與疾病作另外一種理解,即‘文學(xué)病了……或者,‘文學(xué)沒病……這個層面的‘文學(xué)與疾病研究和探討相當(dāng)復(fù)雜,而且始終處于爭論之中…… 然而,即便如此,在人類面對突如其來的重大疾病、重大危機時,文學(xué)本身最基本的良知和靈魂也應(yīng)該并且必將被喚醒,以其與生俱來的免疫力與疾病和危機進行斗爭,進行抗?fàn)帯J聦嵣希S多作家在這次疫情中就是這么做的,他們是為文學(xué)帶來免疫力的良性細(xì)胞,也是文學(xué)生命的守護神。”
拖延癥也是一種病,這次武漢就患了“拖延癥”,山東任城監(jiān)獄也患了“拖延癥”。邀約的文稿都紛紛發(fā)回來了,我也不想再拖延,于是決定再去趟學(xué)校,感受一下防控疫情下的北京。
之所以說“再”去一趟,是因為在春節(jié)前疫情爆發(fā)初期去過兩次,那時大家的警惕性還沒那么高,出入小區(qū)跟平時差不多,只需門禁卡不用通行證,也不用測溫,出入校門口也只需出示車輛通行證。當(dāng)時還順道到附近的超市買了些速凍食品和青菜,大家雖然都戴著口罩,但超市里依然非常擁擠,排隊等候當(dāng)然也沒有現(xiàn)在執(zhí)行的“一米線”距離要求。后來,隨著北京疫情防控要求的升級,學(xué)校發(fā)布通知:除疫情防控需要的工作人員、值班人員外,其他教職工原則上不得進入校園。如有特殊原因需進入校園,須提前一天報本單位負(fù)責(zé)人批準(zhǔn),由單位報人事處批準(zhǔn)。人事處提前一天向保衛(wèi)處報送第二天因特殊原因進校人員名單(特殊原因應(yīng)為“必須、緊急、非本人無法辦理”的工作事項)。
提前辦了入校手續(xù),從居住社區(qū)出發(fā)時才知道供出入的門只留一個了,門口多人值守,入小區(qū)必須登記核實身份、測體溫。入校程序很順利、也很智能,門禁自動打開,出入均不與人接觸,電梯告示:“2月16日已消毒”。
駕車到學(xué)校的路上,喜迎春節(jié)、張燈結(jié)彩的城市裝飾還在,車輛非常少,幾乎看不到行人,公交車照常運行但里面并沒有多少乘客,平常從家里到學(xué)校需要60分鐘的車程,差不多20分鐘就到了。我在想,如果沒有疫情,中國GDP和各方面實力仍保持疫情前的強勁上升勢頭,卻能實現(xiàn)出行沒有限號,沒有擁堵,沒有喧囂,沒有霧霾,人民安居樂業(yè)、富強幸福……眼前的景象,算不算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一項追求?這與大部分美國城市相比也沒有多大區(qū)別了,與哈佛大學(xué)所在的安靜的波士頓也很接近。
哈佛大學(xué),全球公認(rèn)的世界一流大學(xué)。“新冠”病毒出現(xiàn)后一周內(nèi),校方為校友定期發(fā)送的“哈佛報”(The Harvard Gazette)就有三篇是關(guān)涉“新冠”病毒的。在中國各方面最頂級專家都在為日常的如何洗手、如何戴口罩、如何消毒,通過各種宣傳途徑支招和發(fā)布貼示的時候,哈佛的專家也從未曾“脫離生活”。這一方面說明世界越來越是一個“地球村”,說明“蝴蝶效應(yīng)”的有效性和適用性,同時也再次說明,無論人文社會科學(xué)還是自然科學(xué)都應(yīng)是“現(xiàn)實主義的”,都必須是關(guān)注人生、關(guān)注民生的。因為哈佛的知名度,那些動不動就拿哈佛說事的“蹭熱度”文章,我很少看,還專門寫文章批評過這種做法。但是,我很信任哈佛的“官方”推送,因為哈佛大學(xué)雖坐落在美國,但它更是一所國際大學(xué),它的教師和學(xué)生來自世界各地,哈佛人會非常愛惜其“羽毛”,保持其世界一流和高知名度的信譽。
我這次到校要處理多項事務(wù),其中一類就是為同學(xué)寫英文推薦書,提交期限都在這幾天。其中包括一位泰國博士申請聯(lián)合國難民署秘書職位,一位拉脫維亞同學(xué)申請到美國耶魯大學(xué)做博士后,一位碩士同學(xué)申請赴美讀比較文學(xué)博士,和某科研機構(gòu)的一位研究人員赴美國哈佛大學(xué)訪學(xué)。盡管全力支持同學(xué)到世界一流大學(xué)學(xué)習(xí)是我一貫的做法,但由于美國政府在這次疫情中的表現(xiàn)令人大跌眼鏡,令輿論嘩然,所以在目前這樣一個背景下我還是稍有猶豫,猶豫把他們推薦到美國是不是推向了“火坑”,推給了“美帝”。但隨后這種猶豫很快消失,因為我應(yīng)該相信他們的判斷,尊重他們的選擇,而且只有到了美國,對“美帝”的真面目才有全面而直接的認(rèn)識。
從學(xué)校回到家里,趕緊“爬樓”看社區(qū)物業(yè)服務(wù)微信群,發(fā)現(xiàn)了這樣一段對話:“中國做的相當(dāng)好,我原計劃2月3日去旅游,當(dāng)時感覺是‘有那么嚴(yán)重嗎? 多虧政府統(tǒng)一可以退票、退房,否則我們就去了。目前在處理各地流行病學(xué)調(diào)查的數(shù)據(jù),很多過節(jié)旅游時得病的。”“我姐前幾天發(fā)信息給我說,出國吧,對孩子好。我現(xiàn)在倒不想出國了,覺得中國還是有人情味。”“相信祖國會越來越好,國運最好。我也覺得武漢這次要是外國,自生自滅吧, 看誰命硬。”“看美國去日本接人的時候,用一架破飛機,據(jù)說是貨機改裝的。來中國撤僑的也是破飛機。有一部分上飛機前確診的商量半天給帶回去了,但是與沒確診的乘同架飛機,非常擁擠也沒真正隔離。”
這才是“美帝”。
我的抗疫關(guān)鍵詞,似乎還有很多。比如,因職責(zé)所在而每天都必須密切關(guān)注的“國際學(xué)生”數(shù)據(jù)和動向,我指導(dǎo)的國際碩士博士的情況,以及有關(guān)此次疫情的“國際聲音”“國際支援”;又比如,我所在社區(qū)及周邊社區(qū)經(jīng)歷疫情的故事。在社區(qū)微信群里,從安靜到喧囂再到理性的過程,這中間除了居民們各顯神通、發(fā)布和傳播著各路消息之外,還有一些生活中的“雞毛蒜皮”,有抱怨樓上跑步的,有調(diào)侃呆久了鄰居吵架的,有建議應(yīng)該怎樣更好管理小區(qū)的,有舉報在小區(qū)溜達(dá)不戴口罩的,可以說是生活萬象的一種集中呈現(xiàn);再比如,原本計劃是要回家鄉(xiāng)菏澤陪90高齡父母過春節(jié)的,疫情發(fā)生后父母的態(tài)度和看法,臨近市濟寧一夜間增加200多確診病例前后當(dāng)?shù)卮胧┑淖兓鹊取?/p>
我相信,這些關(guān)鍵詞盡管沒有寫在紙上,但卻深深地刻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