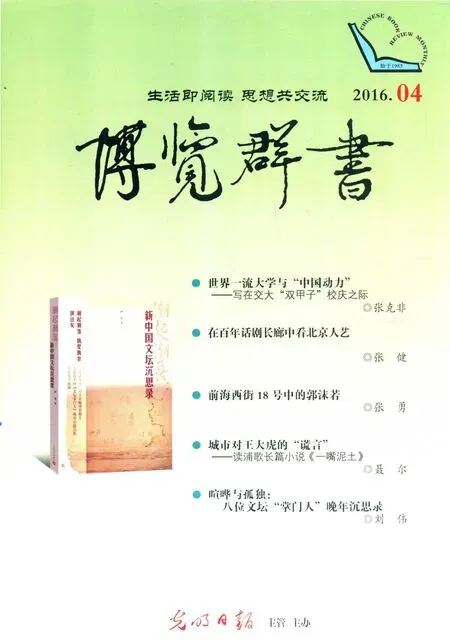韓愈的“基因”與遺傳
張清華
韓愈(768年-824年),唐代杰出的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韓愈官至吏部侍郎,人稱“韓吏部”;其逝后被追贈禮部尚書,謚號“文”,故稱“韓文公”。
蘇軾最是推崇韓愈,說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韓愈一生,最要讓人一提的是,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軍司馬,參與討平“淮西之亂”。還有就是,元和十四年(819年)因諫迎佛骨被貶至潮州,于是便有了治潮之功, 2019年是韓愈治潮1200周年。
韓愈在文學上貢獻卓特,有“文章巨公”“百代文宗”之名。其散文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詩極富創造精神,“為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葉燮《原詩》)。其古詩驅駕氣勢,掀雷抉電,風格豪猛,聲宏調激;而他的七絕則寫得清新爽勁,富于神韻,近似盛唐。
這組文章的四位作者,老中青三代,既有學壇耆舊,又有科研精銳,還有學術新秀,寫法側重各異,分別從吏治家教、社會民俗、文論美學與接受等方面開展,多方位觀照,也有就韓愈七絕的專門研究,全面梳理,深入剖析,讓人看到詩人另辟蹊徑的新變。
—王志清(文學教授、唐詩學者、王維專家)

韓愈有關家教的詩文,比較突出者有《符讀書城南》《示爽》詩和《祭鄭夫人文》,這些作品至今仍然是喻世的恒言。
/詩書傳家:古今同慨/
韓愈一生育有六個孩子,他的這些有關家教的詩文,是對愛子的誡勉,也是詩人自己人生經驗的總結。
《符讀書城南》是為送兒子小符韓昶去長安城南莊讀書而寫的,其詩云:“恩義有相奪,作詩勸躊躇。”顯系教子小符。“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豬。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蟾蜍。一為馬前卒,鞭背生蟲蛆。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歟!”“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雖然初生一樣,讀不讀詩書,“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結果是不一樣的。故教符勤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余”。
《示爽》是送侄孫韓湘去宣城赴任的,云:“臨分不汝誑,有路即歸田。”乃教導侄孫韓湘。“名科掩眾俊,州考居吏前。”“時輩千百人,孰不謂汝妍。”贊湘成材,要韓湘做個廉潔為民的好官,乃肯定其成龍的意思。“昔日同戲兒,看汝立路邊。人生但如此,其實亦可憐。”非一龍一豬之意否?此說曾受到后人的詬病。《符讀書城南》文讜《新刊經進詳注昌黎先生文集》中王儔《補注》說:“黃魯直嘗為眉山石守道書此詩,跋其后曰:‘或謂韓公當開后生以性命之學,不當誘之以富貴榮顯。”何焯《義門讀書記》卷三十則曰:“詩書乃文章根本,人之所以不陷于不義者,莫不由之也。”此乃封建社會教人成材的根本。今文《尚書·召誥》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孔氏傳云:“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為政之道亦猶是也。”孔穎達疏引正義云:“嗚呼!王行教化當如初生之子,子之善惡無不在其初生。若習行善道,此乃自遺智命,智命謂身有賢。智命由己來,是自遺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矣。”此乃韓公教子說所本:詩書傳家。后世學者以此批評韓愈誘子以富貴,卻不知韓愈所據的封建儒學教化的思想就是這樣。
《符讀書城南》詩的龍豬之比,教子符富貴利達,乃千百年封建社會家教的傳統思想,真不高明,所以,宋陸唐老責之曰:
退之不絕吟六藝之文,不停披百家之編,招諸生立館舍,勉勵其行業之未至,而深戒其責望于有司,此豈有利心于吾道者。《佛骨》一疏,議論奮激,曾不以去就禍福回其操。《原道》一書,累千百言,攘斥異端。用力殆與孟軻氏等,退之所學所行亦無愧矣。惟《符讀書城南》一詩,乃微見其有戾于向之所得者,駭目潭潭之居,掩鼻蟲蛆之背,切切然餌其幼子以富貴利達之美。此豈故韓愈哉?(魏仲舉《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卷六引)
這說出了韓愈一生傳儒道而為國為民,不怕窮,不惜死的品格;施教育才的思想;批評了韓愈誘子富貴利達的做法,都很懇切。最后“此豈故韓愈哉”一問,似不知韓愈。實則,陸唐老何嘗不知道韓愈身上,正包含傳統歷史文化精華與糟粕兩個方面。精華是主流,否則,中華民族也不會立于世界優秀民族之林,輝光永照;韓愈之偉大正體現了這活生生的文化史;為賢者諱而拔高,為偏見而詬病,都不對。有學者詬病韓愈時曾贊譽杜甫“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覓彩衣輕”。“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床。試吟《青玉案》,莫羨紫羅囊。”“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又示宗武》)及《熟食日示宗文宗武》囑宗文、宗武紹承家學。家學者正如二子起名文、武,欲繼承遠祖當陽侯杜預、近祖“文章四友”杜審言,以詩書傳家。杜甫是真正的詩人,卻非政治長材。他游宦長安十年才得小官,一直不能施展抱負,怎能和平淮西、批逆鱗、闖鎮州的韓愈相比?其實,大家都不必因小失大。一些人因沉于舊說,正是見小忘大,自縛于繭中矣。
/傳道育才,何惜斷炊/
韓愈教子符和孫爽,都是重教與學,著眼于成材上。《符讀書城南》:“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兩出“勤”字的關鍵在勤,只有勤才能飽有詩書,飽有詩書才能成為府中的“卿與相”,即成材。《示爽》說:“念汝將一身,西來曾幾年。名科掩眾俊,州考居吏前。”即韓湘從宣城西來長安,韓愈教湘讀書,才有“名科掩眾俊”的學識,也才能有“州考居吏前”的才干,成為廉吏賢才。侄孫韓滂雖短命夭歿,卻體現了韓愈家教成材的苦心。《祭滂文》云:“汝聰明和順,出于輩流。強記好文,又少與比。將謂成長,以興吾家。如何不祥,未冠而夭?”韓滂聰明聽話,乃韓愈夫婦精心培養,欲使其成為韓氏繼嗣的人才,卻不幸十九歲而卒。由此可知韓愈乃以詩書傳家,子孫成材為旨歸。
統觀韓愈一生,都是以仁愛為根本,以教育為手段,發現教育使人成材的。他做地方官在陽山、潮州、袁州,總是以教育先行,在潮州甚至拿出自己治潮八個月的全部薪俸作辦學的經費。他四為學官,一為祭酒,是以選材育才出了名的。韓愈一為博士時,即上《與祠部陸員外書》薦材于賢主考。育賢、舉賢、用賢,招攬人才是為國樹根之本,亦是韓公此書的本意。司貢士者之職在得人,佐司者在進賢,權德輿有得人之心,陸傪有進賢之志,二人又相知誠深,相得益彰,故韓公才以四門博士之微職,薦十士于陸傪。此舉在唐無二,史亦罕見。如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八云:
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傪員外通榜帖,韓文公薦十人于傪,其上四人曰侯喜、侯云長、劉述古、韋紓,其次六人:張苰、尉遲汾、李紳、張俊余,而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而苰、紳、俊余不出五年內,皆捷矣。
漏韋珩,實即群玉,貞元二十一年及第。亦如唐李肇《唐國史補》卷下曰:“韓愈引致后進,為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時人謂之韓門弟子。”韓公所薦十人,未出五年,均及第。所以《舊唐書·韓愈傳》說,韓愈“頗能誘厲后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弘獎仁義為事”。韓愈育徒、撫孤、待人,“未嘗宿貸有余財,每曰吾明日解衣質食,今存有已多矣夫”(皇甫湜《韓文公神道碑》)。因缺糧乏食,夫人面有饑色,韓公仍和樂以對。張籍與韓愈為終身師友,長于詩疏于文,而道不及。自貞元十三年秋冬到開封投學韓愈,管吃管住管教,年余“公領試士司,首薦到上京,一來遂登科,不見苦貢場”(張籍《祭退之》)。張籍一舉登第;韓愈子符又受教于籍,詩文大進,于長慶四年登第。韓愈教書育人的思想集中體現在《進學解》里。他招諸生于書館,誨之曰:
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欂櫨侏儒,椳 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余為妍,卓犖為杰,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
工匠、醫師、宰相都應成為伯樂,各行各業不同材質都成為有用之材,得到方方面面的應用,社會焉能不富裕,不和諧,不治理?這就比伯樂之于千里馬,詩書之于卿相要全面,故歷來受到人們的重視。偉哉,韓愈,真大賢圣的識見也。
/為家為國,自振一代/
杜甫之偉大,以詩光耀青史,史不或缺;韓愈以政治家、思想家、詩文家光耀青史,同樣不能或缺。杜甫憂國憂民,以詩展現盛唐至中唐歷史畫卷,以詩史稱詩圣,造就詩莫盛于唐的歷史。韓愈以思想家的識見,辟佛老衛儒道,統一君臣思想;以政治家的氣概參與平定淮西,震懾河北藩鎮;以固國安民的膽氣冒死出使鎮州,說服將帥,促成了中唐振興。杜韓之賢圣而偉大誰不稱頌,誰不自豪。韓愈為家為國,自振一代的事跡,真可歌可泣。《新唐書·韓愈傳》贊曰“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堤末流,反刓以樸,刬偽以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陳言,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捂圣人者”,以至于欲自振一代。韓愈欲自振一代,當涵蓋立其家、振其國兩個方面。
先說立其家。韓愈重孝道,《祭鄭夫人文》曰:“受命于元兄曰:‘爾幼養于嫂,喪服必以期。今其敢忘,天實臨之。”
老嫂比幼弟年長近30歲,嫂卒,韓愈尊兄囑,齊之以禮,為嫂服孝終期。或謂讀《祭嫂鄭夫人文》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祭十二郎文》:
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后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只。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以孝悲慨,泣血感人,如歷來學者所說,讀《祭十二郎文》不墮淚者其人必不義。韓愈“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為義”(《原道》),以仁為根,以孝義為行,可謂集仁、孝、義為一身的典型。換個角度看韓愈的家教,如他在《送楊少尹序》結語:
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游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韓公不戀官,不終客居官所,送兄、歸女于河陽先人墓,又自選“臥牛之地”,終葬河陽。一生多次歸家相親廬墓,幾次長住河陽故居,說明他鐘愛自己的家鄉,故借《送楊少尹序》,贊楊少尹致仕歸里,念念不忘家鄉的舊情,教育子弟雖官而愛家。故張伯行謂此《序》:
末段遂言其歸故鄉之樂,賢于世之貪爵慕祿者遠矣。唐人詩云:“相逢盡說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士大夫出處之際,可念也夫!(《重訂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
再說“自振一代”。如果說杜甫以先祖杜預、審言為楷模,韓愈則以父仲卿、兄韓會為榜樣。李白《武昌宰韓君去思頌碑》云:
仲尼,大圣也,宰中都而四方取則;子賤,大賢也,宰單父人到于今而思之。乃知德之休明,不在位之高下,其或繼之者,得非韓君乎!
君名仲卿。把仲卿宰武昌的賢德政績比大圣仲尼、大賢子賤。韓愈為官施政,自侔圣人,當受嗣于乃父。兄會,唐代宗李豫永泰(765)中,與“崔造、盧東美、張正則居上元及江淮間,好言當世事,自謂有王佐材。以道德文學伏一世,大夫士謂之‘四夔,以其道與皋夔侔。或云夔嘗為相,四人者,身在隱約,天下許以為相,故云”(《全唐文紀事》卷三九《韓會傳》)。韓愈“少小尚奇偉,平生足悲咤。猶嫌子夏儒,肯學樊遲稼。事業窺皋稷,文章滅曹謝。濯纓起江湖,綴珮雜蘭麝。悠悠指長道,去去策高駕。誰為傾國媒,自許連城價”(《縣齋有懷》)。其志尚高、胸襟闊、氣勢雄,而為家為國、自振一代的思想,當受乃兄韓會的影響。
韓愈為家為國、自振一代的思想和行為,正可見韓氏一族的遺傳基因,也是他對傳統儒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的繼承。
(作者系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員,中國韓愈研究會名譽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