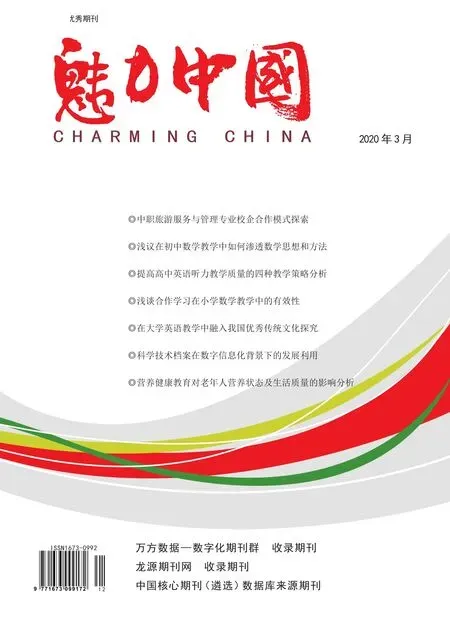“他者“視域下的《囧媽》
(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四川 成都 611756)
一、與“他者”對抗下的“自我”覺醒
“他者“與“自我”往往在相伴出現(xiàn),而大都不是獨立存在,在拉康看來,學會語言,標志著一個人從“自我”與“他者”合一的想象界進入以“缺失”為特征的象征界。隨著劇情的推進,徐伊萬的“自我”在被周圍的“他者”所凝視的過程中,從想象界到象征界,不斷地實現(xiàn)著“自我”的突破。
劇情伊始,徐伊萬和張璐陷入了離婚的糾紛,二人在爭吵時,張璐說出“你的心里面長了一個幻想的老婆。”,“張璐這一角色從影片開始部分便展現(xiàn)出了覺醒:自己并不是徐伊萬心中那個“幻想的老婆”。從張璐的角度出發(fā),張璐的“自我”與徐伊萬幻想下的“妻子”形象衍生出的一個“他者”產(chǎn)生對抗,促使張璐的“自我”在與其對抗中發(fā)現(xiàn)自己與其所幻想出來的“妻子”形象出現(xiàn)缺失,從而使得張璐的“自我”得到覺醒。
而隨著張璐與徐伊萬矛盾逐漸激化,徐伊萬在跟母親出行的火車上也遇到種種麻煩,這使得徐伊萬的“自我”逐步走向不滿的狀態(tài),在與異域美女娜塔莎(歐麗婭飾演)在火車尾扔戒指放縱內(nèi)心之后,徐伊萬終于爆發(fā)了對母親的埋怨。他對母親說到:“在她面前我要維護你,在你面前我要維護她。”
這一矛盾的激化,來源于徐伊萬的“自我”意識從“自我”與“他者”合一的想象界逐步進入到有“缺失”的象征界。徐伊萬開始發(fā)現(xiàn)自己設(shè)定下了兩個不同的“妻子”和“兒媳婦”的符號,但這兩個符號與張璐存在著缺失。這讓徐伊萬的“自我”開始意識到缺失,實現(xiàn)從想象界到象征界的跨越,在與“他者”的對抗下,徐伊萬的“自我”也開始覺醒。
二、“他者”凝視下“自我”的找尋
福科認為,“自我”與“他者”之間存在著“看”與“被看”的關(guān)系,也是一種權(quán)力關(guān)系。在“他者”的注視下,“自我”的主體性失落,由主體變?yōu)榭腕w,變?yōu)槲颷1]。徐伊萬在與異域美女娜塔莎的交流中,過于激進的交流使他意識到感情中不被需要的一方猶如“敝履”。當他認為自己和娜塔莎處境一致時,卻在娜塔莎下車后透過車窗看到了她與前男友的重歸于好。在這個看的過程中,徐伊萬的“自我”主體性失落,產(chǎn)生出孤獨感,同時在看的過程中產(chǎn)生出“自我”與“他者”的對比。
此時的徐伊萬內(nèi)心的失落感達到高峰,在母親這個“他者”的凝視下,徐伊萬的“自我”不斷重新審視,他在不斷嘗試找尋“自我”彌補從想象界到象征界的“缺失”,也由此真正打開了從想象界走向象征界的大門。由于凝視者往往代表了某種社會習俗、社會規(guī)范或意識形態(tài),“看”與“被看”天然地具有不平等的地位。在這種異于自身的意識形態(tài)的脅迫下,個體不得不放棄自己的主體性和獨立性,被“看”所異化。最后在與母親爭吵中爆發(fā),又在母親的不辭而別中開始找尋,找尋母親的過程中,徐伊萬也在完成著“自我”的找尋。在背著母親過冰河的過程中,徐伊萬發(fā)現(xiàn)想要真的尋到“自我”不能放棄。當母親說“來不及了。”他回答母親“來得及。”當母親說“我可能注定沒辦法參加。”他說“要參加,不能放棄。”在這個時期讓我們真切的發(fā)現(xiàn)了徐伊萬對“自我”找尋的渴望。
三、結(jié)語
《囧媽》的結(jié)尾,徐伊萬完成了和自己生命中兩個女人的和解,而這一份和解還完成了徐伊萬“自我”的找尋與覺醒。從劇情發(fā)展順序來看,徐伊萬是在凝視“他者”的同時,被“他者”凝視著。徐伊萬“自我”的覺醒不僅僅來源于“自我”的找尋,而更多的在與被“他者”凝視與凝視“他者”的過程中,一次又一次從“缺失”中找尋出通往真實“自我”的大門,從實在界、想象界又到象征界,又在象征界與想象界來回掙扎與糾結(jié)最終使得徐伊萬“自我”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