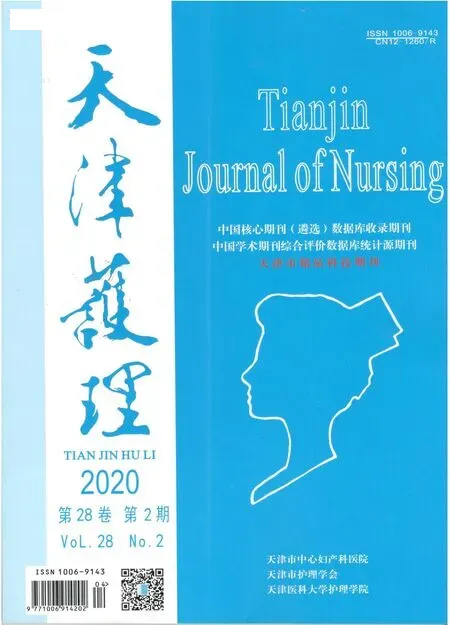康復臨床路徑結合團體心理療法對缺血性腦卒中患者病恥感及日常生活、運動能力的影響*
趙麗麗 唐明霞
(天津市第四中心醫院,天津 300140)
作為嚴重危害人類健康的腦血管疾病,缺血性腦卒中不僅是導致患者死亡的第三大病因,也是長期致殘的首位病因。 據統計,有超過70%的存活患者存在不同程度肢體和認知功能障礙,不僅嚴重影響其日常生活能力,還會因為肢體功能障礙或殘疾使患者出現強烈的病恥感,自尊心受損,甚至會引發情感、心理和人格障礙[1]。 因此,減輕患者殘疾,降低其病恥感,促進其功能的恢復和生活質量的提高至關重要。 針對腦卒中患者的康復治療, 有學者提出了一套有序且規范的分層級、分階段腦卒中康復方案和臨床路徑,其是以循證醫學證據和臨床應用經驗為依據的腦卒中早期康復臨床路徑和相應的治療方案[2]。 團體心理治療則是一種廣泛應用于臨床的心理干預技術,其被證實有利于患者的心理康復[3]。本研究則將康復臨床路徑與團體心理療法聯合應用于腦卒中后的康復,觀察其對患者病恥感及日常生活、運動能力的影響,現將結果報告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2018 年1 月至2019 年3 月在我院接受治療的98 例缺血性腦卒中患者作為研究對象,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將患者分為常規組和研究組各49 例。 研究對象納入標準:①符合《中國腦血管病防治指南》中缺血性腦卒中的診斷標準[4];②首次發病,病程在7 d 之內,或既往有發作史,但無神經功能障礙遺留;③存在不同程度的口舌歪斜、麻木、偏癱、癡呆、 言語不利等后遺癥狀; ④中重度運動功能障礙,Fugl-Meyer 運動功能評分(FMA)≤85 分;⑤初中以上學歷,可獨立完成問卷回答。 排除標準:①患有焦慮、抑郁等精神疾病或重大軀體疾病者;②有≥2 次的腦梗死或腦血栓形成病史;③3 個月內有心臟或呼吸停止、心肌梗死、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重癥肺炎、深靜脈血栓等病史者;④存在或患有其他影響運動功能的病史或疾病者;⑤不愿意參與本研究或無法堅持完成研究者。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表1)。本研究獲得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通過。
1.2 方法
1.2.1 研究組
1.2.1.1 入組第1 d 患者進入臨床路徑,臨床路徑主要包括臨床路徑表單、臨床路徑醫療和護理工作指南、康復技術操作指南。 參與臨床路徑的人員包括醫師、康復師、護士。 康復治療主要包括作業治療、運動療法訓練、言語和吞咽治療、中醫康復治療和物理因子治療等。 具體方案見缺血性腦卒中患者臨床路徑表(表2)。

表1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1.2.1.2 團體心理治療。 將49 例患者隨機分為5 組,每組9~10 例,共治療8 次,每次60 min。具體的治療內容參照認知行為治療理論和既往研究結果設計,目的在于改變患者不良認知、促進其情緒表達、提供支持性環境、提升問題解決技巧和能力等。 所有心理治療師均接受正規培訓。 第一單元(第1~2 次):患者之間介紹自己的姓名、疾病、愛好、參加心理治療的目的和期望等, 承諾在治療以外場所不討論治療內容, 建立基本信任關系。 同時引導學員之間通過游戲、交流等相互認知和了解,形成團隊,建立團隊的參與度和凝聚力,簽訂團隊契約。 引導者同時就急性缺血性腦卒中相關知識進行講解, 引導成員關心和重視疾病進展、治療、預后等問題,并進行討論,制定團體目標。 第二單元(第3~6 次治療):治療師引導學員相互交流,敞開心扉,訴說和互相傾聽患病后的困惑和內心感受, 引導其察覺自身的負面情緒并分析情緒產生的原因,幫助學員彼此之間以關懷、幫助的態度對待,互相提供解決方法。 活動內容包括:通過角色扮演、 情景演繹等方式了解和分析自己在特定情境下的思維模式和情緒表達, 團隊一起探討情緒調控方法;指導患者認知和辨明應激,認識和了解應激對情緒反應的影響和作用,了解應激反應,訓練患者處理應激技術, 指導其通過解決問題來進行應激源的矯正或消除, 從而提升對應激的認識和態度及降低應激強度;指導患者進行情緒管理;幫助患者尋找深層的導致自身不良情緒的信念, 將不合理信念以合理的信念來取代;幫助患者尋找人際支持,幫助其了解自身人際狀況, 用合理的信念替代其在人際交往中的不合理信念和想法; 鼓勵患者之間相互幫助和支持,促使其積極尋找社會支持;培養患者健康性心理狀態,指導患者聽說技巧,鼓勵其勇敢表達自己的想法,可布置相應作業(要求家人一起參與和討論);分享對治療和生活的感悟,講述自己與家人及同事之間相處的模式, 分享負面情緒對自己的影響以及應對和解決方法, 鼓勵其通過語言表達對團隊成員和家人的謝意。 治療師在這一過程中可將態度積極樂觀且恢復效果好的成員作為榜樣, 使其他學員觀察到榜樣成員情緒、行為、運動功能等方面的變化和進展,起到激勵的作用。 對于有積極變化的成員要加強鼓勵,立即給予強化,對負面變化要及時識別并進行處理。 團隊成員進行自我分析,對自己的思維模式、性格特點、應對方式、行為模式等進行分析,使其發現自身存在的不足和缺點, 深化自我認識和自身存在價值,樹立信心。 終止階段(第7~8 次治療):治療師鼓勵成員宣泄抑郁情緒, 更深層次表達自己患病后的內心感受, 鼓勵其談論自己生活中發生的變化和看法,指導其正確調節情緒,制定新的生活規劃。 治療結束前,組織學員談論對團體治療的內心感受, 告別團體, 要求在今后的生活中患者要加強聯系,相互支持[5]。

表2 缺血性腦卒中患者康復臨床路徑表
1.2.2 常規組 保證患者入組時的基礎條件與研究組一致,給予患者常規康復治療方案,入院時由當班護士對患者進行入院宣教, 根據護理規范在住院期間進行疾病知識宣教、康復訓練、治療護理和出院指導等,內容不進行限制,但時間與研究組相同,所有的治療內容和時間需如實記錄在康復治療記錄單中,每周記錄1 次, 同時給予患者心理指導和常規健康教育。
1.3 觀察指標
1.3.1 病恥感評估[6]分別于治療前和治療結束后應用病恥感感受問卷(ISMI)對患者病恥感嚴重程度進行評估, 該量表主要是評估患者對病恥感的主觀內心感受,包括刻板因子、疏遠因子、抵抗因子、歧視因子、社會退縮因子5 個維度,共計29 個條目,采用Linkert4 級評分法,記錄總分,評分越高表示病恥感感受越強烈。 本問卷總的 Cronbach’s α 系數為 0.90,具有良好的信度。
1.3.2 日常生活能力評估[7]分別于治療前和治療結束后應用改良Barthel 指數(MBI)對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動能力進行評估。 該量表評分標準為:大便(可自控10 分、有時失禁 5 分、失禁 0 分);小便(能自控 10分、有時失禁5 分、失禁0 分);穿衣(可自主穿衣10分、協助穿衣5 分、不能自己穿衣0 分);洗澡(可自主洗澡5 分、協助洗澡5 分);進食(自主進食10 分、協助進食5 分、不能進食0 分);移動(自主移動15分、 需要部分幫助移動10 分、 需要極大幫助移動5分、不能自己移動0 分);如廁(自主如廁10 分、協助如廁5 分、完全不能自己如廁0 分);行走(自主行走15 分、協助行走10 分、輪椅協助5 分,不能自己0分);上下樓梯(自主上樓梯10 分、協助上樓梯不能自己上樓梯 0 分);修飾(佳 5 分、差 0 分)。 總分 100分,評分越高表示其生活自理能力越高,對他人的依賴越低。
1.3.3 運動功能評估[7]分別于治療前和治療結束后應用Fugl-Meyer 運動功能評分量表(FMA)對患者的上下肢運動功能進行評估, 內容包括上下肢的肌肉反射活動、反射亢進、伴有協同運動的活動、屈伸肌協同運動、關節穩定性、脫離協同運動的活動、協調能力、速度等項目,每項評分0~2 分,其中上肢運動功能評分總分66 分,下肢34 分,總分 100 分,評分越高表示運動功能越好。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Epidata3.1 建立數據庫, 并進行數據錄入和校驗, 應用SPSS23.0 進行描述性統計及t 檢驗等,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病恥感評分比較 治療前兩組患者病恥感各維度和總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常規組患者的疏離因子、歧視因子、抵抗因子評分和總評分較治療前均降低,治療后研究組患者除刻板因子維度以外的其他維度評分和總評分較治療前均降低, 且治療后研究組低于常規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3)。
表3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病恥感評分比較(分,)

表3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病恥感評分比較(分,)
組別 例數 刻板因子 t P 疏離因子 t P 歧視因子 t P治療前 治療后 治療前 治療后 治療前 治療后常規組 49 14.30±3.15 14.08±3.51 0.327 0.745 14.97±3.05 13.12±2.98 3.037 <0.001 12.17±2.08 11.24±2.49 2.006 0.048研究組 49 14.74±3.39 13.96±3.06 0.337 0.737 14.93±3.12 11.25±2.90 6.047 <0.001 12.29±2.58 8.95±2.03 7.122 <0.001 t 0.666 0.180 0.064 3.148 0.253 4.990 P 0.507 0.857 0.949 0.002 0.800 <0.001組別 例數 社會退縮 t P 抵抗因子 t P 總分 t P治療前 治療后 治療前 治療后 治療前 治療后常規組 49 14.43±3.12 13.95±4.01 0.661 0.510 12.32±2.07 11.03±2.14 3.033 <0.001 68.19±8.05 63.42±7.90 2.960 0.004研究組 49 14.60±2.97 12.15±2.06 4.745 <0.001 12.71±2.48 9.96±2.35 5.634 <0.001 69.27±10.02 56.27±7.55 7.253 <0.001 t 0.276 2.795 0.845 2.357 0.588 4.465 P 0.783 0.006 0.400 0.020 0.558 <0.001
2.2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日常生活、運動能力評分比較 治療前兩組患者MBI 及上、下肢FMA 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 MBI 及上、下肢 FMA評分較治療前均升高,且治療后常規組低于研究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4)。
3 討論
3.1 康復臨床路徑聯合團體心理治療可以降低患者病恥感 本研究結果顯示研究組患者治療后的病恥感評分低于常規組, 提示康復臨床路徑結合團體心理療法有助于降低患者的病恥感。 腦卒中患者普遍存在心理障礙, 其不良的預后和不可逆的損傷使患者因為生活無法自理、 生活需要被協助和需要長期被照顧等問題產生不同程度的羞恥體驗,即病恥感。病恥感的產生會極大地影響患者的康復結局和生活質量,使患者社會活動減少,社會身份喪失,對其尋找社會資源幫助產生很大的限制。 康復臨床路徑是一種分層級、分階段腦卒中康復方案,但需要患者有較高的康復主動性。 但研究指出,病恥感會對腦卒中患者康復過程中的主動性和功能恢復效果產生不利影響,使患者的康復表現和結局降低。 但目前,臨床有關腦卒中患者病恥感的研究和干預均未得到重視[8,9]。 團體心理治療是一種有效的醫學心理干預方式,其通過團隊成員之間的交流和互動可促進成員的自我了解、接納、發展和自我實現,其具有增強團隊凝聚力、改善人際溝通、構建社會支持體系等作用,對不同人群都具有廣泛的適用性。 本研究中以認知行為治療理論為依據, 設計了針對缺血性腦卒中患者的團體心理治療方案, 通過提供患者宣泄情感的環境氛圍,糾正其錯誤地自我羞辱感的信念,激發團體成員之間共同面對、 互相幫助的動力等來減少患者的孤立感, 而康復效果的改善又能幫助患者盡快實現自理能力,提高康復自信心和滿足感。
3.2 康復臨床路徑聯合團體心理治療可以改善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和運動功能 本研究結果顯示研究組患者治療后的日常活動能力和運動功能評分優于常規組, 提示康復臨床路徑結合團體心理療法有助于改善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和運動功能。 循證醫學研究指出, 腦卒中患者的早期康復治療在降低患者致殘率和提高生活質量方面的作用已經得到國內外的公認。 腦卒中康復是康復醫學體系發展的重中之重,但其同時也存在很多問題,例如缺乏循證醫學證據,不同地區、醫院,甚至是醫務人員缺乏統一的、規范性的康復治療方法和流程,以及缺乏臨床應用經驗。康復臨床路徑是指醫務人員針對缺血性腦卒中患者的治療、 康復護理等制定出一個最為合適的康復照護計劃,是一種現代化的護理管理模式,以時間為橫軸,以入院指導、康復宣教、心理護理、康復訓練等手段為縱軸, 將整體的康復護理計劃制定成一個日程計劃表,不僅能保證康復訓練的完整和優質完成,顯著提升康復效果, 還能減少資源浪費, 縮短康復時間,同時能實現患者、家屬與醫務人員之間的信息共享[10]。臨床路徑康復治療與常規康復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對具體的康復治療技術和內容進行了規定,使其更加標準化和規范化, 進而能有效促進康復治療效果的提高[11]。
綜上所述,康復臨床路徑結合團體心理療法能降低缺血性腦卒中患者的病恥感,有利于患者的認知功能障礙和心理康復,使其能夠積極參與到術后的康復治療中,從而能提高患者日常生活活動能力和運動能力的恢復,改善患者預后,提高其生活質量。
表4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日常生活、運動能力評分比較(分,)

表4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日常生活、運動能力評分比較(分,)
組別 例數 MBI 指數 t P 上肢FMA t P 下肢FMA t P治療前 治療后 治療前 治療后 治療前 治療后常規組 49 43.10±8.94 52.37±8.04 5.397 <0.001 22.11±7.89 30.07±9.85 4.415 <0.001 13.57±5.19 26.06±6.83 10.192 <0.001研究組 49 44.03±9.01 74.29±10.08 15.667 <0.001 21.93±8.08 41.04±7.92 11.823 <0.001 14.03±5.74 30.63±6.47 13.435 <0.001 t 0.513 11.900 0.112 6.076 0.416 3.400 P 0.609 <0.001 0.911 <0.001 0.678 <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