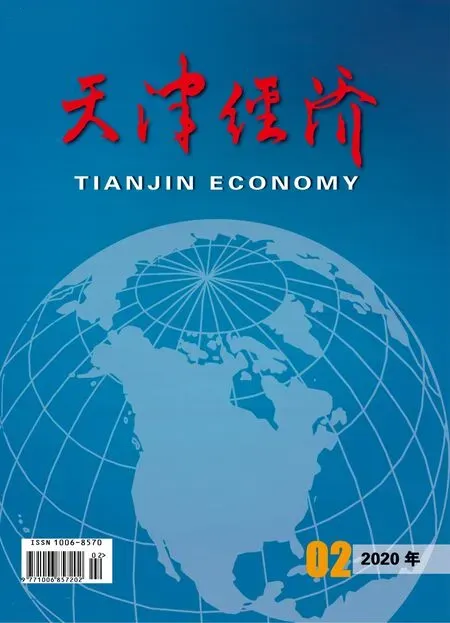金融業增加值占比的國內外比較及思考
◎文/王會奇
一、金融業增加值占比的國內外比較
(一)世界主要發達國家金融業增加值占比對比
1.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金融業增加值波動幅度不大,近年來呈現下降態勢。從整 體 看,1998—2017 年27個OECD 國家 (未選取數據缺失超過2 年的國家) 金融業增加值占比在5.71%~6.53%之間波動,2005 年達到6.53%的峰值,2008 年降至5.71%的低點,2015 年回升至6.39%,此后逐年下降,2017 年為6.15%。分國家看,美國的金融業增加值占比,近20 年基本保持在7%左右,2001 年達到最高值7.83%,2008 年下降到最低值6.23%,2016 年回升到近幾年的高點7.63%,2018 年為7.4%。 英國的金融業增加值 占 比,1998—2003 年 在5.5%上下波動,2009 年達到最高值9.18%后逐年下降,2018 年為6.86%(見圖1)。
2.主要發達國家金融業增加值占比基本保持在7.5%以內。 從2017 年27 個OECD 國家金融業增加值占比的橫向對比看, 除澳大利亞(9.48%)和瑞士(9.25%)兩個國家之外, 其他國家金融業增加值占比均未超過7.5%, 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區間:7.1%~7.5%區間有4個國家,包括美國、愛爾蘭、荷蘭和英國;4.9%~6.2%區間有7個國家,包括韓國、意大利等;2.9%~4.2%區間有13個國家,包括日本、德國、法國等(見圖2)。如果考慮金融市場結構對金融業增加值的影響, 德國和日本的金融市場是以間接金融為主, 德國金融業增加值占比在1999年達到最高值5.43%,之后基本處于下降趨勢,2018 年為3.69%;日本金融業增加值占比的變化趨勢與德國相似,2003 年達到最高值6.07%,2017年降至4.15%。
(二)我國金融業增加值占比變化趨勢及與OECD 國家的對比
1.我國金融業增加值快速增長,占比上升幅度較大。1978—2018 年,我國金融業增加值年均增速達到19.33%。從增速變化情況看,目前正處于從2007 年開始的下降通道內。 2018 年,我國金融業增加值為6.91 萬億元,同比增速為5.67%。 從金融業增加值占比變化看,基本呈現向上的態勢,從2005 年 的 3.99% 上 升 到2015 年的8.44%, 之后有所回落,2018 年為7.68%。
2.我國金融業增加值占比相繼超過德國、 日本、韓國、美國、英國等國家,目前高于大多數OECD 國家。 本文對比分析的27 個OECD國家中, 只有澳大利亞和瑞士金融業增加值占比高于我國。 2018 年,我國金融業增加值占比為7.68%, 分別高于美國、英國、德國、法國和韓國0.28、0.82、4.20、3.99 和2.17 個百分點。 考慮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對金融業增加值占比的影響, 粗略對比與當前我國人均GDP 處于同一水平時發達國家的金融業增加值占比,2018 年我國人均GDP 約9770.85 美元, 韓國在1999 年人均GDP 約1 萬美元時金融業增加值占比為6.77%, 與我國2018 年的水平相比低0.91 個百分點。

圖1 中國和主要發達國家金融業增加值占比變化情況

圖2 2017 年中國和27 個OECD 國家金融業增加值占比散點圖
(三)天津與國內部分省市金融業增加值對比
1.天津金融業增加值年均增速高于全國, 但近年來增速出現下滑。 1978—2018年, 天津金融業增加值年均增速達到36.73%,高于全國17.4 個百分點。 從增速變化情況看, 除個別年份天津增速遠超全國外, 兩者保持了近乎同步的趨勢。 但在2012年后, 天津金融業增加值增速開始下滑,2018 年該指標僅為0.78%, 低于全國4.89個百分點。
2.2011 年后天津金融業增加值占比已超過全國。1978 年,全國和天津的金融業增加值占比分別為2.08%和0.16%, 天津金融業增加值占比明顯低于全國。 改革開放之后, 天津金融業增加值占比在全國平均水平上下小幅波動, 但從2011 年之后, 天津金融業增加值占比開始持續超過全國水平,并且兩者差距不斷增大。 2018年, 天津金融業增加值占比為10.46%,高于全國2.78 個百分點(見圖3)。
3.天津金融業增加值占比居全國各省市前列。 從各省市的金融業增加值絕對值看,2017 年天津金融業增加值為1951.75 億元, 在全國排名第13 位;但從金融業增加值占比看, 天津僅次于上海和北京。 對比天津與國內其他直轄市和一線城市,天津金融業增加值占比改革開放后長期低于其他直轄市和一線城市,2013 年后開始逐漸超過重慶和廣州。 2018年, 天津金融業增加值占比分別比北京、 上海和深圳低6.31、7.23 和2.21 個百分點,比廣州和重慶高1.36 和0.92 個百分點。
4.天津金融業增加值占比的波動幅度高于全國,但低于四個一線城市。 與全國平均水平對比,1978—2018年, 天津金融業增加值占比標準差為2.68, 比全國高0.97。 與一線城市對比,1990—2018 年,天津金融業增加值占比標準差為2.18,比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指 標 分 別 低0.01、0.81、0.82和0.21, 表明天津金融業發展較一線城市更為穩定。

圖3 全國和天津市金融業增加值占比變化情況
二、影響我國金融業增加值占比的主要因素及需關注的問題
我國金融業增加值占比快速上升并處于相對較高水平, 其主要原因是我國金融市場體系不斷完善和壯大。改革開放以來, 我國金融業在制度設計、市場建設、機構培育等方面取得巨大進步,金融業活力和潛力得到極大釋放, 在支持和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應該說,這一指標的變化, 是我國金融業發展成就的一個客觀反映。 但同時也應看到其中的深層次原因和需要關注的問題, 這樣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刻認識和理性看待金融業增加值占比問題。
(一)從資金供給側看,高儲蓄率為金融業快速發展創造條件
我國儲蓄率長期保持在32%以上,2000—2010 年從36.70%上升到51.79%,之后有所回落, 但仍然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2018 年,我國國民儲蓄率為45.29%,高于發達國家22.57 個百分點,高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12.63 個百分點,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8.63 個百分點。高儲蓄率為我國依靠大量信貸資金投放支持投資, 進而拉動經濟快速增長奠定基礎, 也為金融業快速發展創造了條件。儲蓄率高,儲蓄轉化為投資過程中所需要金融業提供的服務就較多, 金融業增加值也就相對較高。
(二)從資金需求側看,高杠桿率、 高投資率進一步刺激金融機構快速發展
改革開放后我國曾長期處于“高投入、高產出”的粗放式增長模式, 各類經濟主體都存在著強烈的融資需求, 特別是國有企業高杠桿運營, 非金融企業杠桿率高居不下, 遠高于主要發達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 2018年, 我國非金融企業杠桿率為151.6%, 而世界總體為90.9%, 發達國家為91.3%,新興市場國家為90.5%,G20國家為91.4%。 與此同時,2000 年后我國經濟投資拉動特點明顯, 資本形成率持續上升, 尤其是為了應對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通過大量基礎設施建設刺激經濟,2011 年資本形成率一度高達48.01%, 此后雖有回落, 但 2017 年 仍 高 達44.41%。高杠桿率、高投資率從需求側刺激金融機構的快速發展,金融業機構數量、資產規模和從業人數快速上升。 截至2018 年末,全國各類金融機構法人數達到5659 家, 金融業總資產300萬億元, 銀行業總資產規模位居全球第一,債券市場、股票市場和保險市場均已位居全球第二。
(三)從資金配置方式看,在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市場結構下, 金融機構提供更多服務、承擔更多風險
經濟主體投資方式和路徑依賴決定其融資習慣,進而影響金融市場的結構和發展路徑。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業呈現以銀行業為主導的特點,2018 年銀行業總資產在金融業中占比高達89.34%。 2002 年以來,社會融資規模增量中各類貸款占比約在七成以上,2018 年為74.76%。相對于直接融資,間接融資需要金融機構為資金供求雙方提供更多服務,開發更多金融產品, 導致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市場中有更多的金融機構和從業人員,這些都會對構成金融增加值的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固定資產折舊和營業盈余產生影響。此外,銀行業具有較強的順周期特點, 在經濟上升期獲取大量盈利的同時也隨之積累風險, 在經濟下行周期時這些風險有可能會削減金融機構的資產和盈余。現有金融業增加值核算方法無法體現這些潛在風險,可能導致當前金融業增加值數據“虛高”。當經濟下行時,該指標可能會大幅下降。
(四)從資金配置效率看,拉動產出效率降低導致信貸投放不斷擴張
在資本邊際效率遞減效應、投資依靠信貸投放、粗放式經濟增長模式等因素共同影響下, 持續的經濟高速增長導致信貸投放規模不斷上升, 但貸款產出效率呈持續下降態勢。從GDP/人民幣貸款指標看, 改革開放以來該項指標在不斷下降, 全國從1980 年的1.74 下降到2018年的0.66,天津從1980 年的1.01 下降到2018 年的0.58。在我國經濟依然保持中高速增長的趨勢下, 信貸拉動產出的效率下降, 信貸投放的規模也就被迫持續上升。 大量的信貸投放會增加金融機構的收益, 推動金融業增加值快速增長, 但未能反映背后的資本邊際效率問題和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效率問題。
(五)從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系看, 結構性失衡問題進一步推高金融業增加值占比
縱觀西方國家的金融史, 資本的盲目逐利常常導致金融活動脫離實體經濟,導致金融資產和金融交易規模偏離實體經濟而高速增長。據上交所《滬市上市公司2018 年年報整體分析》報告,2018 年滬市金融類上市公司實現營業收入6.97 萬億元, 凈利潤1.65 萬億元;實體類(非金融類)實現營業收入26.53 萬億元, 凈利潤1.15 萬億元; 滬市金融類上市公司凈利潤占全部上市公司的58.93%,并且金融類上市公司凈利潤/營業收入也遠高于實體類上市公司。 資金因追逐利潤會從實體經濟流入金融業, 導致過度金融化現象突出: 大量實體企業介入銀行、保險、信托、證券、基金等金融業, 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亂辦金融現象; 金融業大量資金流入股市、 房地產等領域,催生資產泡沫;資金在金融領域空轉以追求短期收益最大化,“脫實向虛”。此外, 多數地方政府熱衷發展金融, 將金融產業作為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給予大量的優惠政策支持。 各種因素疊加導致金融業規模快速擴張, 金融與實體經濟結構性失衡。 過高的金融業增加值占比, 也是對這種結構性失衡的一種反映, 從長期來看, 不利于實體經濟成本的降低、 整個社會資源配置效率地提升和我國實體經濟部門在國際市場和產業鏈中地競爭。
三、結論和建議
總的來說, 通過比較和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幾點判斷:一是從國際上看,主要發達國家金融業增加值占比相對 穩 定, 近20 年27 個OECD 國家金融業增加值占比平均水平在6%上下波動,2015 年以后呈下降態勢,但各國之間在指標水平和變化趨勢上存在一定差異。 二是我國金融業增加值占比在2005 年以后增長較快, 現已高于大多數OECD 國家,2015 年開始回落,與主要發達國家整體變化趨勢相同;從國內各省市對比看, 上海和北京金融業增加值占比遠超其他省市, 反映了其作為全國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影響,天津居全國各省市前列。三是我國金融業增加值占比快速上升并處于相對較高水平, 主要是反映了金融業發展成就和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 但也存在一些深層次原因,高儲蓄率、高杠桿率、高投資率、 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市場結構、 資金拉動產出效率以及金融與實體經濟的失衡問題等, 都是推高我國金融業增加值占比的重要影響因素, 也是需要引起關注的問題。
綜合以上對比和分析,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一)理性看待金融業增加值占比
從指標含義看, 金融業增加值占比是一個受經濟結構、金融市場發展、投融資方式等因素影響而動態變化的指標, 反映金融業發展與經濟發展的動態關系, 不能簡單地將其作為衡量金融業發展的唯一指標, 也不能將其持續上升或保持在較高水平與金融業發展劃等號。 從指標水平看,國際橫向對比,我國金融業增加值占比已經處于相對較高水平, 高于大多數發達國家; 國內各省市對比, 天津金融業增加值占比處于相對較高水平, 在各省市中僅次于上海和北京,2018 年高于全國2.78 個百分點。從指標變化趨勢看,國際上英國、德國、法國、日本等國家已呈現下降走勢,未來隨著我國經濟金融改革地有序推進、儲蓄率下降、直接融資占比上升、 金融業回歸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本源、潛在金融風險水平下降, 預計金融業增加值占比總體上會趨于下降。
(二)著力提升金融業增加值的“含金量”
金融業的發展不能簡單通過擴大規模和追求短期效益實現數量上的增長, 在數字上推高金融業增加值及在GDP 中的占比,而是應該更加注重質量上地提高, 通過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金融業高質量發展,避免金融業增加值“虛高”問題, 真正提升金融業增加值的“含金量”。特別是,應著力解決金融市場的結構問題,以金融體系結構調整優化為重點, 優化融資結構和金融機構體系、市場體系、產品體系,擴大直接融資比例,避免通過過度依賴擴大信貸投放, 推動金融業的粗放式增長; 著力解決金融資源的效率問題,強化金融服務功能,防止資金“空轉”和“脫實向虛”,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更高質量、 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務, 提升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和拉動產出效率; 著力解決金融體系的風險問題,積極、 穩妥、 有序化解金融風險, 擠出金融增加值中的風險水分。
(三)進一步優化金融業增加值核算方法
現有金融業增加值核算方法主要是借鑒國際通行的統計方法, 在如何適應我國金融發展實際方面, 還有進一步改進和完善的空間。 如金融業增加值季度數據參照人民幣存貸款余額增速、證券交易額增長速度、 保費收入增長速度進行推算, 但支付結算、 金融信息咨詢等業務的快速發展使得現行季度估算方法難以反映金融發展全貌。為此,應在保持與國際接軌、保證可比性的基礎上,通過適時調整核算范圍、合理考慮風險因素等方式改進核算方法, 使核算方法充分適應我國發展實際, 能夠更加全面、 真實反映我國金融業發展變化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