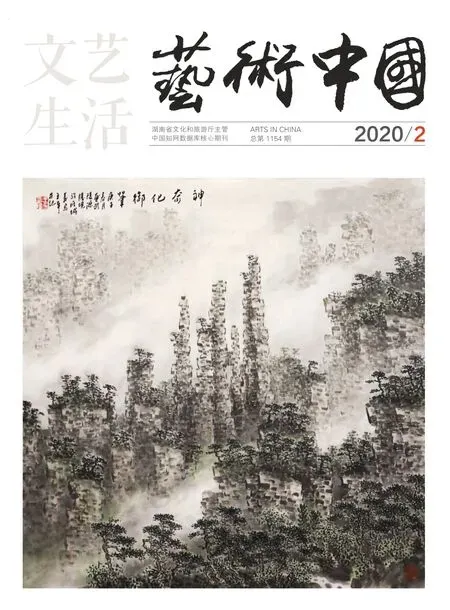硯銘隨刀錄
◆(廣東 深圳)
硯銘之道
“硯”為文房四寶之一,乃文人畫(huà)士隨身不離之物。硯上刻字,古已有之,多為紀(jì)年,文章少見(jiàn),至兩宋文采風(fēng)流,金石之學(xué)盛行,又有東坡、襄陽(yáng)等文人學(xué)士癡硯愛(ài)石,為之題文作句,風(fēng)行一時(shí),遂成硯銘之道。后世稱(chēng)斯文者多有于硯上題文刻字之好,漸成風(fēng)雅之舉。然治銘先需有硯,佳硯難求,得之不易,故于硯銘之道成可觀之規(guī)模者寥寥無(wú)幾。乾隆帝王之身,喜作硯銘,凡宮中所藏,無(wú)論新老多題文治銘,民間則以曉嵐、冬心、南村、鞠人、苦鐵為代表。近來(lái)西學(xué)勢(shì)盛,文心日散,文脈漸斷,文士胸懷只留在那一頁(yè)頁(yè)文字和歷史之中,加之書(shū)寫(xiě)工具的變化、墨汁的流行,硯臺(tái)已離大眾日久,硯尚不存,銘何以附?此道衰矣。然實(shí)可悲者,今硯上落字,或于古硯制偽銘,或于今硯上落某某大師名款。嗚呼,真乃對(duì)文器之褻瀆、對(duì)文字之褻瀆!硯石有靈,何不落淚?我本山川靈秀,知者已去,竟淪落風(fēng)塵至此!
銘者,記也,所記者事與情,即人之事、人與人之事、人與物之事,人之情、人與人之情、人與物之情。歷來(lái)硯銘或記事或抒情,記事者記錄歷史,抒情者借物言志。記錄歷史者,曉嵐之銘多有所為,而今觀之,昔人之來(lái)往、昔人之所見(jiàn)借硯以傳,歷歷在目。借物言志者,情有所托,物則借情以生靈。千百年后,物難以存,文字猶在,見(jiàn)文思情,如見(jiàn)其人,如視其物,是以為精神長(zhǎng)存。
而今硯銘之衰亦可見(jiàn)傳統(tǒng)文化之衰,我輩此生若與硯有緣,可否勉力為之,雖不可望先賢之項(xiàng)背,唯求斯文不斷、硯道不絕而已。
硯以銘貴及硯以銘廢
昔人云“硯以銘貴”,所貴者,文化之提升也。文化為何?自然、人文而已,稱(chēng)其大,可包容天地,囊括古今;稱(chēng)其小,又可隱于衣食住行、春花秋月間。小小一硯,等閑器具,唯研墨儲(chǔ)墨之用耳,卻可集自然、人文于一身,石材之精、石材之美,是為自然之功,雕刻之精妙、銘文之提升是為人文之功,合二為一成就文化。只有石材之功,不成文化,得石材之精美、雕刻之精妙可以成器,可稱(chēng)文化。然尚為文化之個(gè)體、銘文之功在于將硯文化之個(gè)體與中華文化溝通,連成一體,既為硯文化之提升,又為硯文化之?dāng)U展,使我們于一石一硯中可展思緒于天地間,放心胸于千萬(wàn)年,留下那春花朝露,輕撫那秋月流云。硯何不以銘貴乎?
硯以銘貴,貴在硯文化之提升與擴(kuò)展,即人文之功。然所刻文字,若文章雜亂,書(shū)法幼稚,運(yùn)刀生澀,非但文化得不到提升與擴(kuò)展,反有阻礙文化提升擴(kuò)展的效果,好比一畫(huà),畫(huà)尚可,而提款文俗字丑,則畫(huà)也廢了,硯亦如是。故硯可以銘貴,也可以銘廢。
硯銘之道實(shí)為陽(yáng)春白雪,功夫遠(yuǎn)在于硯外,為文人之逸興,非工匠之所為,若以之謀利為生則廢。當(dāng)以平和之心對(duì)待,貶之一笑,褒之一笑,不求人人稱(chēng)善,但求不曲我心,真情真意,隨念為之。此心境為治銘之前提,若無(wú),此道不可為!
一硯一味及一硯一銘
硯之成敗在乎石、工、銘三者。石不珍則不貴;工不精則不成器;銘不高則不得神,難稱(chēng)雅器,三者缺其一終是遺憾。具體而言,石之花色紋理為天然圖畫(huà),絕無(wú)重復(fù),有唯一性。硯工制硯設(shè)計(jì)時(shí),當(dāng)結(jié)合硯石之花色紋理展開(kāi),取天然人為之妙,治銘則應(yīng)顧及石與工之特色,無(wú)論是文體、字體還是布局都應(yīng)斟酌考慮,但求統(tǒng)一。
石、工、銘三者若能互為呼應(yīng),相得益彰,渾然一體,工彰顯石之美,銘彰顯石與工之美,石又反襯工與銘之妙,一硯在手焉不為美妙之事?故而硯銘難以相互套用,應(yīng)結(jié)合一硯具體特征引申之,一硯一味,一硯一銘,最終達(dá)到一種統(tǒng)一的美。
文、書(shū)、刀三功
硯銘雕蟲(chóng)小技耳,然所需前提功課卻不少,主要是詩(shī)文、書(shū)法、金石三學(xué)。
詩(shī)文當(dāng)以硯為本,涉及文事,舒展心胸,引無(wú)限思緒者為上。雖不求太白句,尚不可失文士心。書(shū)法貴乎氣息正,雖書(shū)體可多樣,章法可變化,然古、靜、雅不可失,絕不可張牙舞爪,以古怪為能事,以畸變?yōu)楦呙鳎栌刑锰弥畾狻⒈虮蛑L(fēng),若得高古之意,則已入阿羅漢果。至于此處所講金石之學(xué)乃廣義金石之學(xué),非單指篆刻之學(xué),尚含金文、碑刻等諸多內(nèi)容,故治銘之用刀非單指篆刻之用刀,所含刀法更為豐富,此點(diǎn)須特殊說(shuō)明,具體見(jiàn)后詳述。
此三學(xué)于硯銘之道相互獨(dú)立又相互交融,你是你,我是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失一則全廢。然書(shū)與刀相對(duì)于文更不可分,兩者須刀中有筆、筆中有刀。筆軟刀硬,功力全在這軟硬之間。“有筆”指可表現(xiàn)筆之彈性,及用筆之輕重緩急、陰陽(yáng)頓挫、輾轉(zhuǎn)變化,若存運(yùn)筆之行氣,是為高手。“有刀”指刀路清楚,落刀肯定,直中有曲,曲中有直,不思有刀而刀自行,若能得腕底蒼厚之氣,是為高手。

菩提佛音 篆刻 王正光
王正光篆刻選

畫(huà)意人生

靜觀八荒

木秀于林

硯癡印癖
硯銘不同印章,印章須壓蓋后欣賞,硯銘有直接觀賞性,拓之要有筆意,視之要有刀味,此為治銘最大要訣也,不可不明。
治銘步驟
1、相硯
新得一硯,先不急治銘,放于案頭,置于枕邊,撫之握之,感之念之,記掛于心。相處日久,對(duì)其了解認(rèn)識(shí)就深,所作之銘方可入其髓,得其神,打動(dòng)人心。
吾治硯銘,一般習(xí)慣將欲刻之硯放于案頭或床邊,沒(méi)事看看摸摸,件件種于心里,埋于胸中,務(wù)求對(duì)每方硯的精神氣質(zhì)能有一個(gè)準(zhǔn)確的把握,不知何時(shí)靈光一閃,文章自然隨口自來(lái)生。很多句子是在坐車(chē)或課間所得,往往以煙殼或備課本的邊邊角角先草草記之,再回家根據(jù)韻譜逐字斟酌,反復(fù)推敲,并寫(xiě)好掛于墻上,過(guò)幾日高聲讀幾遍,以修正其音韻不順,用字不精處,如此反復(fù)幾遍,滿(mǎn)意后方定稿。
若治一銘需十日,只相硯一項(xiàng)當(dāng)占九日光陰。
2、思文
此過(guò)程分定文體與索句兩步。如前所述一硯一味,而文體之選擇為第一步調(diào)味。硯銘文體或古風(fēng)或楚辭或律詩(shī)或絕句,或詞或曲或隨筆均可為之,選用何種文體當(dāng)以所銘之硯的味道而定,硯味敦厚可用古風(fēng),硯味浪漫可用楚辭,硯味穩(wěn)重可用律詩(shī)或絕句,硯味娟秀可用詞曲,然此非定式,需要酌情處理,唯求意味相應(yīng)、硯味統(tǒng)一而已。此外,治銘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長(zhǎng)短句亦均可為之,除長(zhǎng)短句外,或四句或八句或十六句或長(zhǎng)篇,然兩句不成篇,亦不成文,文之不成何稱(chēng)銘文,故不可用。
索句當(dāng)一硯一銘,如前所述能以硯為本,涉及文事,舒展心胸,引無(wú)限思緒者為上。若著重于硯石之特色或雕工之特色引申開(kāi)去,也是一法,總之硯不離銘,銘不離硯,找句唐詩(shī)宋詞摹寫(xiě)上去,自然是不行的。但求千百年后,硯如不存,后人如見(jiàn)其銘,仍不免悠悠于心,念念于胸。
銘文內(nèi)容或記事或抒情,記事者可記文事,可記硯事,亦可立論。抒情者可抒愛(ài)硯之情,可抒文墨之情,可以怨霜月,可以唱大風(fēng),可言丈夫志,可訴女兒情,春秋萬(wàn)古,天高地闊俱可收之入筆端,也正因如此,銘文對(duì)硯文化的提升與擴(kuò)展作用方得以體現(xiàn)。
至于氣質(zhì)才情、文采風(fēng)流則不一而論矣。
3、選體
文章既成當(dāng)定書(shū)體,此為第二步調(diào)味。中華文字演變有序,面貌多樣,諸美大雅,大體上可分篆、隸、行、楷、草五類(lèi)。從字體上說(shuō)只篆文就有甲骨、蟲(chóng)魚(yú)、金文、籀篆、小篆、漢篆等等名目,從風(fēng)格上說(shuō)只行書(shū)就有二王、蘇、黃、米、蔡等等面貌,就我等平日作書(shū)而言,心境不同,心緒不同,甚至筆不同,紙不同,面貌亦不同。而書(shū)風(fēng)與文風(fēng)的和諧是一幅好書(shū)法不可缺少的,硯銘亦如是。
硯銘亦有不同于書(shū)法之處,書(shū)法考慮書(shū)風(fēng)與文風(fēng)的和諧,最終以字為本,而硯銘考慮書(shū)風(fēng)于文風(fēng)的和諧最終須以硯為本,也就是說(shuō)書(shū)風(fēng)與文風(fēng)的和諧最終是為了整個(gè)硯味的和諧。選書(shū)體時(shí)硯味高古,書(shū)味當(dāng)高古;硯味敦厚,書(shū)味當(dāng)敦厚;硯味清秀,書(shū)味當(dāng)清秀;硯味清曠,書(shū)味當(dāng)清曠。但如果自家書(shū)法已至苦鐵、冬心等高人“萬(wàn)美納一美、一美生萬(wàn)美”之境界,亦可百硯一體、萬(wàn)法歸一,此為美學(xué)問(wèn)題,不作詳述。
4、辨字
治銘須有治學(xué)態(tài)度,刻石以銘,立文后世,文字?jǐn)嗖豢沙鰡?wèn)題,每用一字無(wú)十足把握,應(yīng)認(rèn)真翻查考證。
在用字上比較容易出現(xiàn)的問(wèn)題為繁簡(jiǎn)體混用、行草楷混用,均屬別字。如用篆文,尚需一定古文字功力。在此說(shuō)一辨字方法,以供大家參考,第一步先查《說(shuō)文解字》以明文字立意;第二步查《金石大辭典》以清文字源流;第三步查《篆刻大辭典》以觀文字變化;第四步翻看《書(shū)法大辭典》以理文字筆勢(shì),最后根據(jù)四者結(jié)合全篇架構(gòu)安排經(jīng)營(yíng)之。
5、布局
古來(lái)硯銘多刻于硯背或硯側(cè),亦有刻于正面者。刻于硯背者或居中或居側(cè),或滿(mǎn)布或留白。刻于硯側(cè)者則有一定規(guī)矩,右為前,左為后,一般硯名刻于右側(cè)上方,銘文刻于左側(cè),如不刻硯名,銘文可刻于右側(cè),落收藏章于左側(cè)下方,如只有收藏章,也不可刻于右側(cè),還是在左側(cè)下方。至于刻于正面者,基本是在上方。硯銘布局有規(guī)矩,但無(wú)定式,或穩(wěn)或巧,依勢(shì)布局,補(bǔ)其空白,穩(wěn)其格局是也。
至于布局目前有以下三種情況值得商榷:
一是將文字等同于雕工,以文字補(bǔ)石之瑕疵處。文高于藝,藝高于工,堂皇文章豈可以之補(bǔ)殘?zhí)钇啤G诣Υ锰幨|(zhì)多軟硬不均,松緊有別,也有礙表現(xiàn)筆鋒變化微妙處。在一些比較粗的石頭上,余一般不作小楷與小篆,亦為此理。
二是認(rèn)為文字不能過(guò)大,更不可掩蓋石品。硯之石、工、銘三者,石在乎天然,工在乎人為,銘在乎文化,制硯一般以石之美者為正面,故正面當(dāng)以石、工二者為重,硯之兩側(cè)及背面則當(dāng)以文章為重,也就是說(shuō)正面如落字當(dāng)銘遷就于石與工,背面當(dāng)石遷就于銘,正反各有主次,各盡其味。此外認(rèn)為文字不能過(guò)大者還有一種說(shuō)法,認(rèn)為文字大會(huì)顯得硯小。試問(wèn)硯越大就越好嗎?有些小巧把玩硯刻兩三大字,更顯硯小,豈不是更可愛(ài)嗎?所以字之大小不是小巧就好,關(guān)鍵是合適。

圖1


圖2

圖3

圖4
三是刻文后以顏料填之,往往字形有變,運(yùn)筆出鋒收鋒含糊,刀法含糊,刀味不全,且色彩鮮艷,與石與工相脫離,難得統(tǒng)一。應(yīng)筆意刀鋒與石品渾然一體,字不礙石,石不礙字,字中有石,石中有字,實(shí)為正途。
6、書(shū)硯
書(shū)銘上石,必用毛筆,如于紙上寫(xiě)去便是,斷不可以鉛筆描畫(huà)或拷貝,否則筆意盡失,行氣難存,筆端素毫旋轉(zhuǎn)微妙處更難以體現(xiàn)。若將毛筆書(shū)法縮小拷貝到硯上再行摹刻,實(shí)有雙鉤之嫌,工匠所為。
7、定式
定式即定文字刻制形式,可分以下幾種:散底、尖底、平底、圓底、雙鉤、凸底、平底陽(yáng)刻、沙底陽(yáng)刻。
散底者即所刻文字不修底,余留刀鋒刀路,此法看似簡(jiǎn)單,實(shí)則頗為講究,最易為之又最難為之,所易者刻制較快,所難者刀鋒間當(dāng)陰陽(yáng)頓挫,疏密有秩,輕重緩急、橫砍豎劈間酣暢淋漓,意雄氣壯。(見(jiàn)圖一)
尖底者指每一筆畫(huà)呈一定角度傾斜,底尖處有一條清晰的“線(xiàn)路”。此法需要修底,講究字底“線(xiàn)路”合乎“筆路”,適合中鋒用筆之書(shū)體,尤其是小楷與小篆。(見(jiàn)圖二、圖三)
平底者指修平底,此法較為費(fèi)時(shí),需要耐心為之,一日做不得幾字,較適合大字。(見(jiàn)圖四)
圓底者指文字凹下處為弧面,刻制時(shí)可先以尖刀開(kāi)路,再以圓口刀反復(fù)修刻,適合表現(xiàn)古文大篆。(見(jiàn)圖五)
雙鉤之法指只將文字輪廓以陰線(xiàn)勾出,如遇大字,偶可為之。(見(jiàn)圖六)
凸底之法指先雙勾,再將雙勾之內(nèi)筆畫(huà)修成弧面,多為大字。(見(jiàn)圖七)
至于平底陽(yáng)刻、沙底陽(yáng)刻裝飾性較強(qiáng),偶一為之即可。(見(jiàn)圖八)
8、運(yùn)刀
拓之有筆意,視之有刀味,至微妙處則為運(yùn)刀時(shí)以刀鋒得其刀味,以鋒背得其筆味。此中秘訣只可言及于此,尚需意會(huì)。
至于刀法大概可概括為:沖、切、琢、旋、劃、打、點(diǎn)、挑八法。

圖5

圖6

圖7

圖8
“沖刀法”開(kāi)筆路,定間架,須肯定果斷,落刀準(zhǔn)確。“切刀法”揚(yáng)氣勢(shì),分節(jié)奏,須陰陽(yáng)頓挫,疏密有秩。“琢刀法”起滄厚,去圭角,須發(fā)中有收,收中有發(fā)。以上三法為基本刀法,切、琢二法往往同時(shí)存在。
筆法要訣在于筆之旋轉(zhuǎn),刀法亦如是,故有“旋刀法”,此法為治銘諸刀法之絕妙法,所謂銘文拓之要有筆味,即要能表現(xiàn)毛筆的彈性,關(guān)鍵亦在于此。
“劃刀法”主要用于修底,多用于尖底、平底、圓底之形式。
有的字體切刀尚不足表現(xiàn)其陽(yáng)剛,則有“打刀法”,此法左手持刀,右手持木錘,敲打而成,似于制硯,唯精確程度勝之。
點(diǎn)、挑二法見(jiàn)于文字精微處,點(diǎn)者用于文字筆畫(huà)出鋒處,挑法用于文字筆畫(huà)收鋒處,二者功夫在于指尖,往往差之毫厘,謬之千里,而高低往往只在這毫厘之間。
此八法可單獨(dú)使用,亦可二三組合,有時(shí)一刀出去只一法,有時(shí)一刀出去含幾法,全在腕底指尖及腰部運(yùn)氣配合,是需要一定功力的。 而出刀肯定,刀路清晰,輕重有度,收刀利索,氣韻流暢則是諸法不變之理。
刻銘除刀法熟練,對(duì)石性也須有一定了解,石材不同,石性不同,或緊或松、或硬或軟、或滑或澀,都會(huì)對(duì)運(yùn)刀形成重要影響,這一點(diǎn)需要經(jīng)驗(yàn)積累,自我體會(huì),到一定程度,甚至可以根據(jù)刀感斷出石料品種及石質(zhì)好壞。余根據(jù)自身實(shí)踐覺(jué)得石質(zhì)越好,刻上去越是不緊、不松、不硬、不軟、不滑、不澀,更不會(huì)有起皮或跳刀等現(xiàn)象。
9、落印
銘文當(dāng)拓而視之,拓印后,白為黑,黑為白,故硯上落印,與篆刻陰陽(yáng)相反,紅為白,白為黑,應(yīng)朱文陰刻,白文陽(yáng)刻,斷不可朱文陽(yáng)刻后在印邊再開(kāi)一圈邊加以區(qū)分,不陰不陽(yáng),拓印后陰陽(yáng)錯(cuò)位,黑白倒置。
此外與篆刻不同,硯銘的印章內(nèi)有較大空白,當(dāng)修平地,如此無(wú)需拓印,直接觀賞印味尚存,再者篆刻本身已有金石味,若底子再余刀痕,刀上加刀,亂矣。
硯銘創(chuàng)作的主動(dòng)性
古來(lái)一般是先有硯再刻銘,硯銘往往是被動(dòng)的從屬于硯,這對(duì)于硯銘一道的發(fā)展無(wú)疑起到了一定的局限作用,對(duì)于石、工、銘三者的統(tǒng)一性也是一種制約。雖有“硯以銘貴”的說(shuō)法,但所貴者更多的是治銘者的名氣,至于內(nèi)容文字反居其次。時(shí)至今日,我國(guó)制硯業(yè)蓬勃發(fā)展,制硯名家輩出,其中不乏有自我之追求者。如能治銘者與制硯者聯(lián)手創(chuàng)作,一開(kāi)始就將石、工、銘三者作為一個(gè)統(tǒng)一的藝術(shù)行為進(jìn)行整體考慮,也就說(shuō)將硯銘作為硯的有機(jī)組成部分,對(duì)其文體、內(nèi)容、布局、字體、運(yùn)刀一開(kāi)始就與整個(gè)硯進(jìn)行統(tǒng)一考慮,無(wú)疑對(duì)于硯藝的發(fā)展與硯文化的提升是有重要意義的。再說(shuō)得具體點(diǎn),就是一方硯的創(chuàng)作與制作是以工藝領(lǐng)軍還是以文化領(lǐng)軍的問(wèn)題。
“硯道”古學(xué)也,我輩在繼承古人的前提下是否可以向前走呢?硯銘創(chuàng)作主動(dòng)性的嘗試這一小步也許可以輕輕邁出了。
余音
硯無(wú)銘,如畫(huà)無(wú)款,亭臺(tái)無(wú)楹聯(lián),山川無(wú)飛檐。千百年后,斯人已去,而精神則通過(guò)一行行文字得以長(zhǎng)存,硯亦有了生命與靈魂,硯道不衰矣。

臥云聽(tīng)松硯 拓片

雙清硯 拓片

硯名:玉潔冰清硯
尺寸:16.4 x 10.5 x 1.7(cm)
描述:
此硯為端硯麻子坑石上品所制,通體天青并有清潤(rùn)魚(yú)腦凍,右上角借鑒漢代玉雕的云紋手法加以裝飾。云紋雕刻圓熟、圭角分明、層次豐富、不露刀痕,有如長(zhǎng)出來(lái)一樣自然貼合。
硯面微凹,視之若平。硯背斜切面的制作,在工藝上也是個(gè)難點(diǎn),難在如何保證斜切面棱線(xiàn)的挺拔峻峭。
硯盒以大漆嵌螺鈿的手法制作,螺鈿花紋由漢代云紋演變而來(lái),硯盒色彩搭配也采用漢代漆器最為常用的紅黑搭配,從而使硯盒與硯本身在風(fēng)韻上得到良好的統(tǒng)一,也極大增強(qiáng)了整個(gè)硯的藝術(shù)感染力。
硯銘內(nèi)容:
背面:
北冥冰魄,昆侖玉魂。
生之幽谷,伴之紫云。
清澈我懷,溫潤(rùn)我心。
與君相守,一往情深。
正光銘 印章:千佛
左側(cè):壬辰一笑齋精制端溪麻子坑逸品玉潔冰清硯。

硯名:云海硯
尺寸:23.2x 18 x 2.8cm
描述:
此硯為端硯坑仔巖精華所制,天青透底,硯面有大團(tuán)魚(yú)腦凍盈蕩。此硯的款式在繼承傳統(tǒng)的基礎(chǔ)上又有新意,正面云紋包覆至背面,有如錦邊。周邊所刻云紋,纏纏綿綿、浩浩蕩蕩,生長(zhǎng)空萬(wàn)載之嘆、揚(yáng)橫掃日月之心。
硯銘內(nèi)容:
背面:江山元?dú)猓f(wàn)載長(zhǎng)空。
橫掃日月,潛隱飛龍。
潤(rùn)澤大地,浩蕩心胸。
倚劍笑傲,立馬揚(yáng)鬃。
辛卯千佛山人王正光題刻
左側(cè):此硯制作始于庚寅之夏,成于辛卯之秋,撫而望之,如見(jiàn)星河水,似立岱宗峰,乾坤吐納,滌蕩心胸,文房神品也。一笑齋精制。

拈花一笑 國(guó)畫(huà) 王正光